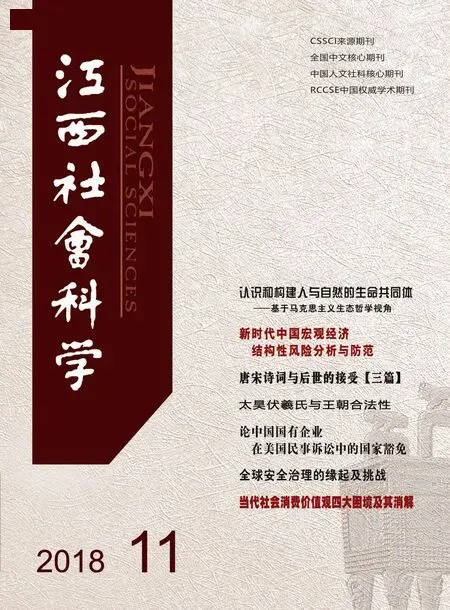漢代文吏的流變
——兼論“儒法合流”的路徑選擇
秦代以降,文吏成為帝國體系存續不可或缺的因素,漢代文吏的演變以一種鮮活的形態呈現出漢代社會思潮的變革,更作為一個例證,說明了“儒法合流”的路徑選擇并非由一二智者主導,不應做“人治”之維的簡單描述,而是經歷了一系列嘗試與博弈之后的歷史選擇與文化自覺。前人有關漢代法制思想變遷、“儒法合流”的敘述已經非常詳盡,但從社會發展的動態角度選擇一個關聯性強的文化主體加以考察的做法并不多見,而漢代文吏恰好可以提供這樣一個視角。“儒法合流”對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乃至傳統文化整體都影響至深,基于社會本身的繼承性與延續性,這種影響在今天依然保有其特定的溫度。
思想學說本身是柔性的、待選擇的,如果其適合社會發展的需要,并得到統治階層、精英階層的認可和采納,柔性的思想便可能具備一種剛性,成為一股構建國家政治、文化的強力。假以時日,如果這股強力能夠成為一種制度,那么在思想的剛性之上就又多了一份韌性,這就意味著具備了更為穩定、更易于適應和延續的特征。漢代社會思想的變遷,尤其“儒法合流”的進程是一個橫亙于中國法律發展史上的大命題,從董仲舒的“春秋決獄”到《唐律》的“一準乎禮”,從“親親相隱不為罪”到“準五服以制罪”,反映了儒家道德準則不斷制度化、法律化的進程。“儒法合流”本是國家政治法律范疇內的現象,但其影響卻突破了這一維度,對整個傳統文化的發展、成型都產生了相當的塑造作用。歷經強秦獨任法家、漢初黃老為治之后,儒家思想逐漸復蘇,并通過吸收其他學派的思想以應對時變,其中對后世法律文化走勢最具影響力的即為“儒法合流”。楊鴻烈在《中國法律思想史》中提到,對中國傳統法律思想的研究應該從“靜態”和“動態”兩個方面進行歷史的考察[1](P4),然而以往學界對漢代法律思想演變、“儒法合流”的研究以文本、靜態的居多,功能性、動態的較少,故本文擬以漢代文吏為對象,通過考察這一群體的實踐活動及其自身發展變化來解釋漢代各種思潮的博弈和“儒法合流”的路徑選擇。
一、兩漢頗重文吏
(一)文吏釋義
文吏之“文”指“文史法律”,因此文吏又稱“法吏”“文法吏”,其主要職責為制作行政、司法性質的文書,因經常需要捉刀弄筆在竹簡上書寫修改,所以也被稱為“刀筆吏”。文吏還有一項重要職責就是處理各種獄案,因此有時還被稱為“獄吏”。①秦漢時期的文吏隨著帝國模式的開啟而登上歷史舞臺,他們往往自幼就接受法家化的啟蒙教育,是法家“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理念的產物,也是國家機器運行中最不可缺少的部件。[2](P274)秦國崇尚法治,而法治的實施需要大量精通法律、訓練有素的文吏作為其政策的執行者,因此提出“置主法之吏,以為天下師”[3](P43)的理論,并在官署中設置“學室”,由“史”或者“令史”兼充教員,專門訓練、培養文吏。“史”“令史”本身是各級政府機構里通曉行政、刑獄、文書、檔案等項事務的吏員,“史子”是其學徒弟子,史子所學的內容包括識字、“吏事”和律令,制作文書、請示應對、熟悉并記錄律令條文為其基本功。根據秦國的規定,平民子弟希望進入吏途必須要有一個學習吏事的過程,需要掌握常見的姓名書寫、熟悉國家律法、通過相應的考試。文吏在成為“吏”之前接受的訓練基本都是如何處理基層行政事務、解決輕微的法律糾紛,只有具備了做吏的業務能力與資格,才有可能通過長吏的辟置而進入吏途。[4]所以在韓非提出“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5](P347)之前,秦國已經在朝著這個方向發展了。
(二)兩漢何以重視文吏
法家思想本是諸子學說之一,其“富國強兵”“以法為治”的主張最終使秦國完成了兼并天下的偉業,締造了中央集權的秦帝國,文吏制度則是法家思想的制度化,法家學說的程序化。隨著強秦二世而亡,法家作為一個學術流派也漸趨衰滅,但有秦一代的諸多制度為后世所承用,也許正是因此才會有譚嗣同“兩千年之政皆秦政”的感嘆。法家思想除了通過確定的制度得以保留之外,還以融入道家成為黃老之學和儒法合流的途徑保持了自己的影響。漢初流行的黃老之學與后來興起的儒術都是作為秦法家思想的反向運動而作用于政治的,秦漢之間法家、道家和儒家的互為消長、迭相興衰構成了中國政治文化史上的奇觀,也是此期傳統法律文化思想史上的一個重要特征。
西漢建立以后,秦制帝國的形態得以保留,因此雖然秦漢兩朝主導思想大相徑庭,法家思想由前臺轉為幕后,黃老與儒家反復爭奪主導地位,文吏作為國家運行的人員保障始終受到重視。文吏的思想構成雖隨著時代發展而不斷變化,但文吏制度卻因帝國形態的保留而得以保留。高祖劉邦甫一入關便與民人約法三章、廢秦苛法,同時卻宣布“諸吏人皆案堵如故”[6](P362),皆因文吏確已成為集權帝制不可或缺的官僚群體。強秦二世而亡的社會現實勢必會給漢王朝統治者帶來極大的心理壓力,以期通過改革來實現長治久安,但凋敝的民生經濟和脆弱的社會心理不足以支持進行激烈的變革,而黃老的清靜無為、休養生息正適合此期社會恢復元氣的需求。以黃老之治代替“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只是淺層的變化,而內里帝國的運轉已經離不開文吏的作用,這也是有實無名的“新法家”稱謂的由來。[7](P823-824)漢宣帝時期的名臣路溫舒就曾經上書直陳,文吏是秦亡的十大禍端之一,也是被漢王朝保留下來的唯一一個。[8](P2369)賈誼也評價文吏說,“俗吏之所務,在于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只顧執法守責、行政效能,卻無助于長久的規劃。因此,“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8](P1547)此類感嘆與評價也證明當時文吏的社會影響非常廣泛。
“西漢中期以前特別是在西漢前期,秦代尚法而治的社會風氣仍給當時的社會以較大的影響,而且此時儒家的思想學說雖逐漸得到上層統治者的青睞,但在實際政治中儒家學派沒有能夠也沒有能力馬上占據國家立法和司法的陣地,因此在社會中‘尚刑名法術之學’的‘文吏’仍在實際上操縱著司法統治大權。”[9](P161)漢代政治實踐中對文吏的重視還表現為刀筆小吏可仕至公卿,漢相蕭何、曹參都做過秦的刀筆吏,明悉國家律令;起自底層小吏的趙禹、王溫舒等官至廷尉,張湯、于定國、丙吉、薛宣等則位列三公,東漢甚至出現了世習律法的大族。后世所謂“秦尊法吏”“秦任刀筆小吏”“獄吏得貴幸”,以及《論衡·程材》言:“文吏治事必問法家,縣官事務,莫大法令……法令漢家之經,吏議決焉”[10](P121),都反映了經過先秦一系列的變法運動,文吏已經取代世襲貴族成為國家行政、司法職能的主要承擔者,其行政管理功能為秦漢帝國所接受。漢代文吏的演變以一種鮮活的形態呈現出了漢代社會思潮的變革,更作為一個例證,說明了“儒法合流”的路徑選擇并非由一二智者主導,不應做“人治”之維的簡單描述,而是經歷了一系列嘗試與博弈之后的歷史選擇與文化自覺。
二、以道統法——漢代文吏的黃老化
漢初的黃老之學雖然不再像戰國“黃老”那樣重點在法而不在道,完全排斥儒家推崇的“禮治”或“德治”,但其依然重視法律在社會治理中發揮的作用,只不過開始強調由道來統攝法律,以道統法,道、法并行。黃老對法律的重視不僅有助于對前朝法制的繼承,也為文吏的延續搭建了一座橋梁。因此,在黃老學說的統帥下,法家思想在西漢前期依然占有重要的地位。
秦代強調以法治國,通曉法律、擅理獄案是對文吏最基本的要求。《商君書·定分》提出朝廷、郡、縣負責向百姓和其他官員宣傳、解釋法律的文吏“敢忘行主法令之所謂之名,各以其所忘之法令名罪之”[3](P42),不僅要求文吏明法還需行法。“刀筆小吏”又可積勞擢為達官、升為朝臣,暗合了韓非“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將必發于卒伍”[5](P354)的理論,以實現文相武將都經過基層文吏的歷練。《韓非子·說疑》將文吏形象描繪為“夙興夜寐,卑身賤體,竦心自意,明刑辟,治官職,以事其君”,知法、勤勉成為秦代文吏的標簽。秦末農民戰爭和楚漢戰爭期間死于戰亂和災荒的百姓幾乎達到總人口的半數,《史記·平準書》載“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餉,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民人更是處于“無藏蓋,大饑饉”,甚至“人相食,死者過半”的境地。在這種情況下,為了安定社會,恢復經濟,發展生產,防止大規模農民起義的再次發生,緩和階級矛盾和統治集團內部朝廷與諸侯王之間的矛盾,奉行黃老的無為而治、與民休息在西漢早期的國家政治生活中形成了廣泛的共識。“舉措暴眾而用刑太極”[11](P42)的秦朝法家思想得到有效的抑制,從而造就了“蕭曹為相,填以無為,從民之欲,而不擾亂”的政治景象。勤于刀筆吏事的文吏也隨之黃老化,高效的行政、嚴苛的執法被無為寬緩所代替。繼蕭何之后擔任漢相的曹參是文吏黃老化的典型代表,其出身秦時文吏卻篤信黃老。在相國任上,他消極沿用前任丞相的政治舉措,選用木詘于文辭的忠厚長者擔任丞相府的重要官員,他自己則無為飲酒,對屬員執事并不過分苛責。[6](P2030)他的擇吏標準促成了漢初“長者為政”的吏治風氣,淋漓盡致地表現了他的黃老風格:“長者”不僅僅指年長寬厚而已,實際上代表了一種清靜放任的黃老治世精神,與文吏的進取苛察、循法守職背道而馳。[12](P276-277)
黃老學派對法律的社會作用有著深刻的認識,提出“言事者必究于法”和“無法不可以為治”的觀點,認為民人很少能夠自覺遵守法度,因此國家必須創設嚴格的法律加以強制,順服者賞,不服者罰。洋溢于黃老著作和人物思想中的這些理論,與法家對法的認識,最大的差別乃在于辨識“法”在一國政治中處于何種地位,在法家看來,法的地位是最高的,甚至君主都應該遵守法度;而黃老則將法納入“道”的統領之下。漢初黃老學派秉承此種對法家理論近乎理性的態度,一方面大力批判了嚴刑苛法對社會的破壞作用,另一方面也認識到立法制刑、懸賞設罰所具有的分別是非、明辨好惡、審察奸邪、消弭禍亂的積極意義。[13]這一學派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沖破了先秦諸子原有的思想體系,從法律思想發展史的角度來看,黃老的法律思想實現了中國傳統法律思想由單一向多元的轉變,很大程度上也為中國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確立創造了前提。
受黃老思想影響,漢初往往“木詘于文辭”者被重用,“吏之言文深刻,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口辯、文深甚至成為晉職的障礙。“趙禹,用廉為令史,事太尉周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居大府。’”[6](P3136)文景時期的名臣張釋之深諳黃老之術,幾次諫言漢文帝守法,與曹參“守法不失”的主張一致。《史記》載文帝曾到上林苑游玩,想了解一下苑內珍禽異獸的情況,向負責管理林苑的上林尉一連問了十幾個問題,他一個都答不上來,而旁邊的虎圈嗇夫卻替他一一答復了文帝的問題,而且“口對響應無窮”,口才非常好。于是文帝想將虎圈嗇夫提拔為上林令,張釋之卻諫言:“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斅此嗇夫諜諜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于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于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6](P2752)文帝聞言打消了提升虎圈嗇夫的念頭。從張釋之的諫言中至少可以得到兩個方面的信息:一方面時為左右丞相的絳侯周勃、東陽侯陳平像上林尉一樣不專注政務,可見漢初重“長者為政”“無為而治”的風尚;另一方面張釋之所言“秦任刀筆吏,二世而亡”與路溫舒所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如出一轍,這種表面上對文吏的否定評價實際上是對文吏身上法家因素保持警惕的一種心理。但是黃老無為并非法律虛無主義,大量好申韓之術的文吏的存在證明了法家思維依然影響著漢初政治,只是不得不潛身于黃老“以道統法”的理念之下,黃老政治的蔓延雖使文吏的活動受到束縛,帝國體制的運行也因之放慢節奏,但文吏制度本身并未受到顛覆性沖擊,“總體而言,文吏政治并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14]。
三、重典治世——漢代文吏的極端化
黃老政治對漢初經濟的恢復居功至偉,但無為而治繁榮了經濟的同時,也促成了社會矛盾的不斷醞釀、積聚,匈奴犯邊、諸侯坐大、強宗豪右壞法,最終迫使統治階層轉變思維。當黃老中的無為因素迅速褪去,儒法思想又尚未實現實質意義上的合流時,法家思想暫時擺脫束縛重又“靈光一現”。
漢初幾十年間無為而治實現了社會經濟的恢復,也促生了新的社會問題。文吏秉持法家思維,希圖以立竿見影的功效解決涌現的社會問題,于是文吏的極端化模式——酷吏開始大量出現。文吏在黃老思想的束縛之下,將其主動性降到了最低點,但當時代背景發生變化時,文吏身上所蘊含的法家的事功性質自然會暴露出來。文吏通常自基層小吏做起,從啟蒙教育階段即開始接受法家思想的影響,熟悉國家律令典籍,掌握處理政事的技能,并依照處斷能力、政事功績和年勞資歷任職升遷。文吏往往追求奉法行事、公平循良,是法家“法治”理念的產物,也是最早的職業官僚形象。在正常的社會政治生活當中,文吏足以用其所學來解決日常問題,但幾十年的休養生息使得諸多社會問題積重難返,超出了普通文吏依靠厲行守法即可達到社會治理目的的范圍。酷吏的大量出現即是在特定背景下對文吏的一種突破②:文吏所表征的是一種正常的社會秩序,而酷吏往往是社會矛盾加劇的產物,而且這些矛盾經常表現為統治集團內部的相互傾軋,地方豪強破壞法度,民變規模較大。[15][16]酷吏秉承法律所面對和解決的絕非日常所見的民刑事糾紛,而多為危及統治秩序和社會穩定的事件。正如史書所載,酷吏以深竟叛逆、不避宗室、摧折豪強、鎮壓平民暴亂為多,很有后世“重其所重,輕其所輕”的味道。一方面封建法制體系中,君主具有最高的權威,可以通過褒獎典型官吏的行事風格、制定新的法令表明個人傾向,并從更廣泛的意義上影響官吏的行為,從而實現鞏固王權和維護社會穩定的目的。趙禹、張湯、義縱、王溫舒、楊仆等幾位酷吏均被君主稱贊為“能吏”,這種導向使得治獄之吏“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8](P2369)。文吏與酷吏的區別即在于此,文吏極端化為酷吏的法律與政治緣由也在于此。文景時期受黃老思想影響,對叛亂的諸侯王有時還會“憐之”“赦其罪”,從寬處斷,而武帝則令“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顓斷于外,不請”,結果“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桀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8](P2137),表現得“嚴而少恩”,不顧宗法情誼,強調遵守法律,維護法制的統一。又如在處理隆慮公主子昭平君“醉殺主傅”一案時,武帝嘆息:“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8](P2583)最終依法處置昭平君,沒有因宗法情誼而破壞法制。
雖然經過漢儒改造的儒家學說沒能立刻取得一統之勢,但其至少在表面上得到官方支持,權以“緣飾吏治”這一點沒有任何疑問,所以后世的“儒法合流”也就更多地表現為儒家漸盛、法家漸弱,法家的合理、順時之處不斷為儒家所吸納的大趨勢。[17](P66)“儒法合流”的趨勢最早在兩家思想的對立中進行,界限分明,隨后則作為一體的兩端,不斷契合。[18](P313)
文吏向酷吏的轉變與個人品格風范也有一定關系,在同一時代背景之下,并非所有的文吏都轉變為酷吏。酷吏之“酷”只有在其積極意義大于消極意義的時候才有存在的價值,而意義的積極或消極則應由當時社會的主流道德標準做出評價。[16]趙禹、張湯、杜周、尹齊等大多數漢代酷吏都出身于底層文吏,他們通曉法律,知道“文無害”③應為其行事的最高標準。身列酷吏,執行政事卻被稱為“無害”“公廉”“廉平”的為數不少,司馬遷也不由得贊嘆漢代酷吏雖然用刑嚴苛,但卻大多能夠做到奉公守法。[6](P3154)文吏所表征的只是常態下的社會秩序,其循法行事僅以常法的威懾力形成一般的社會壓力;酷吏則是社會矛盾加劇的產物,其更傾向于以重法、“文深”處理社會矛盾,意在形成一種高壓恐怖氣氛。酷吏是中國歷史上非常有特色的一種官員類型,又因為他們往往擔任地方長吏、中央御史、廷尉等官職,所以酷吏也是中國歷史上與“法”有著緊密聯系的一類官員。漢代以降,崇尚德禮教化成為中國傳統社會的主流思想,以“殺伐立威”“風行霜烈”等為特征的酷吏遭到“士人”乃至“世人”幾乎一致的批判和貶斥。正是文吏的普遍存在及其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的現實,為武帝時期酷吏的興起提供了人事上的基礎,特定的時代背景和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則為酷吏的涌現提供了最好的歷史節點。酷吏總是處于“法治”與“人治”、實然與應然的緊張關系中,作為加強中央集權這一特定目的的工具之一,他們往往并不遵循常法,而是以殺伐立威、嚴而少恩。文吏重法源自法家重刑,漢代酷吏重法則更多體現為皇權的“人格化”和政治目的性,正是封建“法治”訴求與“人治”本質沖突的結合。總之,漢代酷吏一方面繼受了法家思想奉法、重刑的影響,另一方面則走上了“片面深刻”的道路。因此,當社會狀況良好,以黃老或者儒家學說即可規范社會運行時酷吏自然少有;當社會矛盾驟升,非法家思想無以滿足社會需求時酷吏必然多出。酷吏這把雙刃劍既使一些棘手的社會問題迎刃而解,又揭開了帝王“內多欲,外施仁義”的“人治”面紗。
四、儒法合流——漢代文吏的儒家化
王充在《論衡·程材》中斥責儒生“有俗材而無雅度者,學知吏事,亂于文吏,觀將所知,適時所急,轉志易務,晝夜學問,無所羞恥,期于成能名文而已”[10](P118),一語道破漢末儒生改習吏事的現象,可見法家透過文吏對漢代社會的影響遠比人們先前所了解的要深遠得多,而儒家優勢地位的取得也經歷了一個比人們想象的更為漫長的過程。隨著儒法兩家思想由外在對立到內部融合,“儒法合流”不斷深化,“修經明學”務在“軌德立化”的儒生和起于“刀筆筐篋”長于“優事理亂”的文吏,自然也處于不斷的融合之中,東漢文吏思想中儒家的成分較之西漢文吏明顯增多即為明證。漢武帝通過重用酷吏、嚴刑苛法有效地維護了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但漢代統治者明白一味適用嚴刑峻法、全面推行酷吏政治必將重蹈亡秦覆轍。儒家可以借助法家的事功之性在政治上取得立竿見影之效,法家亦可以借儒家之禮來弱化其“嚴而少恩”的一面,從而形成可以“累世行之”的正統思想,這也正是儒法合流的兩個方面。而其在實踐中則表現為自漢宣帝朝起,酷吏與循吏并用、儒生與文吏融合。西漢時期儒家注意到法律在政治上的重要,因此為了適應政治的需要,儒家的法律思想由原來的反對刑罰轉變為禮法結合、德刑并用。所謂禮法結合就是以法律制裁來維持禮教,所謂德刑并用就是以德為主、以刑為輔。
喜用儒術緣飾吏治的漢武帝時期是從黃老道法向儒法轉變的過渡期,儒家思想雖并沒有一躍而成為國家主導思想,但漢初幾十年的復興及武帝的提倡使得這一時期儒家思想的社會地位迅速提升,進而形成風氣則是不爭的事實。此期儒法兩家還未能相互吸收整合完畢,處于獨立于彼此的階段,表現為被后世所詬病的“陽儒陰法”“外儒內法”狀態。這一結論的得出是以后世儒法合流最終完成,并成為中國正統法律思想為標準的,雖然客觀地描述了武帝時政治法律思想的特征,但卻忽視了思想發展的階段性。其實自武帝時儒法有內外之分,到宣帝自爆“漢家歷來以霸王道雜之”已經充分表現了儒法由外在彼此獨立向內在一體發展的趨勢。鑒于政治思想發展完善有其階段性,武帝雖尊儒,但儒家尚未調整自身、適應社會變化,因此只能暫且權以“緣飾吏事”。“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偽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于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6](P3094)依漢律“大逆無道”“謀反”等罪名足以置淮南王于死地,但謀事大臣還要援引《春秋》中“臣無將,將而誅”的道德罪名,自是要將刑殺之事做到于法于理都讓人心服口服。“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于律,無乖異者,然而春秋漢之經,孔子制作,垂遺于漢,論者徒尊法家,不高春秋,是暗蔽也”[17](P69),《春秋決獄》在宣講儒家大義的同時也不免有以“儒術”潤飾“吏事”的一面。思想上的浸染使文吏的思想成色不斷發生變化,但制度卻以其特有的硬度歷時延續。
漢代元、成以后,隨著大批儒士進入政權,官僚隊伍開始儒家化,明經之士據經術、行德教。盡管政治出人意料地走向混亂和衰敗,但儒生與文吏的融合,尤其是文吏的儒家化卻已然成為不可逆反的潮流,具有專業法律技能的文吏逐漸放棄排儒立場,許多繼承法家傳統的文吏逐漸學習經學。《漢書·公孫弘傳》載:公孫弘“少時為獄吏”,“年四十余,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征為博士”,“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西漢路溫舒早年學習律令,為獄小吏,可謂法家出身,然而“宣帝初,上書言尚德緩刑”。又《漢書·丙吉傳》載:“吉本起獄法小吏,后學《詩》《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8](P3145)《漢書·循吏傳》載,“(黃)霸少學律令,喜為吏”,但“俗吏尚嚴酷以為能,而霸獨用寬和為名”,他在獄中從夏侯勝受《尚書》,此后“力行教化而后誅罰”,終以循吏聞名。“定國少學法于父”,“數年,遷水衡都尉,超為廷尉”,后“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為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強秦的覆滅證明純粹的“法治”并非成功的治國之道,然而倚靠“刑”來維護政治秩序卻是必需的。因此儒學要真正進入統治者的視野必須將刑納入其“德治”的治國之道當中。“德主刑輔”思想反映了封建社會中法律與道德各自的客觀地位,同時利于統治者打著“圣人之道”的旗幟進行統治,起著為統治的合法性辯護的功能。援法家的“刑”入儒學的治國之道,使其具備了實踐上的可操作性。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德主刑輔”使法家之刑被置于儒家道德的評判之下,對酷吏這種張揚法家個性的現象無疑是一種強大的拘囿。
漢代文吏之所以轉學儒術,最終進入儒家化的路徑,既有內在精神價值的訴求,也少不了外部政治、文化環境的壓力。從外部環境來看,隨著經術傳播的范圍越來越廣,公卿大夫們開始變得儒雅起來。與此同時,法家的政治主張逐漸為儒學所融匯,法家思想的獨立性消失,儒法之間也從最初的兩家思想的融合演變為儒家自身德、刑兩種元素的融合。成為正統思想之后的儒學在皇權的權威、道德原則及治國之道上都為君主專制制度提供有力的、系統的解釋和辯護。思想的轉向最終由社會主體來呈現,《儒吏論》所謂“執法之吏,不窺先王之典;搢紳之儒,不通律令之要。……先王見其如此也,是以博陳其教,輔合民性,達其所雍,祛其所蔽,吏服訓雅,儒通文法,故能寬猛相濟,剛柔相克也”[19](P604),準確地闡明了漢魏之際文吏儒家化、儒生文吏化的歷史動因。隨著武、宣、元三帝對儒術態度的變化,漢代朝廷中儒生與文吏的勢力此消彼長,宣帝以后酷吏與循吏并用和儒生、文吏進一步融合的現象與“霸王道雜之”和“儒法合流”思想一一對應,而文吏的儒家化則最終推動了傳統文官制度的形成。
五、結 語
漢承秦制,但社會主導思想迥異,儒、道、法三家學說之間不斷博弈、融合,呈現了漢代法律思想流變的過程,也呈現了傳統文化應時而變、不斷自新的特征。作為傳統法律的實際承用主體之一,漢代文吏也隨著立國思想的演變而演變,以法家理論為基礎,又先后受到黃老無為和儒家德禮思想的鉗制,儒、道、法三家思想之間不斷博弈、融合,這一思想演變過程也在漢代文吏身上留下了鮮明的印記。本文借助梳理漢代文吏在不同時代背景下的演變闡釋了法家思想以何種形態影響漢代政治,也進一步回答了為什么“儒法合流”會成為傳統法發展的歷史性選擇。初創于秦而盛于漢的文吏制度為后世正統文官制度以及士大夫政治的確立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性。發達的文官制度、頗具理性內涵的官僚組織被公認為中國傳統社會集權帝制長期延續的重要支撐,但官僚組織的制度化理性化、士大夫群體的文化認同[20]并非一蹴而就。柔性的思想學說一旦順應社會發展趨勢,并得到統治階層的認可和采納,則往往很容易轉化為具備普遍意義的社會潮流與規范,成為一股構建國家政治、文化的強力,而這種力量能夠多大程度地制度化、法律化則決定了其對一國政治走向和文化傳統的影響力度。儒家原本空泛的倫理學說憑借系統性和實踐性卓越的法家制度,才真正成為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乃至文化整體的塑造力量和主導思想,儒家倫常彰顯了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核和價值訴求,而法家思想與制度則成為實現此等精神與價值的重要途徑。在經歷了漢初黃老“以道統法”和武帝時期“重典治世”之后,“儒法合流”成為傳統法律思想發展的歷史選擇與主要路徑。
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存在不同的價值訴求,以實現既定價值為目的,從理論上樹立明確的立國指導思想,而國家政治體系、法律框架、經濟形態、道德教化均領受指導思想統攝、綜合為用,此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大特色。后世千百年間經儒法合流而成的傳統法以德禮、刑罰為形態,經由“寬猛相濟”的社會調控方式被逐漸熟練地運用于傳統政治活動當中,形成了別具一格的“一體二元”模式。從“刑罰世輕世重”到“禮法并用”都無不體現著傳統法律“一體二元”模式的靈活性與適應性。筆者認為正是這種治世模式支撐中國傳統社會運行了近兩千年而沒有實質性突破,寬猛之間的隨世流轉相當程度上化解了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矛盾對立,既體現了傳統“人治”社會的靈活一面,又表明常態下的傳統社會治理也存在權力邊界,寬猛即為邊界。寬猛相濟思想的流變也生動地演繹了傳統文化適應社會、不斷自新的歷程。同時也昭示著這樣一個道理:法律雖重要,但絕不能獨任法律,必須使其受到特定價值觀念的拘囿。
“儒法合流”從其形成的歷史過程到實在的內容均對當今中國的社會治理具有啟示意義。“人治”傳統下順應時變以求治世的思維與今天的法治建設并非決然對立,法律為實現其終極價值、解決現實矛盾,在合法范疇內保持一定的靈動更能體現其作為社會調控手段的優越性。中華文化以其不曾間斷的傳承性獨領風騷,雖屢遭外族文化的沖擊,但均以其包容性實現了文化間的融合。可能正是基于這個原因,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20世紀60年代在《展望二十一世紀》中就曾預言,“將來統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歐國家,也不是西歐化的國家,而是中國”[21](P289)。中華文化的生命力和韌性正是來自于其能夠不斷自新的特質,這一特質也必然會為當下社會、文化的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
注釋:
①此處“獄吏”是廣義上的概念,狹義的獄吏則專指各級政府中專門負責司法的掾吏。
②筆者認為這種突破當然不僅僅是由文吏而為酷吏,以刑殺為治具,同時也包括一部分由文吏而循吏的情況。酷吏與循吏往往都面對一般文吏所難以應付的問題,只是問題和思維的差異引發了外部措施的不同。
③“文無害”是秦漢時期選吏和考績的一條重要標準。“文”即要求通曉法律,“無害”要求奉法行事,無所枉害,在辦理公事時不能摻雜個人因素。文吏熟知律令,熟悉本職工作,辦事能力強,同時又執法平和,職事無誤就達到了“文無害”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