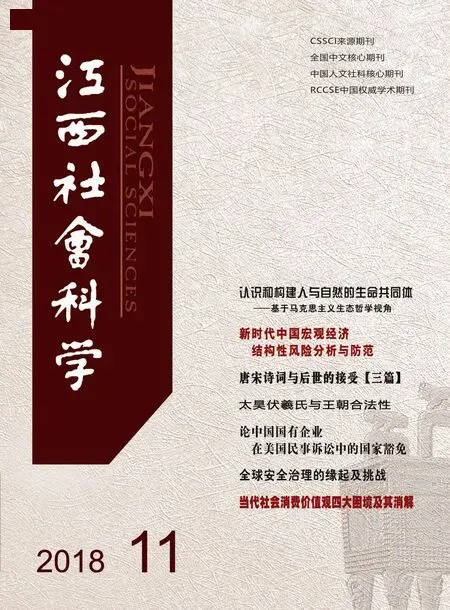后真相:社交媒體時代的新現象?
后真相是當下新聞傳播學科的熱門概念,被認為是社交媒體時代的產物。然而,后真相并不是當下出現的新事物,其早已存在于近現代新聞傳播事業中。后真相不完全是注重情感宣泄而忽視新聞事實。如今的后真相現象恰恰表明了調查性報道式微和傳統媒體公信力下降,以及社交媒體時代碎片化信息惡性循環傳播下,網民對事實的追求與技術利用下的接受心理微變。
在調查性報道日益式微的今天,社交媒體的技術特征使新聞真相往往處于活躍且可知又不可知的撲朔迷離狀態中,造成信息變異、信息異化且反轉新聞的情況時有發生。在 “后真相”(Post-truth)被牛津詞典評為2016年年度詞后,我國新聞傳播學界似乎頓時找到了理論依據與切入口,以“后真相”及“后真相時代”(Post-truth era)為切入視角的研究迅速增加。這些研究認為:當下已經進入新聞后真相時代,這主要表現為傳播者重情感牽引大于事實挖掘,受眾重情感宣泄而忽視事實真相辨析。學界認為只有重塑新媒體規約才能解決這一問題。
一、“后真相”的歷史淵源
(一)后真相起源于政治且一直伴隨著現代民主政治的進程
“后真相”一詞出現于1992年的西方學界,指官方竭力壓制令其蒙羞的真相,封鎖壞消息,民眾則竭力從中辨別出真相,并自覺或不自覺地“生活在一個后真相的世界里”。[1](P12-13)在西方政治語境中,該含義一是強調官方對丑惡政治真相有羞恥感而竭力掩蓋,二是民眾開始有知情權意識且注重對真相的追尋,以此可以看出公民意識開始覺醒。人類進入私有制后的歷史同時也是歷史真相的隱瞞史,因此后真相概念最先出現于政治領域亦屬正常。
2015年美國學者杰森·哈爾辛(Jayson Harsin)創出“后真相制度”(regimes of post-truth)一詞,認為現代社會正從“真相制度”(regimes of truth)轉向“后真相制度”。該論斷缺乏充分的事實依據,當今政治與社會跡象也不能證明這一具有分水嶺式的退化。如韓國的樸槿惠案及多任總統被查而不得善終,美國的水門事件、伊朗門事件、克林頓丑聞、虐俘事件、郵件門等,雖然反映了政治范疇內后真相現象的嚴重性,但亦體現了監督的力量與制度的自我治療能力,同時也不能就此判斷以前的真相是透明。英國學者威廉·戴維斯2016年在《后真相政治時代》一文中指出: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更危險的“后真相政治”(Post-truth Politics)時代——真相不再是被扭曲或受到爭議的對象,而是它本身已變得不再重要,個人有越來越多的機會圍繞自己的觀點或偏見來做出判斷。[2]該論斷看出了社交媒體在這方面的影響與變化,但亦存在以少數個案得出整體性結論的弊端,少數個案既不能得出其是一種現象的結論,更不能以此斷言進入了某種時代,在新聞傳播領域說進入了后真相時代所犯的邏輯錯誤同樣如此。《經濟學人》雜志批評后真相政治“為了創造一種對于虛假觀念的政治謊言的揭露,這些政治謊言加深了目標選民的偏見”[3](P11)。鼓動或左右民眾情緒是歷史上西方慣用的政治手法,只是民主社會給民眾提供了對真相質疑調查與對政治人物通過選票選擇的機會,社交媒體只不過是給了民眾與政治人物一個可以利用的新的技術媒介而已。支庭榮指出后真相作為一種植根于西方政治土壤中的社會現象由來已久,新媒體的興起則將它從幕后推到了臺前。[4]
(二)新聞傳播領域的后真相長期存在,并非社交媒體時代的產物
后真相概念在當下新聞傳播領域爭議不大,更傾向于情感認同宣泄,忽視或缺乏對事實真假的考證,而傳播者也利用這一心理煽動情感強化偏向。也即在社交媒體時代“存在著一種‘后真相’現象,網民在接觸到某些敏感信息的時候往往直接觸發情緒,爭相表達和宣泄自己的情感,而真相到底是什么,許多受眾沒有耐心去等待”[5]。《牛津詞典》對后真相的定義為“訴諸情感及個人信念,較陳述客觀事實更能影響輿論的情況”,這里強調了傳播者視角。英國媒體人馬休·達安科納(Matthew d’Ancona)認為后真相強調的并不是謊言、杜撰或欺騙,而是公眾對此的反應,相比事實和證據,公眾的情感共鳴變得越來越重要了。[6]這一觀點強調網民在接觸新聞信息時身份及階層認同在情感上的積極滲入,從當今受眾在接受新聞信息時表現的群體極化行為、衍生輿情及反轉新聞案例來看,后真相行為確實比網絡出現之前普遍,技術的力量讓這種現象如今易于得以公開呈現。
傳統媒體也一直注重新聞報道中訴諸情感影響的力量,受眾也易于受媒體報道或宣傳內容的影響,“皮下注射論”“魔彈論”“議程設置論”既是典型的受眾接受心理受情感的左右,也是媒體對情感認知規律利用的證明。從東西方近代報刊產生以來,新聞媒體訴諸情感從輿論上左右受眾的做法慣常存在。西方調查性報道多涉及能引起民眾強烈反響的問題,強調什么樣的選題能引起轟動,本質上也有對情感操縱的考慮。美國傳播學者斯坦利·巴蘭等人通過研究指出:20世紀30年代在傳播中用半真半假的陳述和徹底的謊言更易說服人們放棄“錯誤”的想法并接受宣傳家所喜愛的觀點。“一戰”“二戰”時的新聞宣傳即是典型的訴諸情感大于新聞事實的做法,動員民眾的情緒成為必要。李普曼的“刻板成見”與“虛擬環境”反映了當時大眾媒體對受眾的情感偏向的塑形與固定,他指出:“要獲得讀者的注意力……要激起讀者的感情,要引誘他在閱讀時就產生與新聞相一致的感情……為了進入新聞,在新聞報道中他必須找到一個熟悉的立足點,而這個立足點是由固定成見提供的。”[7](P234)新聞學者對于媒體報道內容的框架研究基本上源自高夫曼(Goffman)的框架理論,傳統媒體的框架式報道則是直接直白地訴諸對受眾的情感牽引大于對對象的客觀真實報道,如妖魔化報道即是體現之一。在19世紀后期開始出現的追求“客觀”與“獨立”的新聞專業主義及之后的社會責任論對報刊濫用新聞自由與媒體力量的約束,即有對報刊過于操縱受眾情感傾向的糾正。“新聞專業主義就是在工作中把持自我而不顧個人情感,甚至去做一些自己不相信的事”[8](P109-127),其要求新聞報道中不能摻入個人情感因素,也不要通過報道操縱受眾情感,從而做到客觀報道。新聞專業主義對“客觀”的解讀是對事實的信仰,不相信價值觀,致力于超脫。[9](P6)互聯網時代常常出現的帶有鮮明后真相特征的“媒介審判”,實際上也不是互聯網出現后的產物,紙媒體時代曾經運用得更為直白普遍。
大眾媒體具有在新聞報道上左右受眾情感傾向的屬性,在其發展史上亦長期存在強化受眾情感的做法,同時,媒體一直在致力于揭露真相,也在致力于掩蓋真相,包括用后真相的方式處理新聞。發展到社交媒體時代的用戶生成內容與互聯網的交互性等傳播特征使后真相現象體現更為明顯,發生的概率更高而已,因而后真相出現于社交媒體時代的說法并不嚴謹。
二、后真相時代更需重視新聞事實
受眾缺乏對新聞事實真假的甄別就迅速訴諸強烈情感的表現,使其被貼上后真相行為標簽,但并不能說社交媒體時代受眾在面對新聞信息時重情感宣泄而忽略新聞事實或事實已經不再重要。
(一)后真相恰恰證明受眾依然重視事實,而非事實不重要
新聞的真相與客觀有具體可感的標準,一次特大礦難事故的責任在誰,一個重大事件的黑幕在哪里,深度報道文本準確地呈現出關鍵點即是做到了客觀報道與揭露真相。新聞報道的客觀性要求不是哲學意義上的“客觀”永遠達不到,也不是福柯所言的真相不過是權力的代名詞。真相與客觀一直是新聞從業者追求的目標,也是受眾對重大新聞報道的要求。
傳統媒體時代多為新聞事實引爆輿論,互聯網時代多由新聞事件的觀點爭論引起,社交媒體時代則轉變為新聞事件流行語的病毒式傳播。從信息的傳遞接收而言,傳統媒體時期新聞信息的傳播對象被稱為受眾,社交媒體時代再用受眾概念倒不準確,信息的接受者同時也是傳播者與內容制造者,當今人們花費在新聞信息上的時間遠超過傳統媒體時代,人們對新聞的關注是為了獲取更多的新聞信息,不是為了尋找假新聞或借助新聞信息進行情感宣泄而不在意新聞事實的真假。社交媒體的出現帶來了獲取、傳播、生成信息的便利,加之由于權威信息的滯后或缺失,反轉新聞、反轉輿情現象時常發生。當“后真相”一詞帶著時髦與玄奧色彩出現卻貌似又能很好地概括這類行為時,學者們好像一下子找到了闡釋工具,紛紛認為網民在接收新聞信息時不再關注事實,而在乎借助信息進行個人或群體的感情宣泄,并冠之后真相時代。
真相總是急于掩蓋,真相的當事者經常缺位,不是真相不重要而是揭露真相有難度,這才有調查性報道的存在與新聞專業主義的追求。人類需要新聞業是為了知情權、監督權以及解決社會問題與了解自己所處的環境是否安全。作為后真相典型表現的反轉新聞,其本身多屬于能快速觸發人類倫理良知或公平正義的事件,具有讓人在本能上快速同情或憤怒的特質,如“成都女司機被打事件”“羅一笑事件”“孕婦跳樓事件”“女大學生扶老太太事件”等不斷反轉的后真相新聞,傳播者為了吸引點擊率也易于對這類新聞事件采取后真相處理,從而導致社交媒體時代的后真相現象。另外,從這類事件來看,還是事實帶動了情感,而不是情感帶動了事實。這類新聞事件不同于調查性報道所關注的重大時政、經濟、環境等深度病癥的選題,其多掩蓋在平靜的生活之下,需要專業的記者較長時間的調查才能呈現。
以反轉新聞與反轉輿論為典型體現的后真相行為恰恰是民眾在意真相,網民為不斷新出現的新聞真相改變以前的認知,真相不斷地被挖掘也是網民呼吁真相的輿論聚集壓力所致,這種相互循環不是出爾反爾,倒說明了網民對新聞事實的追尋與認可,不斷呈現的新聞真相也是對網民訴求真相的回答。網民在這類事件中情感的反復是因為得到了新的事實信息,情感愛憎隨著新聞事實的不斷被挖掘而變化亦屬于正常的心理反應,對新聞事實的持續關注則說明了網民對事實真相的看重,而不僅僅是注重借助事件來發泄自己的情感。
如果網民不需要真相就不需要出現反轉新聞,或者說當新的事實被揭示時網民對此應該無動于衷。彭蘭認為擁有了傳播權力但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普通公眾,顯然很難從事實判斷、價值判斷的角度來進行信息篩選,大多數人只能是基于個人的直覺和情緒需要去選擇想要的信息。[10]因而在信息接受中出現后真相表現也不能說明民眾非理性與不再關注事實,理性一直是人類的基本屬性也是人類繁衍發展的基礎,如在武力恐嚇、經濟趨利或某一榮耀理念下的做法看似非理性,實則具有現實的理性。當然,社交媒體時代的技術便利造成了網絡上不斷反轉新聞,受眾面對直接違背人倫良知或公平正義的重大新聞事件時情感宣泄的后真相特征確實相對明顯。
(二)后真相暴露了深度報道的缺位,而非受眾情感認知不足
互聯網發展到社交媒體時代,調查性報道日益式微與傳媒公信力下降,網民轉而通過三微一端等網絡社交工具追逐事實真相,這種情況下造成的反轉新聞或真相撲朔迷離正說明了專業記者專業調查的缺位,加之“信息繭房”效應等讓“我們只聽我們選擇和愉悅我們的東西”[11](P8)。這導致在新聞事件發生后雖然社交媒體上會馬上出現相關信息,取得了時效性與公開性上的優勢,卻缺失了深度報道與權威信息,看似豐富喧囂的信息中有價值的核心信息缺乏,碎片化情緒化的信息在網絡上惡性循環地相互傳播。客觀地說,新聞反轉是網絡輿論場中信息不對稱的一種體現,非圍觀網民之責。[12]網民沒有現場采訪權及受過調查性報道采訪專業訓練,外圍感知或外圍信息的中轉難以獲得全面客觀的新聞信息,網民在碎片化情緒化信息的相互轉發中因事件本身帶來的情緒起伏與得不到權威真相的不滿情緒混雜,也是后真相行為發生的推手之一。
新聞信息權威來源的缺失加之網絡平臺成了商業力量與各類輿論的秀場,具備能快速點燃民眾情緒的新聞事件成了網絡平臺炒作的對象,在微信微博興起后的社交媒體時代,后真相現象的易于發生體現了調查性專業報道的缺位,而不能僅僅歸因于網民媒介素養的欠缺與對新聞事實的不重視。
三、后真相:認知規律、技術因素、專業性式微
后真相出現于社交媒體時代說法雖然欠妥,人類亦沒有進入新聞信息傳播的后真相時代,但后真相行為還是存在,辨析清楚其本質以及其為何產生存在的原因則有利于客觀認知后真相,進而有效解決后真相帶來的新聞傳播問題。
(一)認知規律上:新聞信息接受中情感因素不可分割,增加了后真相的迷惑度
大眾媒體的報道潛在地遵循強化理論(reinforcement theory),強化而不是改變現存的觀點與行為。受眾易于根據情感與認知傾向選擇性關注新聞事件中的部分事實并強化某類情感,從而導致群體性的一致情感走向亦是常見的接受心理,這并非是社交媒體時代才有的認知規律。傳播學者DeFleur在互動過程模式中指出:受眾接受信息過程中具有選擇性暴露、記憶和認知,最終使得“包含特定刺激屬性的媒介訊息,與受眾成員的個體特征發生有差別的互動”。人類對信息選擇在情感與認知標準上具有天然的自我屏蔽行為,“多數情況下我們并不是先理解后定義,而是先定義,后理解”[12](P67)。霍爾(Stuart Hall)提出媒介內容的主導性解碼和對抗性解碼的受眾接受方式皆具有鮮明的情感因素滲入其中。在這種參與中,外在政治、社會、宗教、文化等環境綜合塑形出的受眾前理解、刻板成見、個人記憶、集體記憶、身份認同等都會積極參與到對新聞信息的接受解讀上,而強烈的主觀情感性是這類心理認知的共性。特納認為,集體行為的產生需要某種共同心理,包括共同的意識形態、思想和憤恨。[13](P93)受眾會強化能凝聚身份認同、情感認同的那部分信息,舍棄能弱化情感認同的信息,這種對情感的快速認同多是在一種集體無意識中達成的,個體不需要先告誡自己要從某種情感狀態來解讀面對的信息,無數個體的無意識反應聚集成相同的集體無意識,這種集體無意識的趨同其實是先前共同社會經驗的積累與喚起,如共同的前理解與集體記憶等,導致受眾接收能引起其強烈情緒的新聞信息時表現出即時又強烈的情緒,而并非就是對新聞事實的不重視,也即其表現出的后真相特征主要取決于新聞事件的性質與受眾的生活心理狀態。社交媒體只是更有利形成這種情感表現特征的技術中介而已,因而易于導致產生后真相行為是出現于社交媒體時代的認識。
情感因素的參與是人類認知固有的心理特征之一,也是長期存在于新聞傳播史的受眾接受特征之一。“感性大于理性、謠言超越真相,決非這個時代獨有的病癥,而是伴隨數千年人類社會發展史和傳播史的固有命題。”[14]媒介系統依賴理論(Media-system dependency)認為個人越依賴媒介則媒介對個人的影響就越大,社交媒體時代特別是年輕人已經患上了手機依賴癥,人本身異化為工具的奴隸,陷入手機提供的信息、娛樂與以二者為載體的情感互動與綁架中,依賴越深越容易對社交媒體提供的信息情感性地關注及參與。樸素心理理論指出人們通過經驗和直覺對某些現象、新聞、事件和信息自發地產生不成熟的看法和理解,并將這些看法和理解模式化。人類認知一貫性的特性也表明人們會有意識或無意識地保持他們已經存在的觀點,在接受新聞信息時固有的前理解經驗與個人情感會參與對信息的解讀中。這種心理西方學者從兩個方面進行了接近后真相的闡釋。一是人們對于情緒的追求大于對真相的探尋。人們的判斷和經驗很大程度上來源于情感,情感在任何決策中都起著重要作用。真相正在被情緒化的言論所取代,每個人都可以在網絡上找到屬于自己的真相。在眾聲喧嘩之中,事實往往被埋沒。二是社交媒體在不斷地消弭事實。社交媒體在進行信息把關和過濾的同時,用戶也在過濾屬于自己的信息,優先選擇和消費那些與現有價值觀、信念和觀點相符合的內容。[15]
從引起受眾強烈后真相行為的新聞事件來看,多屬于涉及人倫善惡、切身利益或公平正義的民意表達范疇,這種看似忽視事實的感性宣泄一是體現了人類基本的良知,反轉新聞反轉輿情不是壞事,是人的良知的體現,也是對真相的認可與糾偏;二是體現了受眾在價值信仰、集體記憶、刻板成見、前理解以及身份認同上的快速共鳴。“考慮事物虛幻的形狀,遠比考慮它們的真正形狀更重要,因為只有它們,是我們能看到并加以再現的形狀。有時不真實的東西比真實的東西包含著更多的真理。”[16](P32)為什么會出現群體一致性的情感態度與宣泄,恰恰說明了同類事件反映的社會問題所在,也證明了受眾根據感性經驗的“前理解”等基本能看出問題的本質,因而不能簡單地指責受眾的非理性與對事實的不重視。
(二)技術性因素與調查性報道式微的合謀
互聯網時代與社交媒體的發達,用戶生成內容(user-Generated Content)成為現實,傳播權威消解,信息比以往更多,來源更為多元,有圖有視頻的傳播技術讓人們真假難辨,受眾對新聞信息的淺閱讀習慣在互聯網時代漸趨養成,傳統媒體與政府公信力下降,加之媒介外環境因素帶來的調查性報道日益式微,報道深度與力度日漸收緊,造成在諸多重大新聞事件發生后專業的調查性報道缺位,在需要權威性調查性報道進行解疑時不能跟上,受眾轉而依靠社交媒體獲取信息,“隨著主流媒體陷入‘公信力困境’,越來越多的人轉向另類媒體尋求那些可以證實他們主觀愿望或情感的信息”[17](P19-39)。但網民這種信息來源的碎片化、外層化、以訛傳訛等特征,使其無法得到核心層新聞事實。當缺乏來自新聞現場的深入采訪信息,在淺層次信息轉來轉去的過程中網民情感因素被放大,情緒化表達不斷被強化。
所以,社交媒體時代的技術因素雖然撕開了信息透明的口子,但對新聞事件真相的深入專業性報道還是需要專業記者與具有公信力的大眾媒體參與。就反轉新聞而言,受眾一方面在接受信息時根據先有的“前理解”等認知,點燃了其情緒性的情感,但在過程中往往是進一步的真相一直求而不得,網民之間形成了“碎片化信息的惡性循環”,在以訛傳訛與對真相求而不得的焦慮不滿中加重了后真相行為。
(三)情緒性對抗與身份認同的融合
拋開人固有的認知規律與技術因素外,受眾本身在接受信息時的社會心理亦是后真相行為發生的重要因素。受眾更傾向于憑借自己的情感經驗和自身的觀點看法及所處階層對事件作出評判,這種判斷具有情緒性對抗或情緒性認同偏向。同時,受眾在接受新聞信息時還體現了一種身份認同與意識形態立場,重大新聞事件的當事者多為強弱雙方,受眾本能地在思維上形成身份認同以及意識形態的對立,然后再訴諸情感,形成后真相行為的新聞解讀與交互式傳播。
互聯網時代減弱了人們的單向度思維,當受眾獲取的新聞信息長期與公平正義及受眾利益人身安全等發生背離時,對新聞信息的情緒性對抗式解讀就出現了,當涉及公權力或公平正義的新聞事件發生時就容易陷入感情宣泄重于事實細節考證的解讀與傳播習慣中,并利用社交媒體情緒化地交互傳播情緒化的信息,這也是社交媒體時代顯性的后真相現象增多的原因。所以,受眾拒絕真相或忽略事實還有復雜的社會因素,并不是認為新聞事實不重要。
四、結 語
新近出現的流行術語往往含義模糊不清也容易被誤用和濫用,“后真相”或許更是如此。作為新聞報道中的一種現象,后真相確實存在,但學界對其概念的運用有浮躁及人云亦云之嫌,缺乏冷靜的深入思辨,對其內涵的定性亦多有值得商榷之處。另外,有學者說如今進入了政治以及新聞傳播的后真相時代,如“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出現,使‘有圖有真相’讓位于‘后真相’時代”[18],顯然夸大其詞。從某一視角出發定性社會進入某一種時代需有一系列嚴格的測量指標,而不能隨意定性,動不動就采用“后XX”來定性的這類術語即是典型做法。新聞報道的傳播者與受眾主流上還是以理性與事實為準,離不開專業的新聞業,人類并沒有進入不重事實只講情感宣泄的媒體時代。
對于新聞傳播上的后真相現象,應該把其當做一種現象來重視與分析,分析其主要發生在哪類新聞之上,這類新聞如何報道才會引起后真相反應,以及后真相現象存在的背后原因與本質,弄清楚這些,既能科學地闡釋一種現象,也能撥開迷霧避免對概念運用上的流行。后真相概念也是如此,作為一種現象,后真相行為在社交媒體時代體現得更為常見,但并沒有造成新聞真相的危機,彌爾頓的自由市場的觀點同樣適用于新聞真相博弈的市場,受眾永遠需要新聞真相,影響新聞真實的關鍵因素永遠是新聞報道上不受外在力量的制約且欠缺專業的權威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