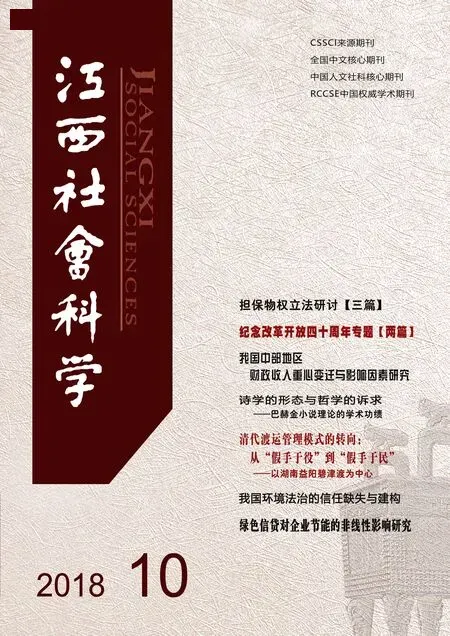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從黑格爾到阿多諾
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Identit?t/identity/identité)問題是哲學(xué)史上一個(gè)經(jīng)久不衰、歷久彌新的問題。自從巴門尼德提出“思維與存在是同一的”這個(gè)命題之后,不同時(shí)代的哲學(xué)家不斷地從這個(gè)課題挖掘出新的理論資源。該問題受到歷代哲學(xué)家的持續(xù)關(guān)注,與它的基礎(chǔ)地位和多重身份有關(guān)。一方面,它屬于“同一性問題域”。在這個(gè)問題域中還有邏輯同一性、辯證同一性(矛盾同一性)、自我同一性(人格同一性)、歷時(shí)/共時(shí)同一性等問題。此外,在同一性問題域的“相鄰問題域”中,還有統(tǒng)一性、差異性、同質(zhì)/異質(zhì)性等問題。在這些問題中,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問題是最具形而上學(xué)色彩的一個(gè)問題。另一方面,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問題又屬于“哲學(xué)基本問題”的論域,恩格斯將其作為哲學(xué)基本問題的第二個(gè)問題——“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問題”[1](P278)。
思維與存在同一性問題既處于傳統(tǒng)認(rèn)識論、本體論的重疊領(lǐng)域,又關(guān)涉現(xiàn)代性、人的有限性等當(dāng)代問題,因而對它的探討在當(dāng)代語境中仍有其特殊的理論和現(xiàn)實(shí)意義。在近代以來的西方哲學(xué)史中,黑格爾、海德格爾、阿多諾對思維與存在同一性問題的思考具有代表性,他們對思維與存在同一性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西方現(xiàn)代性哲學(xué)思想演變的軌跡。
一、黑格爾:貫穿非同一性的同一性
在近代西方哲學(xué)中,思維與存在的關(guān)系在很大程度上轉(zhuǎn)化為主體與客體的關(guān)系問題。黑格爾的同一性概念針對的是近代西方哲學(xué)中的主客二元分立模式,而黑格爾的現(xiàn)代性解決方案即是彌合主客二分、揚(yáng)棄異化(外化)從而達(dá)到同一性,也就是精神與自身和解的方案:“這種最高的分裂,就是思維與存在的對立,一種最抽象的對立;要掌握的就是思維與存在的和解。從這時(shí)起,一切哲學(xué)都對這個(gè)統(tǒng)一發(fā)生興趣。”[2](P6)
笛卡爾的心物二元論確立了近代西方哲學(xué)中主客二分的思想格局。斯賓諾莎試圖用實(shí)體一元論取代笛卡爾的心物二元論,以克服主客二元分立,但斯賓諾莎那里的“思想”和“廣延”仍然是分立的。康德試圖以“統(tǒng)覺”實(shí)現(xiàn)先天綜合統(tǒng)一,彌合主觀和客觀之間的鴻溝,但最終未能統(tǒng)一“現(xiàn)象”與“物自體”。費(fèi)希特從主觀的絕對自我出發(fā),通過自我的“設(shè)定”,尋求自我與非我、主體與客體的統(tǒng)一,然而,他用以統(tǒng)一主客體的“自我意識”仍然是“脫離自然的精神”,因而主體還不是實(shí)體。謝林用能動性原則統(tǒng)一自然與精神、客觀世界與主觀世界,以達(dá)到一種絕對同一性,不過這種同一性中缺乏差異和區(qū)分,缺乏必然性和歷史性。黑格爾綜合了斯賓諾莎的實(shí)體、康德的統(tǒng)覺、費(fèi)希特的自我意識、謝林的客觀的主體-客體等概念,提出了作為最高統(tǒng)一體的絕對精神這個(gè)概念,在絕對精神的自我展開(分裂)和重新統(tǒng)一的辯證過程中實(shí)現(xiàn)主體和客體的最終統(tǒng)一。
在絕對精神的發(fā)展過程中,主體與客體的分離和對立是必然的環(huán)節(jié),黑格爾稱之為絕對精神的外化。在邏輯上,絕對精神最初表現(xiàn)為抽象的理念,是永恒而單純的本質(zhì),即自在自為的理念,這些理念實(shí)際上是處于胚胎狀態(tài)的“實(shí)體”,通過辯證邏輯“預(yù)先”展現(xiàn)了絕對精神的展開過程,正如樹木的種子中已經(jīng)包含了根、枝、葉的區(qū)分,但這些成分在種子中只是潛在的,直到種子按照一定的順序開枝發(fā)葉、長成樹木,它們才得到“實(shí)現(xiàn)”。這些以辯證邏輯的方式聯(lián)系起來形成的整體,就是絕對理念,這是黑格爾的邏輯學(xué)研究的內(nèi)容。
絕對理念是絕對精神的“原始形態(tài)”,是“在其自身的”,是抽象的,還沒有“內(nèi)容”,不具有現(xiàn)實(shí)性,它需要將自身現(xiàn)實(shí)化、外在化,也就是說,要在時(shí)間和空間中讓自己成為“現(xiàn)實(shí)的存在”,達(dá)到“定在”。絕對理念將自己現(xiàn)實(shí)化、外在化和特殊化的過程,就是外化。絕對理念外化出的各個(gè)形態(tài)和外化過程遵循辯證法,構(gòu)成絕對精神自我展開的歷史,這個(gè)歷史與辯證邏輯是一致的,這就是“歷史與邏輯的統(tǒng)一”。絕對理念外化的第一個(gè)結(jié)果,是外在化的理念,即自然。相對于抽象的絕對理念,自然作為空間中的定在,是絕對理念的對象化和自我否定。在自然中,精神是他在的和異在的,是不自知的,是沉睡在直接感性東西的外殼里的。作為整體的自然處于外在的必然性之中,沒有自身的歷史。對絕對理念來說,自然是一個(gè)“他者”,因此從絕對理念到自然的外化同時(shí)又是“異化”,自然是自我“異化”的精神。這是黑格爾的自然哲學(xué)研究的內(nèi)容。
在動物有機(jī)體這個(gè)自然的最高階段上,產(chǎn)生了有自我意識的“人”,理念就超出了自然的范圍,打破自己的直接感性東西的外殼,如鳳凰涅槃一樣從自然中涌現(xiàn)出來,這就進(jìn)入絕對精神發(fā)展的第三階段,即“精神”階段。“精神”是自知的理念,是自為存在著和向自在自為狀態(tài)生成著的理念,是正在實(shí)現(xiàn)著和實(shí)現(xiàn)了自我認(rèn)識的理念。這是黑格爾的精神哲學(xué)研究的內(nèi)容。一方面,在“精神”的初級階段的“有限精神”環(huán)節(jié)內(nèi)部,外化仍然在進(jìn)行,即絕對理念在時(shí)間和空間中繼續(xù)展開,進(jìn)一步現(xiàn)實(shí)化,成為時(shí)間和空間中的定在,這就是世界歷史。另一方面,就絕對精神發(fā)展的整個(gè)過程而言,相對于自然,“精神”是理念揚(yáng)棄外在性,從外化了的狀態(tài)回到自身,最終揚(yáng)棄了外化。“精神”發(fā)展的最高階段是絕對知識,此時(shí)絕對精神完全返回到自身,認(rèn)識到自然和“有限精神”都是從自身外化出來的,是與自身相同一的。這種認(rèn)識,與外化或“異化”相對立,可以稱之為內(nèi)化或“同化”。從絕對理念到自然是外化,是否定之否定的第一個(gè)否定,從自然到“精神”是內(nèi)化,是否定之否定的第二個(gè)否定,兩次否定構(gòu)成了從正題到反題再到正題的“正反合”,形成了一個(gè)閉合的圓圈,這是黑格爾的辯證法在最高層次上的應(yīng)用。在整個(gè)外化-內(nèi)化的過程中,絕對理念首先將自身展開為實(shí)體,即“主體是實(shí)體”,再從實(shí)體回歸到自身,即“實(shí)體是主體”,從而揚(yáng)棄了主體與客體的分裂和對立,最終達(dá)到了自身的同一,這是一種經(jīng)過了中介環(huán)節(jié)的同一,包含著差異的同一,用黑格爾的話來說,是同一與非同一的同一。
列寧用以描述事物發(fā)展過程的螺旋式上升過程,可以借用來描繪黑格爾《哲學(xué)全書》展現(xiàn)的絕對精神外化-內(nèi)化過程。精神的發(fā)展過程類似于半徑下小上大的螺旋,如同龍卷風(fēng)一樣。絕對理念外化出的各形態(tài)構(gòu)成了向上盤旋的螺旋,絕對理念是螺旋的軸心。螺旋在橫向上擴(kuò)張,表明了精神的廣度,軸心在縱向上延伸,表明了精神的深度。外化是將縱向的東西(絕對理念)往橫向發(fā)散,內(nèi)化是將橫向發(fā)散的東西(外化各形態(tài))往縱向聚攏。精神的廣度與深度是同步的,隨著螺旋的上升,螺旋的外緣離軸心越來越遠(yuǎn)。黑格爾認(rèn)為:“精神力量的外在表現(xiàn)有多強(qiáng)大,精神力量就有多強(qiáng)大,精神在自身的展開中能自身擴(kuò)展和迷失到怎樣的程度,精神自身就能達(dá)到怎樣的深度。”[3](P15)精神發(fā)展的程度越深,精神的外延就越廣,發(fā)展意義的外延“是一種結(jié)合,發(fā)展的外延愈廣、內(nèi)容愈豐富,則這種結(jié)合也就愈深而有力”[4](P35)。
但是,精神的外延越大,概念與從概念外化出來的實(shí)體的差別就越大,絕對理念的外化形態(tài)離開絕對理念本身越遠(yuǎn),主體與實(shí)體的分離、疏遠(yuǎn)和對立就越大。文化越擴(kuò)張,可以交織在分裂中的生命變化就越多樣,分裂的力量就越強(qiáng)大。[5](P9)換言之,精神的發(fā)展程度越高,絕對理念的外化形態(tài)越復(fù)雜,精神就越難于從千姿百態(tài)的外化形態(tài)返回到自身,即認(rèn)識自身,就要忍受愈發(fā)深重的分離痛苦,即“異化”的程度越高。這樣,從螺旋向軸心的回歸就要走過越發(fā)遙遠(yuǎn)的距離,外化或“異化”的揚(yáng)棄就需要付出越發(fā)艱巨的努力。但是,就絕對精神的整個(gè)發(fā)展過程而言,精神與其實(shí)體的疏離只是暫時(shí)的、階段性的,而外化或“異化”的揚(yáng)棄是必然的,精神終歸要回歸到自身,自我與對象、主體與客體、普遍與特殊等各種對立最終會統(tǒng)一,同一性會取代非同一性。“抽象地來看,普遍性、特殊性、個(gè)別性就是同一、差別和根據(jù)那樣的東西。”[6](P300)在絕對精神發(fā)展的最高階段,精神歷盡艱辛回歸到自身,克服了“異化”,彌合了分離,最終實(shí)現(xiàn)了自身同一性。
二、海德格爾:作為統(tǒng)一性的同一性
海德格爾對思維與存在同一性問題的興趣貫穿了他的研究生涯。在《康德的存在論題》一文中,他指出:“存在與思想,在這個(gè)‘與’中隱含著迄今為止的哲學(xué)以及今天的思想的最值得思的東西。”[7](P34)他出版于1957年的著作《同一與差異》主要討論的就是思維與存在同一性問題,該書包括兩篇文章,第一篇是《同一律》,是海德格爾對思維與存在同一性問題的正面表述;第二篇是《形而上學(xué)的存在-神-邏輯學(xué)機(jī)制》,主要是海德格爾對黑格爾的同一性理論的反思。
《同一律》一文開始于對同一律這個(gè)基本定律的討論。海德格爾認(rèn)為,同一律的流俗公式是A=A。這個(gè)公式講的是等同性,但它并未說出同一性,反而掩蓋了同一律真正要說出的東西,用等同性掩蓋了同一性。同一根本不是相同,因?yàn)橥恍灾须[含了差異性。在海德格爾看來,只有到了黑格爾,同一性才獲得了其在形而上學(xué)中的最終的也是最完備的表述,因?yàn)橹皇菑暮诟駹栭_始,才真正區(qū)分了同一性與等同性。
具體到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問題上,海德格爾首先把同一性放到兩個(gè)不同的東西“之間”來考察,賦予了同一性以全新的意義。接下來他通過人與存在的關(guān)系來解讀思維與存在的關(guān)系,并進(jìn)一步用人與存在的共屬性(統(tǒng)一性)來界定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思維與存在的共屬與存在者的自身同一之所以不同,關(guān)鍵在于思維與存在中的那個(gè)“與”(und)。如果說“mit”標(biāo)志著自身同一的話,“und”則標(biāo)志著思維與存在“之間”的同一。這個(gè)“與”能起到聚集作用,能把有區(qū)別的東西聚集成為一體,從而把“同一”與“共屬”聯(lián)系起來。海德格爾認(rèn)為,應(yīng)該通過“屬”——相互歸屬——來規(guī)定“共”。人和存在之本質(zhì)必須通過二者的“之間”,通過二者的“緣域”顯現(xiàn),如果在討論人和存在的共屬之前一定要討論清楚什么是人、什么是存在,則又落入海德格爾所力圖克服的表象性思維。正是這種表象性思維,導(dǎo)致了把所有存在者分門別類擺放的構(gòu)架(Gestell)的出現(xiàn)。并非先有存在和人的確定本質(zhì),再有存在和人的同一性,而是存在和人相關(guān)涉、相歸屬才給出存在,當(dāng)然,也給出人的本質(zhì)。
這樣,海德格爾就把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問題轉(zhuǎn)化為人與存在的關(guān)系問題,而海德格爾對人與存在的關(guān)系的表述也經(jīng)歷了一個(gè)漸變的思想過程。他在1935年的《形而上學(xué)導(dǎo)論》中指出,人與存在的共屬是在人與存在的激烈對抗關(guān)系中的共屬。在這種對抗中,人失去了自己的本位(Ort),變得無家可歸。為了克服這種無家可歸的狀態(tài),為人找回“家”,海德格爾后來陸續(xù)探討人與存在在藝術(shù)的共屬、在棲居中的共屬以及在道說(語言)中的共屬。只有在道說中,人與存在才相互歸屬并共屬于道說,才真正達(dá)到了同一。因此,語言是存在的家,也是所有人即“終有一死者”的家。
從“人與存在在對抗中的共屬”到“人與存在在道說中的共屬”,這個(gè)漸變過程展現(xiàn)出海德格爾這個(gè)時(shí)期思想發(fā)展的四條線索:一是人的“家”經(jīng)歷著從藝術(shù)到“終有一死者所筑造的居所”到“作為道說的道說”到發(fā)生的變化;二是人的角色經(jīng)歷著從強(qiáng)力行事者到“藝術(shù)作品的創(chuàng)作者和葆真者”到棲居者到道說者的變化,人在這個(gè)過程中逐漸“退隱”,人從妄圖成為“存在之主人”的此在逐漸轉(zhuǎn)變?yōu)榇嬖诘目醋o(hù)者和發(fā)生的道說者;三是“空間”維度的地位經(jīng)歷了起伏變化,在《存在與時(shí)間》中,此在的空間性被歸結(jié)為時(shí)間性。在《藝術(shù)作品的本源》中,“空間”作為一個(gè)新的維度被建立,其重要性甚至不亞于時(shí)間,在對棲居和道說的討論中,“空間”與“時(shí)間”在天空、大地、諸神、終有一死者的四重聚集中具有同等重要性;四是對存在的言說方式經(jīng)歷了從“此在隱去,存在者整體凸顯”到“存在者整體隱去,存在本身凸顯”到“存在本身隱去,發(fā)生凸顯”的變化。
經(jīng)歷了這些變化之后,海德格爾思考的重點(diǎn)轉(zhuǎn)移到“發(fā)生”(Ereignis)上。人與存在在道說中的共屬是“人與存在在‘發(fā)生’中的共屬”的實(shí)現(xiàn)(Austrag)。人與存在的共屬最終被歸結(jié)為“發(fā)生”的運(yùn)作。“發(fā)生”讓人與存在共屬一體。人與存在相互歸屬并且共屬于發(fā)生。這種讓共屬聚集人與存在,給出二者的區(qū)分并在聚集中保持二者的區(qū)分。這種區(qū)分的聚集就表現(xiàn)為人與存在的同一性。最終,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是發(fā)生的二重性運(yùn)作的結(jié)果,這種同一性的本質(zhì)是發(fā)生的一個(gè)所有物。在海德格爾思想的最后階段,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最終落腳在人與存在在發(fā)生中的共屬性。而共屬性實(shí)際上就是一種統(tǒng)一性。這就是說,在海德格爾這里,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最終是人與存在在綿綿不絕的“發(fā)生”中的統(tǒng)一性。
可見,在思維與存在的關(guān)系上,海德格爾與黑格爾一樣,認(rèn)為思維與存在是同一的,而且這種同一是一種經(jīng)過了中介的、不同于“等同”的同一。用海德格爾的話來說,這種同一種“有一種‘與’(mit)的關(guān)系,有一種中介、一種關(guān)聯(lián)、一種綜合:在一個(gè)統(tǒng)一性中的統(tǒng)一”[7](P6)。不過,在對思維與存在同一性的理解上,海德格爾并非和黑格爾完全一致,主要差異表現(xiàn)在五個(gè)方面。
第一,相對黑格爾的思維與存在同一性更多地表現(xiàn)為“同”,海德格爾那里的思維與存在同一性更多地表現(xiàn)為“統(tǒng)”。具體來說,就是統(tǒng)一性、共屬性。而在客觀唯心主義者黑格爾看來,思維與存在同一性更多的是存在“同一”于思維,也就是存在在某種意義上“屬”于思維。這種同一性有一種居高臨下、不容否定的意味,能夠?qū)⒁磺胁町惗蓟肽菬o所不能的同一性中。
第二,相對黑格爾那種“強(qiáng)勢”的思維與存在同一性,海德格爾的思維與存在同一性看起來更為“溫和”。當(dāng)然,在他早期作品中,“人”與存在處在激烈的對抗中,此時(shí)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是一種“緊繃著”的同一性。隨著海德格爾思想的發(fā)展,“人”在后來的作品中不斷“退讓”,而“存在”也越發(fā)顯得“寬厚包容”。這種“后退”,使得人與存在之間出現(xiàn)一塊“林中空地”,也彰顯人的有限性。而黑格爾不承認(rèn)人和思維的有限性,就此而言,海德格爾在某種意義上又返回到康德。
第三,相對于黑格爾對辯證法的倚重,海德格爾對辯證法的使用極為慎重,在他那里辯證法有時(shí)甚至還有消極意義。不可否認(rèn),海德格爾的很多論述頗具黑格爾辯證法的味道,但海格德爾本人對黑格爾辯證法的評價(jià)并不高。例如,在《黑格爾的經(jīng)驗(yàn)概念》一文中,海德格爾將《精神現(xiàn)象學(xué)》導(dǎo)論中的認(rèn)識論和本體論的辯證法,以及體現(xiàn)為“意識的經(jīng)驗(yàn)科學(xué)”的概念的歷史進(jìn)展的辯證法,解讀為某種“在場的形而上學(xué)”,視為他自己的“基礎(chǔ)存在論”的一種不成熟的表達(dá)。在該文中,海德格爾甚至還說:“關(guān)于辯證法的探討?yīng)q如人們根據(jù)靜止的污水來解釋噴涌的源泉。”[8](P168)
第四,相對于時(shí)間在黑格爾那里所處的“過渡性”地位,海德格爾給予了時(shí)間以“基礎(chǔ)性”地位。在黑格爾那里,只有精神世界才是無限的、永恒的、超出時(shí)間的,現(xiàn)存的有限世界是永恒的絕對精神的外化。只有在外化的過程中,時(shí)間才“出場”,而外化最終要克服“時(shí)間性”,從外化的有限形態(tài)“回歸”到無限而永恒的精神世界。對海德格爾來說,時(shí)間是存在的本質(zhì),時(shí)間也標(biāo)記著人的有限性,時(shí)間成就了存在與人的“共屬”,換句話說,時(shí)間造就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沒有時(shí)間,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無從談起。
第五,相對于黑格爾那里同一性之下差異的豐富性,海德格爾的同一性中“虛化”了差異。悖謬的是,盡管黑格爾的同一性顯得有些“咄咄逼人”,似乎要吞噬差異的多樣性,但黑格爾卻不厭其煩地表述精神外化諸形態(tài)的差異,以至于恩格斯把黑格爾的哲學(xué)體系稱為保藏著無數(shù)珍寶的大廈。反觀海德格爾,盡管他一再強(qiáng)調(diào)同一性中的差異性,但他對最終給出思維與存在同一性的那個(gè)“發(fā)生”(Ereignis)卻語焉不詳,從而使這個(gè)概念“高深莫測”“玄之又玄”,差異在其中反倒“虛化”了,隱沒在深邃幽暗的同一性之中,因此,后期海德格爾的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概念有些類似謝林的絕對同一性概念,用黑格爾的話來說是“黑夜觀牛,一切皆黑”。
三、阿多諾:貫穿同一性的“非同一性”
黑格爾和海德格爾的同一性思想在阿多諾這里受到了最猛烈的批判。阿多諾把同一性問題作為自己的中心課題,他的《否定辯證法》圍繞著主體與客體、思維與存在之間的關(guān)系,在對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傳統(tǒng)形而上學(xué)同一性哲學(xué)、以海德格爾為代表的存在論同一性哲學(xué)的批判中,建構(gòu)起其非同一性的哲學(xué)主張。阿多諾認(rèn)為,黑格爾的思辨同一性理論展現(xiàn)了一種“概念帝國主義”,主要表現(xiàn)在四個(gè)方面。一是普遍對特殊的壓制。阿多諾指出,黑格爾和柏拉圖一樣,把非概念物、個(gè)別的東西和特殊的東西排除在哲學(xué)主題之外。但如果概念超出自身的抽象范圍,強(qiáng)行把非概念物“納入”自身,就會造成普遍性對特殊性的壓制。二是量對質(zhì)的吞噬。阿多諾認(rèn)為,客體的質(zhì)的要素,即非概念性、個(gè)別性和特殊性,構(gòu)成哲學(xué)的主題。但自柏拉圖以來,它們總被當(dāng)成無意義的東西打發(fā)掉,黑格爾稱其為“惰性的實(shí)存”。阿多諾認(rèn)為,把質(zhì)變?yōu)榱坎皇鞘加诤诟駹?而是來源于自笛卡爾以來一切科學(xué)的定量化傾向。三是“一”對“多”的統(tǒng)治。這種統(tǒng)治既與自古希臘以來對第一原則的尊崇有關(guān),又與近代盛行起來的量對質(zhì)的優(yōu)先性有關(guān)。四是形式對內(nèi)容的特權(quán)。阿多諾認(rèn)為,雖然黑格爾的辯證法體系力圖建立一種“內(nèi)容”的邏輯,但黑格爾的哲學(xué)體系最終還是排除了內(nèi)容,把純形式的絕對精神當(dāng)成了最高者。以上四項(xiàng)概念帝國主義的“罪行”,可以歸納為一個(gè)總的“罪名”:同一性強(qiáng)制,或者說全面的同一化。在阿多諾看來,黑格爾辯證法中雖然包含了否定,但仍然是指向肯定的否定,因此黑格爾那里的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是貫穿非同一性的同一性,是強(qiáng)制同一性。
同樣,阿多諾認(rèn)為海德格爾的存在本體論雖然有別于以前的各種形而上學(xué)理論,但仍然樹立了一個(gè)最高的自足者和自我同一者——存在,實(shí)質(zhì)上仍是一種隱秘的同一性理論。在批判同一性思維的基礎(chǔ)上,阿多諾提出自己的否定辯證法,主張非同一性和徹底的否定,要求為非概念物、非同一物、特殊者、個(gè)別者、他者等被邊緣化者正名,并用“星叢”“力場”等隱喻來描述主客體之間“和平”的理想關(guān)系,這種關(guān)系是“反體系”“非同一”“去中心”的,用不被同一性控制的事物的觀念,來替代同一性原則,替代處于最頂層的概念的至上性。[9](序言P2)因此,在阿多諾那里,思想與存在是異質(zhì)的,是非同一的,二者之間“不可通約”,但又并非截然不同,毫無共同之處。在阿多諾看來,思想與存在之間的非同一性是貫穿于同一性之中的非同一性。
阿多諾的非同一哲學(xué)和否定辯證法對同一性思維的批判,對異質(zhì)性、個(gè)體性、特殊性、差異性等非同一性的強(qiáng)調(diào),是對傳統(tǒng)辯證法的積極的革新,他剔除傳統(tǒng)辯證法中的同一性、整體性等觀念,撕裂了傳統(tǒng)辯證法的核心內(nèi)容,他否認(rèn)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拆除了西方形而上學(xué)的根基,因而構(gòu)成了傳統(tǒng)辯證法、形而上學(xué)乃至根本思維方式的革命性變革。他的非同一哲學(xué)和否定辯證法體現(xiàn)了一種理論上的不妥協(xié),在西方現(xiàn)代性思想內(nèi)部以一種特別的方式捍衛(wèi)現(xiàn)代性,反對時(shí)髦哲學(xué)思潮,決不屈從于所謂的主流,決不媚俗。就這一點(diǎn)而言,阿多諾繼承了馬克思的批判精神。除了哲學(xué)層面的批判,阿多諾還基于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的批判,經(jīng)由對資本主義的商品交換同一性原則的批判,轉(zhuǎn)向?qū)ξ幕捌湟庾R形態(tài)的批判,揭示了當(dāng)代西方主流文化及其意識形態(tài)對人類自由的壓抑。因此,阿多諾“處在了代表那個(gè)時(shí)代的許多最有創(chuàng)造性思想潮流的強(qiáng)烈的非總體化力量的動力型立場中的關(guān)節(jié)點(diǎn)上”[10](P254)。
但是,正如哈貝馬斯指出的那樣,西方馬克思主義和批判理論由于在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理論傳統(tǒng)之中摻入了韋伯合理性理論的內(nèi)容,因此不可避免地偏離了馬克思的邏輯。阿多諾最為徹底地貫徹了這一理論邏輯,從而走向了一種無為的寂靜主義。可見,阿多諾的非同一哲學(xué)和否定辯證法更多的是一味“解藥”,它或許能夠幫我們祛除思想中的一些重大的“隱疾”,但我們不能依靠它使思想“成長”。或許因?yàn)槠涑坝谒幍臅r(shí)代,它的作用以及它在西方思想史中的意義,還要等到未來再進(jìn)一步挖掘。
阿多諾的非同一哲學(xué)對同一性、總體性的批判,對非同一性、特殊性、個(gè)別性的強(qiáng)調(diào),是20世紀(jì)下半葉西方思想界中開始出現(xiàn)的一種普遍傾向的先聲。這個(gè)傾向可以稱之為后現(xiàn)代主義的異質(zhì)化傾向,在阿多諾之后的諸多前沿思想家身上得到了體現(xiàn)。德里達(dá)提出解構(gòu)主義,反對邏輯中心主義、同一性和確定性,要求拆除結(jié)構(gòu),試圖消解一切他稱之為在場形而上學(xué)的固定的東西,以至于瓦解形而上學(xué)。福柯反對自我編造的同一性,要求消除同一性的幻象。利奧塔提倡微觀敘事,反對總體性和宏大敘事,“向同一性開戰(zhàn)”。詹姆遜認(rèn)為西方當(dāng)代社會文化的每個(gè)方面都“齊一化”成了商品,人喪失了自主性,被消費(fèi)行為所主宰。在德勒茲看來,各種社會矛盾不可能有最終的解決方案,我們能做的只是斗爭中的“讓步”,他將克服絕望的希望寄托在精神分裂者、邊緣人、游牧民等主體上。馬丁·杰伊指出,阿多諾的《否定辯證法》等著作預(yù)示了后現(xiàn)代的一些要素。[11](P13)
阿多諾與后現(xiàn)代主義之間的相似性,并不意味著阿多諾要主張一種類似今天后現(xiàn)代思潮般的相對主義。他明確反對哲學(xué)理論上的相對主義。否定的辯證法既與相對主義嚴(yán)格對立,也與絕對主義對立。阿多諾指出,過去對相對主義的批判還只是偏重于形式,而沒能觸及它的思維結(jié)構(gòu),現(xiàn)在,應(yīng)該旗幟鮮明地反對相對主義。阿多諾認(rèn)為,相對主義起初是資產(chǎn)階級個(gè)人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這種個(gè)人主義把個(gè)人意識當(dāng)作終極的,使一切個(gè)人的意見都獲得了平等權(quán)利,仿佛其中根本不存在真理的標(biāo)準(zhǔn)。可是,這種看起來平等和民主的觀念實(shí)際上是一種虛偽的假貧民主義。在阿多諾看來,相對主義的這種激進(jìn)的批判性外表是抽象的,因?yàn)槌橄螅艑?dǎo)致從外部來判斷一切認(rèn)識的相對性;同時(shí)相對主義又是瑣碎的,因?yàn)樗环矫嬲J(rèn)為事物是隨意的和偶然的,另一方面認(rèn)為它們是不可還原的。阿多諾反對哲學(xué)理論上的相對主義,實(shí)際上也就承認(rèn)了否定的辯證法中并非沒有任何穩(wěn)固的東西,只是“它不再賦予這種東西以第一性”。阿多諾尊重物質(zhì)、尊重主體、尊重概念,甚至尊重理性和同一性,但不再將這任何一種東西變?yōu)橹粮邿o上者。
由此看來,能夠被阿多諾認(rèn)為同道的思想可謂少之又少。《否定辯證法》的英譯者阿什頓在該書譯序中指出,阿多諾幾乎與哲學(xué)史上的所有大家為敵,“這些靶子覆蓋的范圍之大給人以深刻的印象。阿多爾諾既未放過19世紀(jì)的唯心主義者,也未放過實(shí)證主義者,而且還猛烈打擊了20世紀(jì)的新本體論者、直覺主義者和存在主義者,秘而不宣地駁斥了20世紀(jì)馬克思主義的既成體系”[9](英譯者按語P3)。對于“處處樹敵”將會帶來的受到四面圍攻的境況,阿多諾自己也有心理準(zhǔn)備,在《否定辯證法》序言的最后部分,阿多諾這樣說:“作者準(zhǔn)備承受《否定的辯證法》給他招來的攻擊。他不覺得有任何怨仇,并不妒忌兩個(gè)陣營中的何種人的喜悅,盡管這些人斷定自己一直都了解《否定的辯證法》,斷定作者正在懺悔。”[9](序言P2-3)
在1971年出版的《馬克思主義與形式》一書中,詹姆遜仍然認(rèn)為阿多諾“消極防守”[12](P46),對未來過于悲觀。近20年后,詹姆遜對阿多諾的態(tài)度出現(xiàn)了反轉(zhuǎn),在1990年出版的 《晚期馬克思主義——阿多諾,或辯證法的韌性》一書中,詹姆遜稱贊《否定辯證法》為“批判理論后期綱領(lǐng)、90年代辯證法楷模”[13](P5)。他認(rèn)為,阿多諾援引馬克思對費(fèi)爾巴哈的批判,指明了資產(chǎn)階級哲學(xué)的核心秘密并不在于其邏輯構(gòu)造,而在于它無意識地進(jìn)行翻譯的社會生產(chǎn)過程。詹姆遜指出:“阿多諾對‘總體體系’的預(yù)見,最終不折不扣地以出人意料的形式變成了現(xiàn)實(shí)……阿多諾的馬克思主義雖然在以往的歲月中無甚裨益,卻可能正是我們今天所需要的東西。”[13](P5)德勒茲也半認(rèn)真地說,阿多諾是因?yàn)闀r(shí)機(jī)不到,暫時(shí)懸置了革命目標(biāo)。等到大家走投無路時(shí),自然會破譯阿多諾的密碼,將火種傳遞下去。[14](P175)馬丁·杰伊則認(rèn)為,阿多諾是一只被扔進(jìn)大海,或許可能被再一次撿回來的漂流瓶。[10](P255)
四、結(jié) 語
不同解答者展現(xiàn)的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是充滿了差異的“同一”。如前所述,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在黑格爾那里是貫穿著同一性的同一性,在海德格爾那里是作為統(tǒng)一性的同一性,而阿多諾直接否定了這種同一性而強(qiáng)調(diào)思維與存在的非同一性,但阿多諾本人也并未徹底走出同一性思維,因?yàn)閳?jiān)執(zhí)于同一性與非同一性的區(qū)分,本身就是一種同一性的思維習(xí)慣在起作用。從同一性到非同一性的轉(zhuǎn)變,從特定角度反映現(xiàn)代性思想向后現(xiàn)代性思想的過渡。不過,直到今天,這個(gè)問題也并未有一個(gè)定論式的解答。
與西方不同,古代東方思想中沒有主體、客體這樣的哲學(xué)范疇,并不強(qiáng)調(diào)“本質(zhì)”,也不強(qiáng)調(diào)判斷中主語與謂語中嚴(yán)格的邏輯同一關(guān)系(中國古代哲人很少用系動詞“是”來連接主語和謂語,而更多地使用“有”、“無”這樣的詞),因此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問題在中國哲學(xué)中并沒有成為一個(gè)真正的問題,也許這可能使中國古代哲學(xué)的探討錯(cuò)失了某些重要領(lǐng)域,甚至可能表明在思維方式上中國古代傳統(tǒng)智慧與自然科學(xué)對嚴(yán)格性的要求之間的隔膜。但反過來說,中國古代思想家不執(zhí)著于在“是”與“不是”之間做出區(qū)分,不執(zhí)著于做出非此即彼的判斷,既走出了同一性思維,也走出了“非同一性”思維。這種東方思想中的“非”同一性思維或許在更高層面上契合了處理復(fù)雜問題的一種“混沌思維”“模糊思維”,從而與西方哲學(xué)以一種相對直白的方式揭示出來的辯證法之間有著某種會通的可能。西方思想與東方智慧的結(jié)合,或許能為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這個(gè)古老的命題開出一片新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