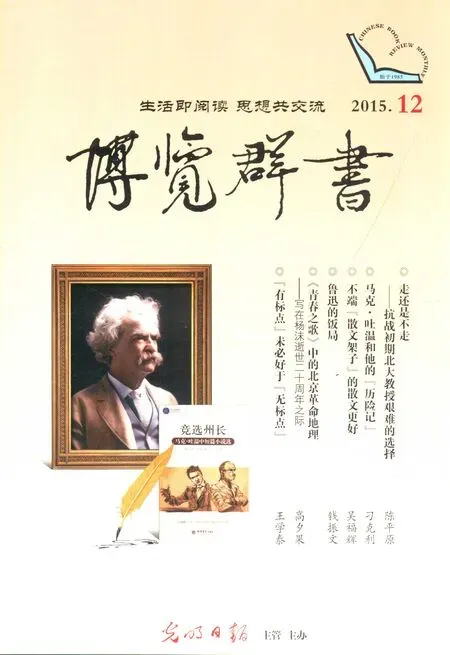西施的下場有兩個
周巖壁
在理想國里,美女是怒放的鮮花,芳香,嬌嫩,永不凋零;在現實中,美女和我們常人一樣,有生,也有老、病、死,有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時候。于是,在歷史上,這個地方如同沙場,理想與現實旅進旅退、此起彼伏、交互作用,美女的下場總是莫衷一是,眾說紛紜,沸沸揚揚,永無定論。西施就是這樣。
關于這位美女的本事,我們多少都知道一些,史書上雖有記載,但詰屈難讀,不妨看詩仙——王安石抱怨李白“詩詞十句九句言婦人、酒!”(《冷齋夜話》卷五)——的描寫:“西施越溪女,出自苧蘿山。秀色掩今古,荷花羞玉顏。浣紗弄碧水,沉吟碧云間。勾踐征絕艷,揚蛾入吳關。提攜館娃宮,杳渺詎可攀。一破夫差國,千秋竟不還。”(《全唐詩》卷181李白《西施》)說西施本是苧蘿山里一個浣紗的村姑,越王勾踐出于滅吳的戰略考慮,把西施作為尤物獻給吳王夫差,誘他沉迷聲色,不治國事,終致吳國敗亡。這是沒有異議的;但關于這位美人的下場,說法就不一了。太白只是說,吳破后,西施沒再回越地。曾被貶謫嶺南的宋之問則說:西施“一行霸勾踐,再笑傾夫差。一朝還舊都,靚妝尋若耶;鳥驚入松網,魚畏沉荷花”。(《唐詩品匯》五古卷二宋之問《浣紗篇》)西施是衣錦還鄉!大概也有根據,宋之問曾到會稽游覽過,謁過禹廟、游過禹穴、泛過鑒湖。(《全唐詩》卷52/53)
晚唐皮日休說:“半夜娃宮作戰場,血腥猶雜宴時香。西施不及燒殘蠟,猶為君王泣數行。”“響屧廊中金玉步,采蘋山上綺羅身。不知水葬今何處,溪月彎彎欲效顰。”(《全唐詩》卷615皮日休《館娃宮懷古》之三、五)埋怨在夫差面前,國破家亡身將死,這個美人卿卿我我蝴蝶雙雙多年,卻一滴同情的眼淚都沒有!但西施還是(被)淹死了。和皮子唱和陸龜蒙卻溫和一些,沒有那么苛刻,說:“三千雖衣水犀珠,半夜夫差國暗屠。猶有八人皆二八,獨教西子占亡吳。”“寶襪香綦碎曉塵,亂兵誰惜似花人?伯勞應是精靈使,猶向殘陽泣暮春。”(《全唐詩》卷628陸龜蒙《和襲美館娃宮懷古》之一、五)慨嘆西施死于亂兵。和皮日休一樣,李商隱大概也持此觀點,西施在吳亡后淹死,所以在《景陽井》中說:“腸斷吳王宮外水,濁泥猶得葬西施。”(《全唐詩》卷541)
其實,西施在吳亡后就(被)淹死了,這一說法大有來頭。墨子說:“西施之沈(沉),其美也。”(《墨子·親士》)意思是,西施所以被淹死,因為她是美人!孫詒讓在《墨子閑詁》中為此說張目,認為“墨子書記當時事,必有據”。此說影響遠大。在我們上面征引的唐代五位詩人的詩中,宋之問持西施滅吳后衣錦還鄉。皮日休和李商隱都說是淹死。李白和陸龜蒙雖沒有明確表態,但和西施吳亡后淹死說并不捍格。就是說,在唐代或唐詩里,西施在吳滅后淹死,是個多數人同意的說法。
此外還有一個說法,西施在吳滅后,“隨范蠡泛舟五湖而去”。(《香艷叢書》第三集卷三楊淮《古艷樂府·白苧歌·序》)此說在唐詩里也有反映。杜牧《杜秋娘詩》:“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全唐詩》卷520)鴟夷子皮是范蠡的號。(《史記·勾踐世家》)此說在宋詞里蔚為大觀。柳永《瑞鷓鴣》:“西子方來、越相功成去,千里滄江一葉舟。”蘇軾《水龍吟》:“空江、月明千里。五湖聞道,扁舟歸去,仍攜西子。”杜旟《摸魚兒·湖上》:“待學取鴟夷,仍攜西子,來動五湖興。”張孝祥《水調歌頭·垂虹亭》:“欲酹鴟夷西子,未辦當年功業,空擊五湖船。”陳人杰《沁園春·鐃鏡游吳中》:“過鴟夷西子,曾游處所。” 楊冠卿《賀新郎》:“西子五湖歸去后,泛仙舟、尚許尋盟否。風袂逐,片帆舉。” 辛棄疾《摸魚兒·觀潮上葉丞相》:“白馬素車東去。堪恨處,人道是、子胥冤憤終千古。功名自誤。謾教得陶朱,五湖西子,一舸弄煙雨。”
耐人尋味的是,南宋的道學家也認同西子范蠡泛舟五湖的說法。但他們意在維護圣賢,不是憐香惜玉。羅大經說:
范蠡霸越之后,脫屣富貴,扁舟五湖,可謂一塵不染矣。然猶挾西施以行,蠡非悅其色也,蓋懼其復以蠱吳者而蠱越,則越不可保矣。于是挾之以行,以絕越之禍基,是蠡雖去越,未嘗忘越也。”(《鶴林玉露》乙編卷三)
由此我們知道,西施原來是危險的罪犯,為避免她再犯,終身被監禁于五湖煙水,小牢子是范蠡,義工。對范蠡的良苦用心,羅大經言之鑿鑿,發覆于千載之下,雖然令人笑來,卻不失可愛。至少也沒有太煞風景。明代楊慎則不然,說是見《吳越春秋》逸篇有“吳亡后,越浮西施于江,令隨鴟夷以終”的話。楊慎考證:“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沉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丹鉛總錄》卷十三)似是而非。到底是誰來為子胥報仇?越是勝國,吳是敗國,子胥是吳國大臣,被夫差賜死。吳人沒資格、沒能力來為子胥報仇。如果西施滅吳有功,越國應該獎賞她,而不是明詔大號地以給越國仇敵子胥報仇而淹死她。所以,楊慎的說法不能成立。
無獨有偶,還有一位明人要致西子于死地。馮夢龍說:勾踐班師回越,攜西施以歸。勾踐夫人潛使人引出西子,負以大石,沉于江中,曰:“此亡國之物,留之何為!”(《東周列國志》第83回)明確把勾踐的夫人定為致死西施的罪魁禍首。這是前所未有的。作為妻子,從妻妾斗爭的角度看,這大老婆心狠手辣,是妒婦。作為王后,從國家政治健康的層面看,她是要江山,不要美人,是揮淚斬馬謖。這后一說法合理性就比楊慎強,雖然有點煞風景。
雖有楊慎、馮夢龍之類的不同意見,但明代關于西施的下落,還是沿襲宋代,以范蠡西子泛舟五湖為主調。而且在梁辰魚《浣紗記》傳奇中定格。傳奇中,西施是范蠡的未婚妻,為實現滅吳計劃,西施在范蠡勸說下,同意入吳宮,并把當年定情物溪紗一分為二,各留一半,以志不忘。吳亡后,勾踐拜謝西施。范蠡與西施功成不受賞,一起泛舟五湖,云水生涯,終成眷屬。(《六十種曲》第一冊)
刪繁就簡地說,西施的下場有兩個:一個是吳亡后,被作為禍害而處死,這大概也是現實的結局;一個是和意中人一起,泛舟五湖,看霧卷云舒,這是個理想的結局。我們更愿意相信這后一個結局,滿足普遍對大團圓的渴望。曹鄴說:“常聞詩人語,西子不宜老!”(《全唐詩》卷592《登岳陽樓》)西子不但不宜老,而且也不老,始終是原來的嬌俏模樣,經常在詩文里浣紗、泛舟,不經意地裝點我們從書頁打開的窗口瞭望下的風景,使之成為人文的景觀。
(作者系鄭州師范學院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