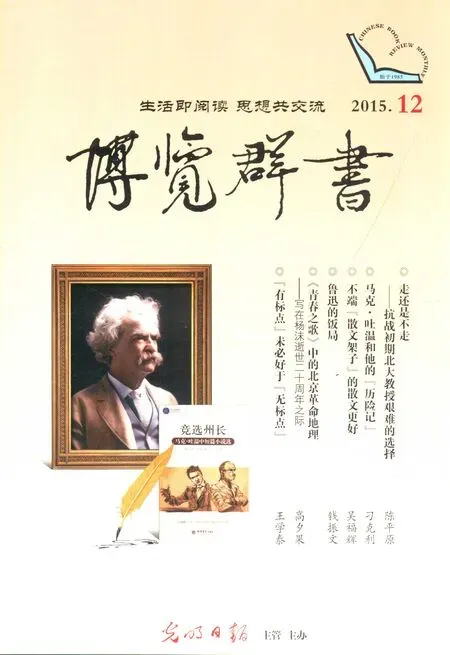《四個杰出科學家如何改變世界》讀后
在人類歷史上,19世紀可謂日新月異,人文蔚興,科學發展突飛猛進。1873年,英國時任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驚訝地說:
這五十年的時間發生了多少事情——我要說的是,在人類歷史中,這是前所未有的非凡時代。我所說的并非帝國的興起衰落,朝代的更替,或是政府的建立。我所說的是科學的革命,這些革命的影響遠勝過任何政治事件,這些革命改變了人類的地位和前景,其作用是史上所有的征服、所有的法典、所有的立法者都無法比擬的。
這個改變人類地位與前景的非凡時代是如何出現的?是什么因素觸發如此空前巨變?它又是如何影響了人類歷史的進程?從那些卓越的社會潮流引領者身上我們可以得到哪些啟示?
紐約圣約翰大學科學史學家、維多利亞時期科學與文化學者勞拉·J·斯奈德的《哲學早餐俱樂部:四個杰出科學家如何改變世界》以歷史事件與傳記的形式,生動地展示了歷史巨變的緣起與過程,揭示了事件背后的社會背景、時代潮流與引發巨變的深層原因。
成就非凡時代
大約在1812年至1813年兩年間,還在劍橋大學讀書的威廉·休厄爾、查爾斯·巴貝奇、約翰·赫歇爾和理查德·瓊斯四個出身、專業、性情各異的大學生走在了一起。每個周日的上午,他們聚在一起,討論培根思想并以為指導,審視科學研究現狀,從科學家職業、研究方法、學術研究的目的與抱負等方面,提出自己的規劃。
他們看來,新的科學人士獲取知識,不應該像螞蟻與蜘蛛那樣,而應向蜜蜂學習。螞蟻只是知識的搬運工,蜘蛛只吞吐自己的東西;如同蜜蜂采得百花釀出甜美的蜜,科學人士應該觀察世界,對觀察結果分析推理,創造出新的科學理論;知識應該開花結果,有助于改變人們的生活條件。科學應該是一種受人尊重的職業,理應得到國家與社會基金的支持,而非一種興趣愛好,休閑之余的零敲碎打。科學研究應該加強聯系,制定學科規劃。一幅現代科學的藍圖在他們熱烈的討論中呼之欲出。
日后,雖然他們走上不同的職業與研究領域,經歷了迥異的悲歡離合,然而他們恪守當初確定的宗旨,走出生命的低谷,成就不凡:威廉·休厄爾成為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院長,在多個領域卓有成就,為維多利亞時代科學界權威;查爾斯·巴貝奇成為著名數學家,科學管理的先驅,世界上第一臺計算機的發明者;約翰·赫歇爾是那個時代最有聲望的天文學家,攝影技術的發明者之一,是杰出的數學家、化學家和植物學家;理查德·瓊斯是卓越的數學家,在他的影響下,新興學科政治經濟學獲得了認可。他們的成就涉及諸多科學領域,如水利、教育、化學、機械學、政治經濟學、統計學、天文學、植物學、計算機、編程、繪圖、潮汐學、地質學、地磁學、攝影、翻譯、密碼、探討外星生命、生命起源、科學和宗教關系等,有力地推動了這些領域的科學發展,波瀾壯闊的社會變革由此發生。
單就職業命名來說,科學家一詞即是威廉·休厄爾的命名。當時,從事科學的人被稱為科學人士或者自然哲學家。在1833年6月24日英國科學促進協會——該協會的成立也是在四人影響下成立的,他們參與其中——第三次大會上,大名鼎鼎的詩人柯勒律治尖銳地質疑自然哲學家的稱謂,休厄爾即刻從藝術家的命名法推演出科學家的術語。自此,科學家真正成為一種職業稱謂。不僅僅是科學家命名,事實上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們的科學研究實踐、科研成果,“科學和科學家才開始像那么一回事,并最終有了今天的樣子”。這真是人類史上讓人難以置信的奇跡。
首先,在19世紀初歐洲,科學家很有可能是閑暇時光搜集甲蟲的鄉村牧師,或者在自己出資興建的實驗室里的紳士,甚至是富人手下的差役。科學活動摒棄女性局限于男性活動的同時卻沒有一條職業界限,融匯摻雜于諸多社會活動之中。不同的人士都可以就科學問題發表高見,如柯勒律治就發表過論述科學的文章。1833年科學家術語出現之后,詩人談論科學已經罕見。科學漸漸成為一個專門的領域。現代科學制度也已建立:專業協會只接納科研人員、研究基金,培養年輕科學研究者的大學實驗室與大學。
其次,經過四人的努力,科學方法成為經常談論的話題,最終培根的歸納法成為科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反省自己的研究方法,不可非隨意為之,科研自覺性成為科學家的基本素養。
第三,科學的目的與功能發生巨變。總體上而言19世紀初乃至以前的歐洲科學研究動機雖然不一,但總體上無非為了個人榮譽,國王或者帝國的榮譽,或者是推動“純粹的知識”。在四位杰出科學家的努力引領下,到了19世紀末葉,科學家的職責與義務已經成為常識,從某種意義上講,科學家被視為肩負公共服務的職責。自然科學的方法能夠而且應該用以理解并解決社會所面臨的問題成為普遍的認識,成為現代科學研究的核心。
第四,把最新的數學方法引入物理學研究,注重精確的測量與計算。巴貝奇、赫歇爾建立了分析學學會,并得到了休厄爾的支持。他們認為科學需要準確的測量與運算,科學本身,更重要的是科學運用,需要準確的觀察、準確的測量與準確的計算。數學迄今已經成為科學研究的基本工具,甚至滲透到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在古典文學研究中,統計學方法也占有一席之地。
正如該書序言中所描繪的:
從19世紀20年代到19世紀70年代——從他們熱忱地開始改變科學到他們離開人世之際——爆發了一系列耀眼的科學成就。這一時代見證了攝影、計算機、各種現代電氣設備的誕生,見證了蒸汽機的出世,見證了鐵路系統的開創。在這一時代,興起了統計科學、各種社會科學、潮汐學、數理經濟學,還有物理學的現代“萬用理論”。
這一時期,福利體系、郵政體系、貨幣體系、稅收體系和工廠制造業都得到了改革。各個國家從歐洲的戰場上走了出來,開始在科學項目中展開合作。人們意外地發現了一顆行星,這是自遠古之后,人們發現的第二顆新行星。關于其他行星上是否有生命,人們就此爆發了激烈的爭論。南半球的天空和全世界的潮汐第一次被繪入了地圖。人類第一次派出了公共資助的科考隊前往南極洲研究地磁現象。達爾文的進化論改變了人類的視野,改變了人類在世界上的地位。
即使是天才人物和博學人士,也對四位杰出科學家引發的巨變驚嘆不已。
知識的信仰與倫理訴求
《哲學早餐俱樂部:四個杰出科學家如何改變世界》不僅通過時代的巨變展示了哲學早餐俱樂部成員的豐功偉績,而且以傳記的形式,揭示四人之所以成為時代巨子的原因。
誠然,他們是歷史的幸運兒,時代成就了偉人。19世紀英國掀起對科學與探索的熱潮。整個歐洲,學者人都在混合化學制劑,激活電流,通過水晶棱鏡將光分解成多彩的光束。英國皇家學會會報上刊載最新的科學實驗,各種新的雜志如雨后春筍,同大眾分享著科學新聞,如《尼克爾森雜志》《布萊克伍德愛丁堡雜志》《季度評論》《月刊》……在裝訂車間里,邁克爾·法拉第讀到了簡·馬賽的科普讀物《化學對話》,決定投入科學事業中,后來實現了關于電力場的關鍵性突破,改變了人類文明。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中,這四位科學家應運而生,順潮而動,他們的探索與提出的解決方案是歷史轉型期亟待解決的問題,他們個人的情志、抱負、職業、社會活動與實踐恰與時代脈搏吻合,最終成為現實。歷史是時代與個人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拋開時代因素不論,就四人個人因素而言出,成就他們偉大事業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知識的信仰與倫理訴求,他們自覺接受培根的知識論并身體力行。
從本質意義上講,知識是人類對于自然與社會認識的結晶,科學研究活動及其成果無疑是知識的重要內容。一個人的知識觀無疑在世界觀與科學探索中具有重要的意義。
培根提出“知識就是力量”,頌揚知識的功能與價值,知識不僅是促進國家強大、塑造個性實現人性自我完善的動力,也是人類認識和駕馭自然的力量。他甚至認為科學技術發明的意義遠在君主的文治武功之上,君主的功業往往只有一時一地的功效,而科技知識可以超越時空永久造福于人類。在劍橋的早餐俱樂部里,培根的思想是威廉·休厄爾、查爾斯·巴貝奇、約翰·赫歇爾和理查德·瓊斯談論的基本內容。他們接受了培根的知識目的、功能、倫理屬性。他們的科學研究,無一不以解決社會問題、改善人類生活、服務人類而非特殊群體為宗旨,他們的知識探索也超越了個人興趣愛好的隨意性層面,含有一種崇高的責任心與使命感。
為了設計出準確、高效的分析機,巴貝奇進入了癡迷忘我的狀態。他一天工作24小時,幾乎不吃東西,很少睡覺。他的妻子急忙請來了醫生,醫生警告巴貝奇,要他注意休息放松,否則健康會受到永久性的損害。
在非洲開普殖民地,赫歇爾幾乎每晚都守在折射式望遠鏡前,直到次日凌晨四點鐘,摒慮凝神,觀測星空。經過四年的觀測,他完成了南半球最透徹的天文觀測。他匯編了1707個南半球星表,編纂了2102組雙子星表。7萬顆星圖的繪制,提供了恒星分布圖,得出銀河系形狀的結論。
休厄爾在世界各地建立潮汐觀測站,在沒有即時通訊的時代,實現同步觀測潮汐現象。1836年6月,數千名海員、調查者、碼頭工人、本地學者,以及業余的觀察者夜以繼日,每15分鐘就測定一次潮汐,一直持續數天,英國、美國、法國、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時、丹麥、挪威、荷蘭一共有9個國家,近700個潮汐觀察站參與了這一項目。一次滿潮,休厄爾被沖下碼頭。休厄爾的潮汐學研究與等潮線的繪制,使航海變得更為安全了。之前,出于私心與利益考慮,港務人員對于自己所知嚴守秘密,而他們所熟悉的潮汐現象又局限于某一特定區域,休厄爾的目的是全世界潮汐規律。他將調查結果印成冊子,免費向世人發放。
無疑,在諸多因素中,由于四人的知識觀,他們對知識的信念與知識倫理性恪守,他們走在時代的前面,引領風潮,改變世界,型塑今日。
走出象牙塔
中華民族擁有悠久的歷史和豐富多樣的文化瑰寶,歷來有重視事功的優良傳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張載)激勵了一代又一代文人士大夫,但也不乏“一心只讀圣賢書,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嫻雅。通常意義上,前者側重于政治上的事功,后者多為文人雅士失意落魄時的一種調試與人生姿態。對于知識的認識,雖然重視“格物致知”,但總體上說重視道德倫理,而自然與科學領域內的知識觀念稍顯薄弱,思維層面上精確運算與數理運用略顯薄弱,尤其是在重道輕技思想影響下,科學事業被歸屬于“技”的層面受到一定程度忽視。在21世紀,雖然重道輕技傾向得到糾正,技術與科學受到重視,但是整體知識的認識中,依舊有一種視知識為與世隔絕的“象牙塔”內事務的傾向。威廉·休厄爾、查爾斯·巴貝奇、約翰·赫歇爾和理查德·瓊斯不僅是科學家的楷模,勵志的典范,在知識論方面,恰好是一個可資參照的域外鏡像。
知識既然是對人類自身、自然、世界、宇宙的認識,絕非是一個孤立的體系,正如四人所堅信的那樣,它是一個開放的動態體系,知識的汲取應該如蜜蜂廣泛采集花粉,釀出的蜜為人類提供營養。雖然也有個人修身養性的自娛性知識,但總體而言,知識是服務人類絕非私人財產。知識與知識的探索,雖然說是高雅的人類智力活動與科學探索,就其終極結晶來說,它是一個公共產品,社會服務產品,絕非一個獨享的私人訂制。培根與叔父的一次對話,是知識社會屬性的一個生動例證。培根說,相對于哲學家的稱謂來說,他更喜歡人們稱他為慈善家,因為知識服務大眾,改善民生。
當下,世界科技發展日新月異,人類交流空前活躍,社會節奏日益加快,人類精神需求豐富多樣,信息渠道多樣化,即時通訊發達,任何一個審美趣味或者興趣愛好都容易形成特定的群體。這種情形下,無論是在個人素養、社會生活還是青少年的教育層面,知識論問題——如何看待知識,知識如何引導人生——就顯得尤為重要了。
(作者簡介:張立敏,文學博士,中國藝術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