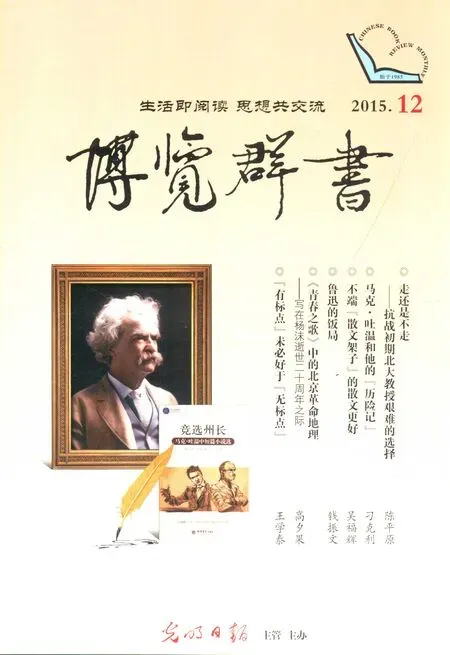史學的“問題導向”可能是歧路
《博覽群書》編輯部:
當前,“理論”與“問題意識”在史學研究領域屢被提及,備受關注,大有一股視“理論”“問題意識”為律之四海而皆準之風氣。尤其是近年來,一些來自域外的作品動輒受到國人熱捧,其一個直觀的原因在于這些作品往往能鮮明地體現出一種理論的色彩、問題的意識以及敘事的故事化。不可否認,史學研究需要有“理論”滋養,也要有“問題意識”。然而,一味地追求以“理論”“問題意識”為導向的史學研究無疑是一種誤入歧途。其實,走出“理論說教”與“問題導向”的史學別有一番風景。
眾所周知,中國史學的發達程度曾經首屈一指,然而自從近代以來,隨著西學東漸,國人在向西語世界學習的同時,卻將中國傳統當中的一些優秀成分給丟棄了。比如,傳統史學當中注重敘事、講求義理、重視實證的優良做法迄今處于被邊緣化的境地。時下,在史學研究領域熱衷于追隨、模仿西方范式的現象依然屢見不鮮,這不得不讓人感到一種生搬硬套、亦步亦趨之嫌。與其人云亦云、邯鄲學步,不如從先人智慧、中國文化的脈延中來汲取營養。史學是一門行走在藝術與科學之間的學問,所謂“藝術”即是指它的人文性,也就是說史學要講究以人為本的敘事。而且,在敘事中要追求美,像藝術那樣;所謂“科學性”即是指這門學問還要求真,體現在史料的真實可靠以及解讀史料的合理度上。這兩個特點在中國傳統史學中有著非常明確的體現。
那些發生在歷史上的事,如同發生在現實生活中的事一樣非常豐富多彩,一種理論顯然不可能做到恰如其分的概括。因為任何一種理論都是從事實中提煉出來的,它“涵蓋面越廣、抽象性越強,丟失的事實信息量就越多”。史學區別于其他學科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其能極盡所能地描摹那些曾經的現實,讀者能從所描摹的歷史場景中激發出一種馳騁的想象力,從而留下自我思維張揚的空間。在這個意義上,史學研究實際上是把客觀的歷史存在內化為主觀的歷史認識的過程。某種程度上,從客觀到主觀又是一個次第漸進生發的過程。然而,對于發生在無限時間線條上和廣袤空間范圍內的歷史客觀存在來說,作為追述者的我們在人類歷史長河中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點,不可能原汁原味地呈現出具體的歷史現場,海登·懷特說:“按目前的理解,歷史是一種事件,是特定歷史環境的產物”,極準確地反映了追述者在與生俱來的局限下的一種努力。正是因為追述者很難一下搞清楚“歷史究竟是什么”,所以才試圖按照提出一個個問題、嘗試解答一個個問題的思路來走進歷史本身。然而,這種“問題意識”的產生又常常出自追述者在現實生活當中的觀感和體驗,因而又不免沾染上對現實社會的某種關懷。不得不說,對于史學研究而言,這又存在著誤入歧途的潛在危險,“史學從來不可能給解決現代問題提供什么對策。史學選擇之前,作者必存有問題意識,但他能提供的則是歷史事例,不是代替別人,而是讓人獨立地從歷史事例里經歷一種智力的考試、道德的考試,用以改善自己思考的方法,端正對問題的認知態度”。就此而言,或許人們常說的“以史為鑒”并非是指歷史研究為現實提供了多么具體的良策,而是人們在讀完歷史之后獲得的一種自我認知改善而已。可以說,一種在沒有實事求是地呈現歷史復雜性的前提下所預設的解釋歷史的模式,并以此模式為基礎所建構出來的另一種復雜性,其實是一種本末倒置。
讀過《庚子救援研究》一書,閃念于腦海的便是該書的“敘事”特色。作者皇皇數十萬言,除導論、余論之外的六章內容都在盡情講述“庚子救援”這個故事,即庚子(1900年)年間,“義和團運動”燎原于華北大地,繼而八國聯軍攻陷平津,兩宮倉惶西狩,京師原有的秩序蕩然無存,大批滯留在京城的東南各省的官員及紳商市民在生活來源斷絕、生命堪虞之際,遠在上海的一些紳商起而號召東南各省商民,在南北之間交通、郵電、金融遭受阻遏的情況下,合力上演了一場曠世大救援。學界關于“庚子事變”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不曾講到這場橫跨大半個中國的“大救援”。通過作者在該書的敘述,我們可以看到,庚子國變前后,京城的社會管理、京官們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所發生的變化,在南北交通中斷后南方報刊媒體對北方時局充滿想象的報道,江南社會義賑傳統的形成及江南經濟之于全國的影響,以及盛宣懷在打通南北通訊、匯兌業務中的努力、李鴻章倡導各省督撫捐款接濟京官、張之洞聯合劉坤一及袁世凱向京官匯款、陸樹藩率員親自北上救援并與洋人交涉、劉鶚因購買太倉粟平糶而獲罪、“浙江三公”回南及祭奠的種種情景,一幕幕歷史場景生動形象地映入眼前,如同電影鏡頭的不斷切換,足以在剎那間觸動觀眾的心靈。這種以具體事例呈現歷史復雜性的做法實屬不易,得益于作者在上檔發掘的《救濟日記》《救濟文牘》《盛宣懷未刊檔》中有關“庚子救援”數量不菲的第一手史料,以及大量的時人日記、文集、報刊等資料,并以此為基礎所進行的精心編排。
當然,對于一本學術專著來講,其旨趣應不只限于滿足內容的可讀性方面,在講好一個故事的同時還需要有某種更深層次的關懷。就史學研究而言,通過對事件的敘述,讓隱藏在事件背后的前因后果及其意義浮現出來,方可算是向深層次的關懷邁進了一步。如果一部史學著作,其字里行間閃爍著智慧的火花,當讀者在閱讀它時能夠引起心靈上的共鳴,在讀完之后能夠在智識上得到啟發,近而能引導讀者自覺地去追求真善美。那么,這樣的作品足以稱得上經典。然而,這樣的作品也確是比較稀見的。特別對于史學研究來說,沒有經歷過豐富的人生閱歷,專業素養沒有積累到夠高的深度的話,想要撰寫出有厚度和深度的作品尤為困難。《庚子救援研究》一書,作者詳盡地勾勒了“庚子救援”的歷史畫面,在感性層面上能夠使讀者印象深刻,在理性層面上也能夠使讀者通過這種歷史畫面觸動情感上的波瀾。在這場被時人稱為“自有家國以來未有之奇變”之后,無論是那些曾經“高居廟堂”的達官顯貴,抑或是“處江湖之遠”的市井小民“或彷徨、或憤怒、或掙扎、或得意、或憂懼、或無奈”的千姿百態經由作者的筆端躍然紙上時,怎能不讓人心生戚戚,發出些感慨來。不僅如此,當這一幕幕畫面浮現在眼前時,又怎能不心生出一種家國天下的情愫來。經庚子國變,中央權威衰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不可同日而語,當清廷借助交通、電訊、郵政等這些現代化的工具所維系的遠方統治忽然塌陷時,出現的信息不暢、失真報道以及由此產生的地方猜疑大大加劇了地方的離心自保。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如同斷了線的風箏。與此同時,整個社會自上而下,也充斥著權吏、官紳之間的爭權奪利等,“庚子救援”中所流露出的種種跡象似乎已預示著大清王朝的未來。
最后一提的是,該書的“余論”部分,作者以闡釋“五對關鍵詞”的形式將貫穿在“庚子救援”這一事件背后的前因后果及其意義娓娓道來。以這種形式結尾,像似一種無奈之舉,實為一種別出心裁。對于歷史復雜性的敘述有時候并非都可以歸結在一個直系根源上,實際的情況可能更像一條大江大河是由眾多支流最終匯聚起來的一樣,但這些支流又是由許多細小的支流匯聚而成的,并非每一條細小的支流都可以直接投入大江大河的懷抱中。因此,在作者對“絲業”“京官”“省籍意識”“東南意識”“義賑”的深入探討中,我們能覺察到出現在前面故事當中的每一個細枝末節,仿佛又在這些探討中能夠找到其發生變化的源頭。而以五個“關鍵詞”為切入點的總結性的探討,最終又匯聚成一個大的主題,即在如此錯綜復雜、艱難險阻之下所進行的曠世“大救援”背后,實際上濃縮了自鴉片戰爭以降中國社會特別是東南地區的歷史變遷。
陳來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