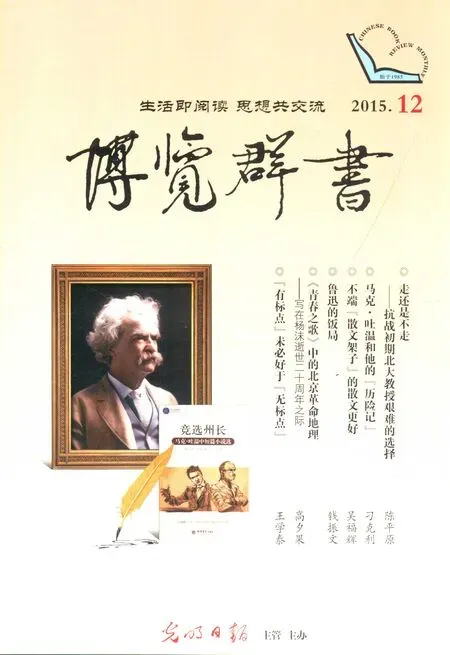此文對全民閱讀有啟示
楊阿敏的《向鄭板橋學讀書》對鄭板橋讀書之道的論述頗有可觀之處,文章總結了鄭板橋在讀書上的一些獨到見解,一是反對所謂的過目成誦,強調熟讀深思;二是強調精讀的重要性;三是認為讀書必須首選經典;四是讀書要有特識,有自己的主張;五是對讀書救貧的思考。論點鮮明獨特,對當下的全民閱讀活動不無借鑒作用。
鄭板橋的讀書觀深刻影響了他對文章之道的理解,他認為文章有大乘法,有小乘法:
《五經》、《左》、《史》、《莊》、《騷》、賈、董、匡、劉、諸葛武鄉侯、韓、柳、歐、曾之文,曹操、陶潛、李、杜之詩,所謂大乘法也。
閱讀學習這些經典著作易而有功,是提升文章寫作水平的最好途徑。可見其提倡熟讀經典是具有現實意義的,并非虛論。鄭板橋所理解的文章包含時文、古文、歌詩、詞賦等形式,與如今對文章的定義并不相同,但其可資借鑒的意義是一樣的。
鄭板橋“自豎立,不茍同俗”的追求亦影響到其藝術風格的形成。在藝術道路上“發憤自雄,不與人爭,而自以心競”,力求形成自己獨到的藝術風格。在書法上,“以漢八分雜入楷行草,以顔魯公《座位稿》為行款,亦是怒不同人之意”,正是有了自覺的藝術追求,不同流俗的自覺認識,最終自創一格,在書法史上留下“六分半書”之“板橋體”。這種意識與今天提倡的創新,本質上是一樣的,不論在學術研究還是藝術實踐中,都值得我們學習提倡。
從儒學角度而言,鄭板橋對三代歷史的認識,沒有明白孔子“美化”三代的意義。孔孟荀以及歷代儒者常講堯舜之道,是回避了歷史細節的真實,而追求歷史本質的真實,即在“道”——核心價值層面重構歷史,這就使史書變為經典,史學變為經學。六經皆史,是指六經本來是史,經源于史,但經孔子整理,經就高于史,不能當史書看待。在當今傳統文化復興、文化主體性重建的情況下,還是要強調經學的根本地位,道統傳承的作用等,充分認識和理解孔子整理六經,傳承上古以來文化典籍的重大貢獻。
(作者簡介:韓星,畢業于西北大學中文系、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分別獲文學學士、碩士、歷史學博士學位。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