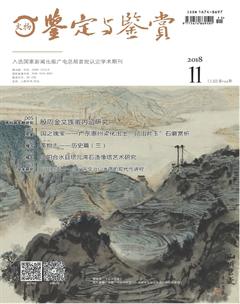公眾考古的傳播要素分析
孫蒙蒙



摘 要:“5W模式”是哈羅德·拉斯韋爾在《傳播在社會中的結構與功能》一文中提出的一個基本的傳播學理論,它首次用模式的方法對人類社會的傳播活動進行分析。文章所研究的公眾考古是一種信息流動的傳播活動,在這個過程中涉及到“5W模式”中的所有要素,因此很適合用這個模式去分析公眾考古存在的問題,以期在此基礎上獲得解決問題的方法。
關鍵詞:公眾考古;傳播者;受眾
1 理論介紹
“5W模式”是誰、說什么、通過什么渠道、對誰、取得什么效果。其稱謂來自模式中五個要素同樣的首字母“W”。這五個要素又構成了后來傳播學研究五個基本內容(圖1),即控制分析、內容分析、媒介研究、受眾研究和效果研究[1]。
傳播者在傳播活動中負責收集、加工、傳遞信息,通常被稱作是“把關人”,包括個人或者媒介組織,是整個傳播活動的出發點。訊息是由一組有意義的符號組成的信息組合。要實現信息有效的傳播,就必須對信息內容的生產以及傳播方式等進行研究。媒介是信息傳遞過程中的中介或者所借助的物質載體,如大眾傳播媒介中的報紙、電視、廣播、網絡等,它是傳播得以實現的物質手段。受眾是信息接受的一個端點,也是信息再傳播的起點。效果即信息傳遞到受眾后引起的受眾思想、觀念、行為方式等各方面的變化。
在借鑒國外相關公眾考古的理論的基礎上,學術界對公眾考古的定義是:“公眾考古就是考古學的大眾化,其核心思想為‘考古學利益相關者‘交流和‘解釋。”[2]如果從傳播學的角度來解讀這個定義,公眾考古就是將考古學的專業知識以各種符號的形式走出象牙塔為廣大的公眾所接受,并對廣大公眾產生影響的一個傳播活動。這種傳播應該是雙向的,即信息到達公眾之后,公眾將所接受的信息進行反饋,實現有效溝通。而這一切活動都是圍繞著公眾,公眾是核心。
2 公眾考古活動中的各要素分析
2.1 傳播者
傳播者首先是信息的接受者,在此基礎上決定什么樣的信息,以什么樣形式,通過什么樣的渠道傳遞給公眾。在公眾考古活動中所涉及到的“專業”傳播的信息往往由考古行業內人員控制并進行發布。作為信息的傳播者,考古工作者不僅僅是考古發掘者,更是文化遺產的保護者。在做好發掘的同時,要有與公眾交流溝通的意識,將考古的成果及時有效地傳遞給公眾,實現知識信息傳播的良性循環,也實現信息的共享[3],有助于提升文化遺產保護意識。但是他們掌握的知識艱澀難懂,只有具有一定考古文博基礎知識的受眾才能讀懂相關信息。對此一些學者撰寫科普類讀物、另類解讀考古,如陳星燦的《考古隨筆》、許宏的《何以中國》等,都受到了廣泛的歡迎。
另一部分傳播者是媒介組織。新媒體傳遞考古新發現更加方便快捷,公眾可以通過新聞或者直播的形式了解最新的考古動態,如CCTV紀錄片《考古中國》《探索發現》。近年來一些考古發掘會聯合電視臺進行直播,如“南海一號”沉船水下考古等,報紙雜志如《中國文物報》等。
需要注意的是,媒介組織會對傳播的內容、語言、傳播過程等進行各種控制和約束,即充當“守門人”的角色。新聞的傳播注重時效性,且要有噱頭。而考古發掘工作時間漫長,且需要細致嚴謹,或者出于各種考慮會推遲信息的發布。這種不協調使信息傳播有一定的延遲性[4]。
2.2 接受者
接受者即所謂的受眾。只有信息傳達到受眾,為受眾所接受,才能產生效果。如果僅僅以到達受眾為目標,而不求效果,那公眾考古是無用的。公眾的需求是開展公眾考古活動的一個著力點,告訴公眾應該知道什么,考古工作如何進行、得出哪些結論和認識,同時又能使公眾認識到發掘的價值,也理解考古工作者本身存在的意義[5]。
目前中國考古發掘并沒有將公眾的重要性考慮在內,公眾只是考古信息的被動接受者,受眾的選擇性很小。相比之下,土耳其恰塔胡由克遺址的公眾考古活動著實是一個范本,它的公眾考古活動由專門的人員進行設計并負責實施,且活動涉及多個方面,方式多種多樣,每年都會舉辦,并將公眾考古活動貫穿到考古工作的每一個細小的環節[6]。
2.3 訊息
訊息是有意義符號的組合。公眾考古中所講的信息是通過載體呈現出來的信息,有時載體本身就是信息。對古代遺存的解讀是建立在考古發掘基礎上的,通過發掘獲取原始的考古材料。研究、展示和傳播都是考古資料重要的利用方式,公眾對考古學家所做工作的過程、方式、方法具有極大的興趣,希望進行體驗式分享。目前所進行的考古信息的發布以結果發布為主,但也需要考古過程的開放,更需要探索對發掘資料提取、保存、發布的方式[7]。
“施拉姆在《傳播是如何進行的》一文中提出了傳播的循環模式,指出傳播者與接受者之間,只有在其共同的經驗范圍內才真正有所謂傳通,只有在這范圍內的信號才能為傳受兩者所共享。”[8](圖2)考古報告編寫的過程中,所運用的是專業術語,而這種術語并不能為大眾所熟知,能看懂考古報告的必須具有專業知識。現在所講的公眾考古,就是需要將這些艱澀難懂的信息運用各種形式進行多級解讀,才能使不同知識水平的公眾獲得其所在層次的知識。也就是說公眾與考古之間需要有一個媒介,即需要培養信息的解碼者,這些解碼者需要將難懂的信息翻譯成大眾所能理解的信息。
但是針對考古報告是否需要考慮公眾,學者意見不一。有學者指出,考古報告是為研究使用的,并不是為公眾服務的。但是筆者認為,考古所研究的人類歷史有其特殊性,考古報告并不能和理工科的研究報告相提并論。目前在探索面向公眾考古報告的道路上,一些報告也表現出了自己的態度,如《梁帶村里的墓葬——公共考古學報告》就是用通俗易懂的語言為公眾解讀遺址。[9]
2.4 媒介
公眾是通過各種媒介才能夠接觸到考古知識,如書籍、電視、廣播、互聯網、手機等途徑。這些媒介是大眾傳播主要運用的手段,也給公眾考古的實踐提供了便利手段。
各類媒體組織各顯神通吸引觀眾。網站是一種獲取信息的方式,如考古匯、中國考古、中國公眾考古網等;隨著智能手機的普及,公眾可以利用手機App暢游博物館,其他知識類App如紫禁城祥瑞、胤禛美人圖;使用微信關注公眾號,如上下探訪五千年、弘博網、考古中國等,就可以輕松地獲取這方面的知識等。
除此之外,非大眾傳播媒介的手段也應該受到重視。如博物館、考古工地等,這些是揭示考古工作原貌的最好的場所。博物館是考古發掘出土文物的集中展示地,博物館展覽質量的高低關系到公眾信息的接受。考古工地的開放,可以讓公眾近距離接觸遺存,同時有考古工作者在現場講解最原始的考古素材,可以實現與公眾進行互動 [10]。
還有一個特殊的媒介是博物館的志愿者等具備考古知識的大眾,這些人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又是傳播者,在與人的交流過程中將自己所掌握的信息傳遞給其他人。
2.5 效果
效果即效用。在公眾考古過程中,各種考古信息傳播到公眾以后,對公眾會產生多大的影響?而信息是否到達公眾,是否對公眾起作用是關鍵。據調查顯示,很多參加過考古活動的公眾表示收獲頗多,同時表現出再次參與的強烈愿望[11]。這就達到了傳播和教育的目的。與此同時,也應該注意到傳播活動的信息交流的環節,即公眾在接受到信息之后可以通過各種途徑進行信息的反饋(圖3),發表自己的見解,這樣傳播者會吸收來自不同領域中的新知識和見解,從而重新構建自己原來的知識系統[12]。曹操墓認定就是一個公眾參與考古的例子,社科院考古所更是舉辦了“聚焦曹操高陵”公眾考古論壇。[13]
3 綜合分析
公眾考古是一項復雜的系統活動,任何一個環節的缺失或者薄弱,整體的效果將大打折扣。就目前的公眾考古活動的主導者來說,基本都是考古領域的工作者,很難有外領域跨界搞公眾考古。而考古工作者并不具備傳媒方面的知識,不了解大眾傳播的特性,在與公眾溝通的過程中可能會存在各種問題。如果考古工作者變被動應對為主動出擊,掌握發布的主動權,確保信息的嚴謹準確性,這類問題則會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決。
公眾考古從業者需要具備各方面的知識,如歷史、考古、新聞傳播、心理、經濟等[14]。在大眾傳媒時代,考古要想走近公眾,就必須加強宣傳與交流,必須充分利用大眾傳播,培養復合型人才。一方面,熱衷于從事公眾考古傳播研究的學者或者學生等,要探索將學術語言向通俗語言轉化的方法,與媒體聯合尋求更有效的傳播手段。另一方面,各類媒體負責考古文博新聞信息的采集部門,要重視記者編輯的考古知識的培訓,做好儲備,以便深入理解考古工作的各個環節,增強報道考古類新聞的準確性[15]。懂需求、會溝通、善分享,這些復合型人才是一座架在考古與公眾之間的橋梁,可以實現考古信息的多級傳播。
公眾考古活動的開展首先要建立在公眾特點與需求的調查基礎之上,針對不同公眾設計不同的公眾考古活動,使活動從“小眾”走向“大眾”。如威爾士國家博物館建立網頁“挖掘維京,正在進行的考古”,每天更新發掘工作的細節及教育信息等[16]。
在這里引入一個“意見領袖”概念。“意見領袖”是在人際傳播網絡中經常為他人提供信息,同時對他人施加影響的“活躍分子”,在大眾傳播效果的形成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中介或者過濾作用,由他們將信息擴散給受眾,形成信息傳遞的兩級傳播[17]。因此,也需要注意在民間的“意見領袖”的培養。他們身處大眾之間,在危機事件發生時,通過“意見領袖”來引導輿論,對于解決危機十分重要。“意見領袖”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信息的傳播者,將上級傳播來的信息運用自己的知識進行解讀與轉化,也會使考古、文博知識的傳播更接近大眾。
參考文獻
[1][8][17]邵培仁.傳播學(修訂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郭立新,魏敏.初論公眾考古學[J]東南文化,2006(4):54-60.
[3][4]姚偉鈞,張國超.中國公眾考古基本模式論略[J].浙江學刊2011(1).
[5][10]蒂姆·科普蘭.將考古學展示給公眾——建構遺址現場的深入了解[J].黃洋 譯.陳淳 校.南方文物,2013(1).
[6][12]王濤.土耳其恰塔胡由克遺址考古記 [J].大公考古,2014(9).
[7]曹兵武.資料·信息·知識·思想——由專家考古學到公共考古學[J].南方文物,2011(2).
[9]陳燮君,王煒林.梁帶村里的墓葬——一份公共考古學報告[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11]鄭媛.試論在中國建立“公眾考古學”的必要性[J].文物世界,2010(4).
[13]邵鴻.當代史學的公共面向和大眾參與——對曹操墓認定風波的初步分析[J].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1(2).
[14]孫波.新傳媒時代的“公眾考古學”與危機公關[N].中國文物報2012-08-31.
[15]郭云菁.公眾考古傳播的人才培養機制[N].中國文物報2011-09-02.
[16]尼克·梅里曼.讓公眾參與博物館考古[J].黃洋,高洋 譯.陳淳校.南方文物,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