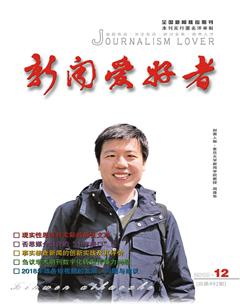先秦時期《詩經》的傳播形態
楊建偉
【摘要】從先秦時期文化傳播的兩種基本形式入手,指出了《詩經》在先秦時期以口頭傳播為主,輔以文字傳播的基本傳播形式,并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具體分析了《詩經》的傳播手段和傳播特點,從這些方面綜合闡述了《詩經》在先秦時期的傳播形態。
【關鍵詞】先秦時期;《詩經》;傳播形態
《詩經》作為我國古代詩歌文學的開端,收集了從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500年間共311篇詩歌,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豐富的社會面貌,具有極高的歷史研究價值和文學價值。分析《詩經》在先秦時期的傳播形態,有利于深入了解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和文化傳播的一般形態,進而深入理解《詩經》的歷史文化價值,對促進《詩經》在當今時代的傳播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一、先秦時期文化傳播的一般形態
分析先秦時期《詩經》的傳播形態,有必要先考察先秦時期文化傳播的一般形態。先秦是中華文明的頭顱[1],作為中華文明的早期階段,先秦時期的文化傳播形態有其獨特性,一般有口頭傳播和文字傳播兩種傳播形式。
(一)口頭傳播
文化傳播交流的最初階段是口頭傳播,口頭傳播廣泛應用于文字記載和交流體系成熟之前的漫長文明時期。在中華文明早期,盡管夏朝已經出現了文字,商朝已經有了較為成熟的甲骨文,商周時期中華文明已經進入了有文字記錄的時代,但早期的文字符號只是作為神諭的記載工具,由占筮人員支配和使用,主要用于記錄,尚未用于創作。隨著文字的成熟,文字作為重要的媒介權力,由統治者所掌控和支配,文字承載的信息溝通功能尚無空間發揮,更不用說用于文學創作和傳播了。在周代,封建政治體制決定了各諸侯國各自為政,區域性差異較大,各國之間缺乏統一而廣泛的交流工具,這進一步限制了文字作為交流工具的發展空間。這些早期文字的特點及當時的政治、社會環境,決定了最初的文學創作和傳播不可能大量以文字為媒介。
盡管如此,在當時,從中央王室、各諸侯國所在都市到偏僻鄉村,從繁華街道到田間地頭,民間的口頭傳播渠道卻是暢通無阻的。豐富多彩、活潑生動的民間生活為早期文學的創作提供了大量素材,神話、傳說、寓言、諺語、奇聞、逸事、歌謠都在民與民之間口耳相傳。口語在日常使用中自然地、無形地發揮了文化傳播的功能,民間百姓的街談巷議、娛樂歌唱成為一種最普遍的社會輿情傳播方式和早期文學傳播方式。
(二)文字傳播
文字符號的產生是人類文明進入更高層次的重要標識,文字的出現及其運用體系的成熟極大地推動了人類文明的傳播。文字傳播在時空廣度上比口語傳播更加長遠。先秦時期尤其是周代后期,文字系統和使用逐步成熟,文字傳播在先秦時期的文學傳播中也占據了重要地位。
文字書寫有悠久的歷史,考古發現,中國大地上原始社會的陶器時代已經有了刻劃符號,遠古時期有倉頡造字之說,至商代甲骨文已經是成熟、系統的文字。早期文字主要用于記錄占卜、神諭,周代文字已經運用到禮儀祭祀中,成為記載和傳播禮樂文化的重要媒介,春秋戰國時期,記錄在竹簡木牘上的文字成為上流精英階層溝通交流和文化傳播的重要媒介工具。文字傳播的發生是出于控制的需要,周代諸侯國林立,文化相對隔絕,溝通交流不便,中央與地方聯系困難,文字體系成熟之后就逐步代替口語成為國家和社會管理的重要工具,成為周王室加強政治統治的重要手段,文字傳播隨之更廣泛地運用于社會領域。文書成為周代統治者政治決策、國家管理等一系列活動的重要輔助工具。春秋時期,已經出現了許多典藏文獻機構,戰國時期,文書制度進一步完善,文字隨著中央王朝統治權力的輻射,成為當時禮樂文化的重要傳播載體。
二、先秦時期《詩經》的傳播形態
《詩經》作為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是周代禮樂文化盛行下的產物。《詩經》屬于集體創作的產物,其創作者可能來自王公貴族,也可能來自民間百姓,其產生的地域也遍及周代王權覆蓋的所有重要區域。《詩經》的內容包含了周王朝樂官制作的樂歌,諸侯、大夫進獻的樂歌,以及許多來自于民間鄉野的歌謠。總之,《詩經》的產生成書與周王朝的統治息息相關,它是周王朝用于傳播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禮樂文化)、了解民間輿情、加強政治統治的需要,所以說《詩經》的文化傳播功能遠遠大于其文學功能。[2]《詩經》的傳播史從其產生就開始了,從最開始的傳唱、采集,到演奏、歌唱,到作為必學科目進行教授,再到諸侯交流時的賦詩、吟詩,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到《詩經》的使用和傳播之中,豐富了《詩經》早期的傳播手段。
(一)先秦時期《詩經》的傳播形式
《詩經》在先秦時期口頭傳播和文字傳播兩種形態兼有,具體形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1.演奏歌唱
《詩經》是禮樂文化盛行下的產物,是適應周代禮樂需要的一種樂歌匯編,它為周禮服務,進而發揮維護周代統治秩序的功能。所以,為了傳播宗法等級意識,固化社會等級觀念,強化周王朝中央權威,《詩經》中的內容成為在周代大型祭祀、宴會等莊重儀式活動中,演奏歌唱的重要內容。這種演奏歌唱的形式,在周王室權力興盛的西周及春秋早期廣泛采用,詩的內容通過樂聲表達出來,樂詩相合,一唱三嘆,使《詩經》中的內容廣為傳播,成為人們所熟知的語言。
2.師生傳授
古人重教,教育是中國古代最有效和廣泛的一種文化傳播途徑。春秋時期教育興盛,文化繁榮,百家爭鳴,《詩經》就是這一時期教育傳授的重要內容和開端。《詩經》的傳授不僅在于修身明德,更是出于政治事務中發言立論的需要。[3]春秋時期的學校有官學和私學兩種,它們都為《詩經》的傳播提供了重要場所。在官學中,又有貴族學校和樂工學校,課程之一都是《詩經》,通過學習《詩經》,貴族子嗣不僅學會了樂曲和歌唱,還學會了借詩言志,以詩立論;樂工學校則通過學習《詩經》,學會了演奏歌唱技巧,為上層貴族提供更好的服務。《詩經》作為官學的課程內容,其傳播僅限于王侯、大夫等上流社會精英階層,當時西周時期的精英階層幾乎人人熟悉詩歌,學詩的目的不僅在于演奏吟唱,還在于借詩言志,以詩交流成為上流精英階層的重要交流形式,這進一步促進了《詩經》在上流精英階層的廣泛傳播,為后來《詩經》跨階層的廣泛傳播奠定了堅實基礎。
春秋末期,王權衰微,禮崩樂壞,官學式微,私學盛行,包括《詩經》等在內的宮廷典籍流入社會,成為私學傳教的主要教材和課程,以孔子為代表的各大學派,把文化從朝堂帶入民間。作為偉大的教育家,孔子提倡有教無類,廣納學生,門下學生徒弟來自各行各業、各個階層。《詩經》作為孔子傳授的重要課程,隨著其眾多學生的傳播,突破了階層的藩籬,跨越了地域限制,得到了廣泛的流傳。在《詩經》的師生傳授過程中,不僅直接傳播了《詩經》本身,同時還培養了大量精通《詩經》的人才,這些人把《詩經》廣泛運用在抒情言志、修身明德、言語修辭、歌頌諷刺等方面,賦予、傳播了《詩經》更為豐富的文化內涵,使《詩經》得到了更為廣泛的傳播。
3.賦詩言志
賦詩言志是春秋時期上流社會盛行的一種風氣,也是《詩經》使用和傳播的一種重要方式。春秋時期,各諸侯國之間需要頻繁地交往,作為掌握文化資源的諸侯、大夫,他們的交流方式自然不同于民間百姓,他們在會談中相互稱頌、規勸、諷刺成為日常,有時候也需要委婉言志,在這些場合,借助《詩經》中的語言可以委婉、高雅地進行表達,借詩言志成為一種重要的風氣。在這種潮流下,精英階層只有對《詩經》足夠熟悉,才能大方應對,合禮表達。在這種社會氛圍中,賦詩成為諸侯、大夫處理政務和外交活動的重要語言工具,這使得精英階層必然加強對《詩經》的學習,這也促進了《詩經》的傳播。
4.引經據典
《詩經》內容豐富,其中包含了周代政治、社會和當時人們的生活習俗、思想感情等方面的大量資料,反映了周代百姓生活、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歷史風俗等方方面面的主題,其豐富內容為后人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大量素材和依據。同時《詩經》作為一部歌謠,語句簡短,朗朗上口,文學性和藝術性極強。這些特性使其成為春秋戰國時期人們言語和著述的重要引證來源,在語言交流和著述寫作中引用《詩經》的內容,也成為《詩經》的一種重要傳播途徑。這種對《詩經》的引用方法成為引經據典這一文學修辭的開端。引經據典可以將自己平淡的語言替換成優美簡約、人人皆知的古詩,從而引發共鳴,增強感染力和說服力,又可以顯示自己的博學和才智,因而這種風氣在整個周代一直長盛不衰。《詩經》的很多內容借助人們的大量引述而獲得了間接的廣泛傳播,它啟發誘導人們去閱讀、熟悉、運用《詩經》,進一步推動了《詩經》的傳播和使用。
總之,《詩經》在先秦時期的傳播方式是豐富多樣的,它通過多種口頭和書面的方式得到了廣泛的流傳。
(二)先秦時期《詩經》的傳播特點
分析《詩經》的傳播特點,也有助于理解《詩經》在先秦時期的傳播形態。先秦時期,《詩經》的傳播有以下特點。
1.鮮明的口頭傳播色彩
《詩經》成書于春秋中期,但在春秋時期,其傳播仍以口頭為主。一方面,這是由于書寫材料和文字傳播使用范圍的限制,在春秋時期,文字已經比較成熟,但由于技術的限制,當時所用的書寫材料主要是竹簡、木牘和帛書,這些材料相對商周時期的甲骨、金石,雖然易寫易存易傳播,但依然不夠方便,竹簡、木牘不容易制作,且體積較大,不方便攜帶,而絲帛價值貴重,一般人更是用不起,材料的限制導致文字書籍的傳抄極為困難,同時,文字的發展及普及難度較大,春秋時期雖然文化得到了較為廣泛的傳播,出現了百家爭鳴的現象,但文字還是主要由上層社會人士所掌握,平民使用仍不夠廣泛,一個典型的例子便是孔子教學“述而不作”,他的思想和言論都是由他的弟子及后世整理而成書的。另一方面,當時的社會環境限制了書面的文字傳播,春秋戰國時期,王室衰微,諸侯割據,各自為政,各諸侯國之間文化背景不同,“書不同文”,同一個字在各諸侯國寫法不同,這就造成了書面溝通理解上的障礙,不利于《詩經》的文字傳播。因而口頭傳播便成為《詩經》早期“天然”的傳播方式和主要傳播特征。
2.具有音樂性
文化傳播是政治或軍事領袖先知先覺的具有高度協同性的群體活動,是有組織的文化傳播形式。[4]《詩經》的傳播同樣遵循這樣的規律。《詩經》所承載的是周王朝的禮樂文化,發揮著重要的政治教化功能,為了使其廣泛流傳,必然要采取廣大民眾容易接受和喜聞樂見的形式,歌唱、音樂的形式就符合這一需要。《詩經》不同于神話傳說、寓言諺語等一般早期的口頭文學,它是一種具有韻律和美感的樂歌,《詩經》的各篇都是可以合樂歌唱的,它的所有詩歌都以樂歌的形式向外傳播。《詩經》中風、雅、頌的劃分就出于音樂的不同[5],清朝學者王國維就曾說“風雅頌之別,當于聲求知”。一種觀點認為:“風”具有聲調的含義,十五國風,就是十五國當地的音樂;“雅”代表周代中央王朝統治地區的音樂,象征正統之聲;“頌”有“形容”的含義,是一種宗廟祭祀和其他莊重儀式活動中所用的樂曲。此外,《詩經》中大量運用了“賦、比、興”的藝術手法,其句式以四言為主,四言句屬于兩節拍句式,有很強的節奏感,再加上重章疊句和雙聲疊韻的復沓結構,《詩經》就有了結構舒卷徐緩,朗誦回環往復的特點,這種藝術表現便于《詩經》的口耳相傳,容易被廣大民眾接受和了解。
3.突出的政治和道德取向
《詩經》從誕生之初就帶有明顯的政治性,它是周公制禮作樂、實施教化、輸出秩序、便于管理的一種政治行為。出于這種政治教化的目的,《詩經》的傳播采取了容易被廣大民眾所接受的樂歌形式進行傳播,《詩經》的傳播是合樂行教化之用的。[6]《詩經》傳播的政治性和道德性取向體現在《詩經》傳播的所有形式中,一是表現在周代的祭祀、宴會等重大儀式中,在這些儀式中,演奏歌唱《詩經》的內容成為人神溝通、宣示權威的重要形式,宣揚、表達了鮮明的政治含義和等級觀念。二是表現在春秋時期官學私學教授《詩經》的目的方面。學校傳教是《詩經》的重要傳播手段,而學校傳教《詩經》主要是因為《詩經》包含豐富的禮樂文化,具有培養性情、陶冶情操的道德功能和強烈的關注現實的理性精神。三是在各諸侯國之間的政治交往和集會交流中,引用《詩經》委婉表達愿望、闡明態度,甚至發表意見,借詩言志,這些活動都帶有強烈的政治目的。四是在后來的引經據典階段,引述方把《詩經》作為論述依據,作為真理和格言來論證、表達自己所要闡述的帶有某種道德評判和價值評估的觀點。《詩經》中明顯的政治道德取向,也許正是司馬遷所記載的“古者詩有三千余篇,而孔子刪成三百零五篇”的重要原因(見《史記·孔子世家》)。
4.傳播范圍廣泛
春秋時期諸侯國各自為政,地域隔絕,但這并沒有妨礙《詩經》的廣泛傳播。通過演奏歌唱、賦詩言志等形式,《詩經》隨著周王朝統治權力的輻射和各國之間頻繁的政治交往而得以廣泛傳播,遍布當時王權覆蓋的所有重要區域。
總之,《詩經》在先秦時期的傳播以口頭傳播為主,具體的傳播形式則有演奏歌唱、賦詩言志、學校傳授、引用引述等手段;在傳播過程中,《詩經》表現出鮮明的口語色彩、強烈的音樂性和藝術性、突出的政治道德取向以及廣泛的傳播范圍等特點,這些共同構成了先秦時期《詩經》的傳播形態。
參考文獻:
[1]羅家湘.論先秦時代的文學傳播活動[J].語文知識,2011(12):9.
[2]方堅偉.先秦《詩經》傳播形態論略[J].黑龍江教育學院學報,2016(5):13.
[3]何如月.從傳播學視角看《詩經》在春秋時期的流傳及其影響[J].陜西師范大學繼續教育學報,2006(3):19.
[4]劉娟.先秦時期《詩經》傳播過程中的主旨演變[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6(8):23.
[5]潘祥輝.“歌以詠政”:作為輿論機制的先秦歌謠及其政治傳播功能[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7(6):21.
[6]魏瑋.先秦口頭敘事的概念、類型及特征[J].文學批評,2017(12):16.
(作者為鄭州財經學院講師)
編校:王志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