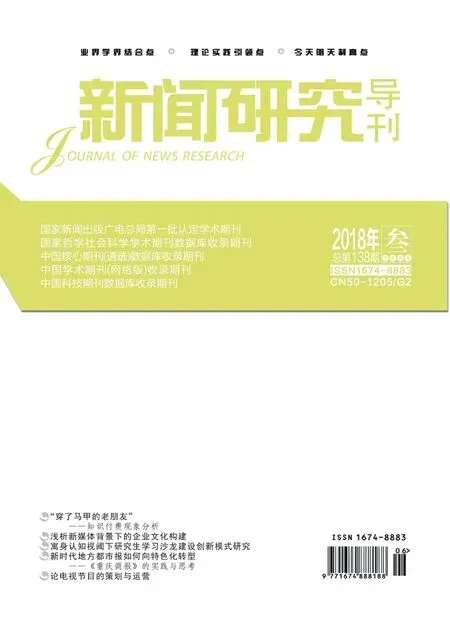后真相時代下媒體該以何種“姿勢”報道熱點
張 誠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 軍事文化學院<南京教學區>,江蘇 南京 210000)
自2017年起,媒體報道的一些公共事件引發了輿論的熱烈關注,如江歌被害案、保姆縱火案、辱母案、尋找湯蘭蘭事件等。相關報道和討論在較長一段時間維持較高熱度,它們的輿情走向也驚人的相似——輿論和觀點隨新聞一起反轉,公眾的注意力不斷失焦,而已知信息真假難辨,各方輿論各執一詞……公眾在輿論場中一次又一次被說服,真切感受到了2016牛津詞典年度國際熱詞“后真相”的威力。
媒體作為連接信息和公眾的橋梁,在引發“訴諸情感及個人信念,較陳述客觀事實更能影響輿論的情況”時,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所以,在享受了由10萬+瀏覽量變現的業績后,即使是大牌媒體也免不了付出代價,即在觀點泛濫、事實稀缺的報道中,公眾對媒體的信任度逐漸下降,媒體本身成為被評價的對象。
因此,在后真相時代,媒體該如何與公眾交流?該如何化解這場信任危機?又該如何奪回輿論場的公信力?這值得每個新聞工作者深思。
一、避免不當報道方式
(一)避免個人化
庫利的“鏡中我”理論表明,在圍觀中,人們往往會通過他人來反顧自照。所以,為了使讀者感到“無盡的遠方和無數的人都與我有關”,越來越多的新聞事實被拉到個體層面解讀。分析被害者的心理、剖析當事人的原生家庭等,在親情特別是涉及直系親屬的問題上,很多情感無法用理性解釋。這種有失平衡的片面性解碼激起人們的同理心和情感共鳴,讓人們感到自己仿佛和遙遠的事件產生了聯系。
這樣的報道巧妙利用了接近性原則,勾連了讀者與事件的相關性。這個時候往往容易激發讀者樸素的正義感,自動代入受害者角色,以簡單的二元對立標準評判復雜的事件真相。這種報道方式有失偏頗。
(二)避免戲劇化
19世紀末,黃色新聞在西方盛行,“趣味性”似乎成了判斷新聞價值的首要標準。這種現象現在也并不鮮見,如吸睛的標題提煉、細節描寫,以及戲劇沖突、矛盾性的敘事方式等。作為媒介產品的新聞開始仰賴這些“包裝”,如同花哨的商品任君挑選。“假如謬誤對他們(指群眾)有誘惑力,他們更愿意崇拜謬誤。誰向他們提供幻覺,誰就可以輕易地成為他們的主人……”[1]為了迎合公眾的認知期待與情感投射,媒體越來越多地報道過度渲染的戲劇化情節,不惜犧牲真相。
2017年初,南方周末的《刺死辱母者》以聳動的標題和帶有大量刺激性詞語的案發細節描寫,成功引爆輿論。雖然最后證實這些細節大量失實,但由于彼時呈傾倒之勢的輿論狂潮,后續跟進的真相鮮少有人關心。
貝內特曾在新聞生產研究中提出“新聞戲劇化”的報道方式,事實證明,過于戲劇化會只突出單一矛盾,忽略整體事實的復雜性,使感性的解讀壓過理性的聲音。新聞是可以平易近人地講述的,新聞報道如何把握尺度,規避將當事人作為“故事”人物進行敘事性、故事化的聳動呈現,防止報道中情感煽動、細節描寫過剩,依舊任重道遠。
(三)避免情緒化
很多時候,人們關注、轉發一篇報道,并非因為內容,而是情緒和觀點更易戳中痛點。當謾罵、同情、安慰蜂擁而至成為輿論場的主流并形成一定規模,誰還會注意信源是否真實呢?
新京報旗下的人物專訪欄目《局面》報道江歌案,鏡頭記錄了大量江歌媽媽哭泣的場景,刪除了劉鑫的部分重要陳述,對殺人兇手也并未過多提及。于是,評論一邊倒地大罵劉鑫。這檔節目雖然沒有故意引導輿論,但不平衡的報道過分渲染了情緒。在痛失愛女的母親痛哭流涕的畫面前,情緒化的觀點一擊即中并得到廣泛傳播,而等落后輿論一步的真相姍姍而來時,它似乎已經不那么引人關注了。
2017年12月11日,江歌案在東京公開審理的當晚,輿論達到頂點。咪蒙在公眾號發文《陳世峰被判20年,江歌媽媽被判無期》,帶著粉絲下了判決書:殺人償命。全文情緒激烈,態度主觀,卻絕口不提兩國法律差異,不談證詞沖突。此時,由于情緒化的觀點席卷全網,理性的聲音非常微弱。
(四)避免碎片化
事物的發展趨勢是前進性與曲折性的統一,謬誤變為真理需要時間的積累。然而,在新聞追求實時化的今天,為時效性買單的只能是殘缺的真相。在事件還未完全展開時,碎片化的新聞和解讀就已爭先恐后地呈現。它們往往截取聳人聽聞的一小段,孤立時間,單獨對待事件。
客觀事實的呈現方式本身就帶有一定的引導性,真話片面了也會失實,而碎片化傳播呈現的大多就是局部事實。當割斷了事件間的聯系,語境缺失,人們忽略了需要去反復核查、拼接、全面思考的事實,很難再把握全部的真實。
1989年,江澤民同志在新聞工作研討會上說過:“不僅要做到報道的單個事情的真實、準確,尤其要注意和善于從總體、本質上以及發展趨勢上把握事實的真實性。”[2]然而,在大量搜奇獵異、捕風捉影的報道中,能夠全面完整闡述事件的,具有權威性、科學性的新聞報道是稀缺的。
二、探求正確報道方法
(一)有理有據報道真相,追求“客觀”永遠在路上
受眾接收信息的心理呈現出選擇性注意、理解、記憶的線性過程,記者也是如此。所以,新聞工作者要常常問自己:“我們只愿意傾聽與我們道德觀相吻合的斷言嗎?我們是將新聞當作客觀證據,還是根據自己的主觀愿望引導讀者從中尋找證明?”人類的感性意志剔除不了,所以不理性的聲音是難以從輿論場域中剔除的,就連媒體的客觀都是有傾向性的客觀。真相如同反比例函數,無限趨近,卻永遠不會抵達,但這不是媒體放寬報道標準的理由。如何減少這些因素給受眾帶來的影響,并盡可能全面展現事件真相,應是所有媒體始終追求的目標。
首先,對于一個事件,我們需要更多的聲音。柴靜在《看見》中說:“客觀并不是關上耳朵啥都不聽怕被任何一方的觀點左右,相反應該去思考每一個角度和立場發出來的聲音,讓每一股力量相互拉扯,達到平衡。”彌爾頓在《論出版自由》中提出“觀點的自由市場”,認為真理是通過各種意見、觀點間自由辯論和競爭獲得的。只有更多理性的觀點不斷補充、彼此碰撞,才能讓輿論情緒趨于冷靜,才有機會達成輿論自凈。
雖然沒有絕對的客觀理性,但我們要盡力做到有理有據。正如李普曼所認為的,新聞很多情況下是對“可能的真相”的報道,是“探照燈”。[3]記者、評論者和我們所有人一樣,看見的只是片面的真相。新聞可能無法承受我們強加的“提供真相”的標簽,但在塵埃尚未落定前,我們就不該放棄尋找。為了離“客觀”更近一點,媒體在報道的同時,更要對事實進行核查,事實是否被巧妙截取、加工、拼湊等都需要判別,這也是踐行新聞專業主義的表現。
(二)秉持專業精神和公共性,提升記者的職業素養
因種種條件限制,記者和編輯對素材會有一定程度的取舍,甚至會出現當事方缺位,而受眾很難察覺的情況。若當事方越過媒體,直接面對公眾,輿情走勢也會不同。因此,即使條件有限,也要盡量交叉印證、平衡報道,避免潛移默化引導受眾。央視自1996年開播至今的《新聞調查》欄目提供了很好的報道范式,其《追查轉基因大米》《注射隆胸》等經典節目都嚴格踐行不偏不倚、平衡深入的原則。反觀今日,許多媒體正與專業精神背道而馳。
傳統媒體運用寫作框架、技巧時,應避免刺激社會情緒。例如,使用“大媽”“富二代”等強暗示性的口語詞的初衷是拉近受眾距離,但在特定語境,其隱含的微妙感情色彩易引發對腦中基模和刻板印象的聯想,與無關的經驗和感情相聯系。
新興媒體也需具備公共性和公益性。一些著名自媒體已是公眾獲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其粉絲量決定其言論的巨大影響力。公眾不能無限安裝APP、關注公眾號,大V們相當于占據了公共資源。所以,新媒體將承擔一部分維護公共利益的責任,特別是在傳統媒體渠道失靈、輿論引導功能缺失時,其要以客觀公正的視角,冷靜看待事件進展。
因此,考查記者的職業素養尤為重要,如用事實說話的能力以及理性、克制、張弛有度等。記者務必恪守新聞倫理,不在事件定性前妄下定論,同時精準洞察受眾心理,如考慮隱私暴露的反彈心理、共情心理等。對于在“尋找湯蘭蘭”事件的報道中,個別記者暴露當事人隱私的做法,人民日報評論:“媒體追求正義,需建立在尊重事實,合乎法律的基礎上。”
(三)加強事實探索,重視深度報道
報道成本有時決定了讀者的認知成本,好的調查報道能引起公眾對社會的深入思索和反躬自省。挖掘事實難,但基于事實片段的想象和推演卻很簡單。遺憾的是,如今越來越多的媒體選擇走捷徑,“市場化都市報迫于生存,壓縮采訪成本,甚至撤銷深度報道部”。媒體常常愿意去報道人們已經在談論的事,而不會關注、挖掘被忽略的事情。
這不禁讓我們懷念20世紀80年代深度報道興起時,一些記者前輩的努力——中青報的葉研、李偉中等記者奔波一個月深入調查,寫出了震驚全國的“三色報道”,為公眾還原了大興安嶺火災發生前后完整真實的過程,而在距今不久的“紅黃藍幼兒園”事件中,媒體卻疏于做細節事實脈絡的調查梳理,偏信單一信源,觀點嚴重失衡,即使最后真相揭露,也難以說服公眾。前后“三色”對比,令人唏噓。
對此,國外亦有他山之石可供我國媒體借鑒。2017年,在媒體競相追求速度時,BBC逆勢而為,推出“慢新聞”計劃。更多資源、事件、數據將被挖掘,篇幅更長、更有深度、制作更費時的文本報道和視頻解說將被發布。“我們并不想單純為了追求速度而氣喘吁吁地往前趕,而是想要精心打造一套成熟的編輯理念。我們需要慢節奏,需要更深入的新聞。”BBC新聞編輯部主任杰米·安古斯如是說。這可供借鑒的是,做新聞要“對話題有更深入的分析,還原事件的情景,并為觀眾提供新聞頭條背后的事件(what)和原因(why)”。我們需要媒體付出專門的努力去采編被我們忽略的新聞,而不是在現有的合唱中增加一種聲音。
[1]古斯塔夫·勒龐(法).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M].趙麗慧,譯.中國婦女出版社,2017:23.
[2]江澤民.關于黨的新聞工作的幾個問題[Z].1989-11-28.
[3]沃爾特·李普曼(美).公眾輿論[M].閆克文,江紅,譯.上海世紀出版社,2006: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