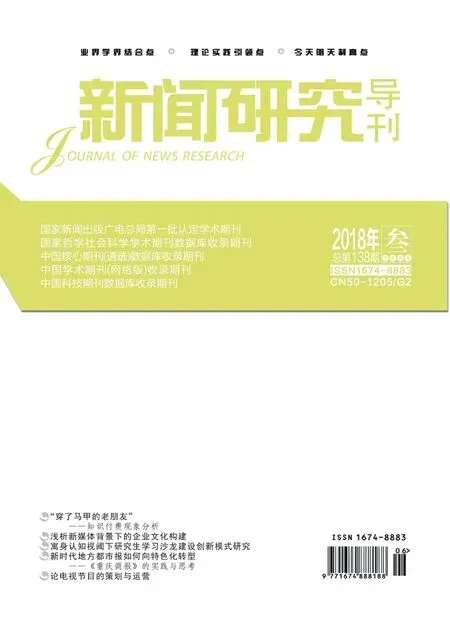人文景區書店文化空間的生產研究
——以成都散花書院為例
宋雨霜
(四川大學 文學與新聞學院,四川 成都 610065)
隨著國家近幾年在政策上對文化產業的不斷扶持,市場化的持續開放,以及實體書店始終不放棄努力探尋自我救助的發展策略,實體書店迎來了發展的回暖期。此外,隨著旅游需求的提升,人們對景區的文化內涵要求越來越高,景區書店成為集旅游、文化、休閑等功能于一身的文化空間,作為景區的組成部分發揮重要作用。關于實體書店的研究出現“空間轉向”,具體來說就是用文化空間理論研究書店的物質空間和文化氛圍建構,但關于景區書店的研究相對較少。學者列斐伏爾的核心觀點就是“空間的生產”。他認為,空間是一個社會的產物,每個社會都有與其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空間生產模式,并生產出與此適應的空間。[1]本文以成都散花書院為例,基于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理論以及文化消費理論進行闡述,走進散花書院的各大景區門店,并對店員和讀者進行訪談,分析其文化空間建構過程及空間消費問題。
一、人文景區與書店的空間共生關系
在眾多實體書店類型中,一種特殊的書店出現在人們的生活中,即景區書店。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景區書店作為出版產業鏈零售端的延伸應運而生,滿足出行旅客的閱讀消費需求。歸結起來,景區與書店可以說是一種互動共生的關系。
一方面,書店為人文景區增色。景區書店可以滿足讀者的信息、文化需求。人文景區區別于自然景區,更多的是給予旅游者歷史積淀深厚,有著特定的人文風情的體驗。旅游者走進景區書店,可以購買關于當地的各類書籍,豐富對景區及本地文化的認知。散花書院專注于成都本土文化的傳播,打造了各類書系,如由散花策劃、成都文聯出品、中國旅游出版社出版的“文藝成都書系”,是一套反映成都歷史、城市魅力的文化藝術作品集,從美術、詩歌、散文、書法和攝影五個方面來展現成都歷史發展的厚度和廣度。景區書店豐富了景區商業生態。在人文景區里面,商業生態內容豐富。以寬窄巷子為例,各大特色飯館、展覽館、咖啡館、特色文化展示廳等一應俱全。其中,散花書院的兩家門店見山書局與散花書屋分別位于寬巷子、窄巷子。這豐富了寬窄巷子景區的商業生態,也增加了景區的文化氣息。
另一方面,景區為書店提供載體。列斐伏爾在空間的實踐表明,這屬于感知的層面,即物質化的“空間性實踐”,是指在特定的空間中實踐活動發生的方式,它圍繞生產和再生產,以及每個作為社會形構的特征區位和空間組合。景區在規劃和建設實踐時,應該預留出書店的位置。寬窄巷子在2008年的整改和商業空間重構中,就特別邀請散花書院入駐,這對于雙方來說,是文化與商業的共贏選擇。人文景區為書店提供歷史文化資源,與書店文化功能相互呼應,可以策劃一些主題活動,相得益彰;把書店的宣傳作為景區宣傳的重要部分,用文化帶動旅游,文旅結合,吸引游客。
二、人文景區書店的傳統功能:消費的空間
景區書店作為一個物質性的實體空間,容納了圖書、文創、茶咖等產品,是旅游者文化消費的場所,是在“空間中的消費”,也即“消費的空間”。當前,散花書院有圖書消費和非圖書消費,基本門類是圖書消費。散花書院在成都市內的人文景區開了八家門店,書籍特色以成都本土文化為主,兼顧其他書籍。在見山書局內的訪談中,游客表示“這個書店書比較齊全,分類也是比較合理的,旅游買書不錯”。由此表明,景區書店作為實體書店的一種,圖書的售賣及展示是基本功能,也是十分重要的功能。在景區開設的書店,圖書消費是區別于其他商家消費的重要標簽。
其次是非圖書消費。當前實體書店的發展呈現復合式狀態,即豐富了書店內部的經營內容,成為了一個綜合性的文化消費場所。在散花書院的各大門店中,除了基本的圖書,還有大量的文創產品及茶咖服務。總的來看,圖書與非圖書產品的占比大約是6∶4。無論是在書店內售賣文創產品,形成多元化經營,還是將咖啡、軟座引入書店,其核心都是對書店空間內部結構的調整,是圍繞旅游閱讀的社會實踐和空間需求而轉變的。其中,散花書院很注重原創文創產品的研發。如印有散花LOGO的布袋,以及成都標志性花朵芙蓉花的書簽形簪子、熊貓圖案的冰箱貼等。
三、人文景區書店的轉型升級:空間的消費
人文景區的打造也是滿足旅游消費的一種空間實踐。正如列斐伏爾提到的那樣,“空間像其他商品一樣既能被生產也能被制造,空間本身也成為消費對象”。因此,空間的生產和消費邏輯變成了“空間中的生產”到“空間的生產”,從“空間中的消費”到“空間的消費”。對于散花書院的空間體驗及消費,筆者在調查和訪談中發現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類型。
(一)可以緩解焦慮的休閑空間
進入書店的人選擇了復合式的文化空間,這是特別的休閑空間。如游客在訪談中回答:“景區書店可以是一個比較閑適的空間,可以歇歇腳、喝喝水、聊聊天。旅游期間,看看書,真的很難得的休閑。”這表明,書店是景區游覽疲憊后的一個休閑去處。另一方面,也是基于現代人的焦慮。吉登斯在《現代性與自我認同》中提及“現代社會是一個飛速發展的世界……現代性帶給個人的負面影響,最為突出的就是焦慮”。[2]這一點在游客的回答中有所體現:“是的,現在城市生活繁雜,很容易浮躁,時間久了,也容易焦慮。看書時的獨處,可以適當減緩我們的焦慮。”
(二)作為懷舊的空間
懷舊在當下的社會是一種普遍的現象,懷舊心理和行為無所不在。進入20世紀50年代后,西方社會進入后工業時代并具有后現代特征,人們在充分享受現代技術文明帶來的便利的同時,面臨著個人生存意義和精神信仰的缺失,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精神尋根,在社會傳播媒介和商業環境的推動下,并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3]如在寬窄巷子的見山書局,打造的口號就是“體味少城生活,還原老成都時光”。通過古色古香的書院環境及老成都的蓋碗茶等元素提供了懷舊的空間。有游客表示“在成都的老院子,看成都的書,喝著蓋碗茶,想象一下老成都人的生活狀態,很有意思的”。
(三)帶有本地文化印記的公共空間
成都的散花書院在各大景區的門店,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開展文化活動,打造成都特色的公共空間。如見山書局基于寬窄巷子的歷史文化打造的“寬窄講堂”,定期邀請文化名人、作家等開展講座、新書發布會等,有助于當地人和游客進一步了解成都本土文化。在活動過程中,參與的讀者可以結交朋友,也可以獲取知識和愉悅的體驗。
四、結語
散花書院憑借一直以來的人文精神堅守和對自身空間結構的調整、補充,成為成都市的文化名片,并豐富了成都人文景區的文化空間需求。正如列斐伏爾所說,空間是各種社會關系發生交互后的結果,空間的生產總是和社會的政治力量、商業資本、文化傳統等要素相連。人文景區是實體書店生存的基本空間,書店的生存發展不能忽略景區對于多元空間的需求。景區作為書店的物質空間載體,書店又為人文景區增添了文化氣息。總的來說,景區書店的發展還有很大的市場前景與潛力,值得進一步關注與研究。
[1]廖衛華.消費主義視角下城市遺產旅游景觀的空間生產——成都寬窄巷子個案研究[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32-33.
[2]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39-40.
[3]理查德·沙普利.旅游社會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165.
[4]向莉.南京先鋒書店的文化空間建構[D].南京師范大學,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