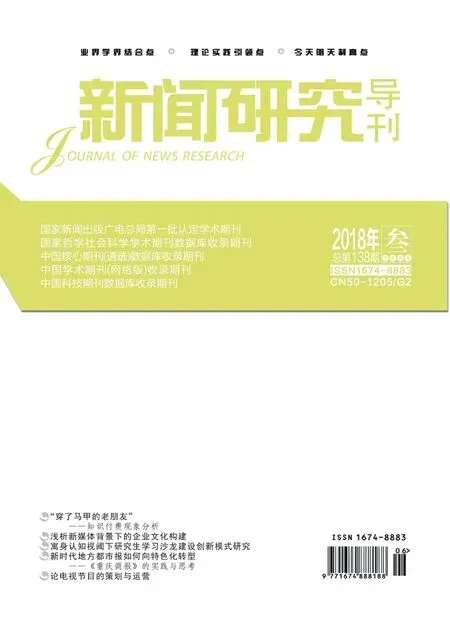《路邊野餐》詩意的亞熱帶鄉土
袁梓涵
(上海大學 數碼藝術學院動畫系,上海 201800)
《路邊野餐》無疑是2016年國產電影中的一匹黑馬,年僅27歲的導演畢贛在國際國內斬獲了眾多獎項。在當今的中國電影市場背景下,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藝術片,這部時空交錯且充滿詩意的電影讓人耳目一新,充滿詩意的長鏡頭、匪夷所思的夢境和魔幻現實主義題材將人們帶到了一片潮濕的亞熱帶土地里,這里沒有晴天,陰天和濃霧使大家分不清現實與夢境。
一、長鏡頭
在這部具有超現實主義味道的電影中,長鏡頭對詩意的營造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電影新浪潮之父”巴贊認為:“敘事的真實性是與感性的真實性針鋒相對的,而感性的真實性是首先來自空間的真實。”長鏡頭的美學特征源于它的真實性,長鏡頭再現了現實事物的自然流程,因而更有真實感。畢贛的《路邊野餐》致敬塔科夫斯基,塔科夫斯基的詩意長鏡頭注重意境的表達而減少敘事。在《路邊野餐》中,這些長鏡頭將觀眾悄無聲息地帶到了這個神秘的地方,讓觀眾從客觀的角度去看陳升的世界。
整個影片有十幾個長鏡頭,每段都是十分平淡、生活化的片段。影片一開始便是一個一分半鐘的長鏡頭,環繞式平搖的運動鏡頭,一閃一閃的燈,咳嗽的聲音,診所里老醫生光蓮在給陳升打針,兩人在閑聊。這一切將人們帶入這種緩慢的生活節奏中,這個鏡頭也奠定了整個影片的基調。
長鏡頭里大量使用了平搖旋轉的運動鏡頭,像是在模仿時鐘旋轉和時間的流逝,具有意象的鏡頭運動無疑增加了影片的詩意。在塔科夫斯基的《犧牲》里大量運用了長鏡頭,而《路邊野餐》也有類似的表現手法,如在老歪去取車、花和尚來接小衛衛、陳升問老歪衛衛的去向等鏡頭。
不得不提的是《路邊野餐》長達40分鐘的長鏡頭,畢贛在接受采訪的時候說過:“而為什么用到長鏡頭,因為我覺得時間就像一只隱形的鳥一樣,我能碰到它、看到它,但我怎么樣才能讓別人也能看到它呢,首先我就需要用一個籠子把它關在里邊,這個籠子就是長鏡頭的段落。”在蕩麥這個地方,有著現在、過去和未來的時間穿插的魔幻力量,為了將其塑造到極致,增強其真實感,導演大膽運用連續的長鏡頭加以表現。這個長鏡頭采用了跟拍的形式,營造一種客觀視角,使觀眾身臨其境般感受蕩麥這個神秘領域的魔力。低成本和非職業演員、畫質低等問題,導致這個長鏡頭讓人產生暈眩感。演員調度不夠,其中有兩段空鏡頭可以明顯看出攝影師拿著攝影機在行走,使觀眾跳出這個“籠子”,這無疑是給電影減分的,但這也是一次偉大的嘗試。
二、語言
《路邊野餐》采用的是貴州鎮遠當地的方言,即便是陳升旁白的詩句也是方言展現出來的。在歷來的電影里很少有旁白詩句也采用方言,這是在“視聽”的“聽”里給予觀眾新穎、奇特的感受。一個鄉村醫生有著對詩的熱愛,用自己最真實的聲音讀出來,其中蘊含的詩意具有極強的感染力。
方言在1990年之后漸漸出現在電影里,如《秋菊打官司》《小武》《瘋狂的石頭》等,它是現實主義題材電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增強了電影的感染力,提升了電影的藝術魅力。
方言對話增強了電影的真實感。《路邊野餐》是發生在貴州黔東地區的故事,為了讓觀眾沉浸在這片亞熱帶鄉土中,影片鏡頭以紀錄性的客觀長鏡頭為主。另外,方言是展現當地人最真實的一面的基礎,其不僅能展現貴州這塊鄉土的文化、生活氣息,讓觀眾觸及其質感,還可以讓觀眾看到演員內心深處的情感。影片中大霧、山川、摩托、打牌、看病等風景和情節都表現出貴州鎮遠的鄉土氣息,最后再加上當地方言,視聽結合才做到了極致。
方言的對話加強了對人物的性格塑造,方言像一個人的精氣神,也像外語電影,人們更愿意聽原聲版而不是國語版,國語配音會讓外語電影的文化差異、人物性格表達等大打折扣。要表現角色的性格特點、行為動作、穿著打扮等,語言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
三、夢境
夢境也是這部影片的一大特色,畢贛將夢境和現實連接起來,通過長鏡頭讓觀眾分不清哪里是夢境哪里是現實,在不知不覺中走進夢境。
第一個夢境是陳升晚上睡覺夢到自己在一艘船上,水里漂著母親的繡花鞋。在這一段中,鏡頭向睡著的陳升推進,直到耳朵的大特寫再拉出來。這看起來像一個鏡頭,但其實是兩個鏡頭拼接起來的。但在導演看來這就是一個長鏡頭,使陳升從現實到夢境的過渡變得更加客觀,將夢境和現實連接起來,顯得更加真實。
導演對夢境的表達最受矚目的是后半部分長達40分鐘的長鏡頭,這個長鏡頭是陳升去鎮遠的路上做的一個夢。這個長鏡頭一開始是大衛衛的女朋友坐了其他人的車去了鎮上,接著陳升從山里走出來坐上了大衛衛的車去找會吹蘆笙的廟人。導演悄無聲息地將觀眾帶入陳升的夢里,直到唱完送給逝去的妻子的歌后,大衛衛送陳升離開時陳升和觀眾才知道這是一個夢,他遇到了還沒瘋掉的酒鬼,還未死去的妻子,長大后的衛衛的女朋友,將光蓮送給林愛人的磁帶送給了還未死去的妻子。酒鬼在凱里瘋跑時手肘上綁著木棍,在蕩麥大衛衛叫陳升腋下綁上兩根木棍,防止被野人偷襲。在這個長鏡頭里,陳升看到了過去和未來,既是昨日的記憶,也有明天的幻想。在這個夢境里,我們看到了陳升內心的愛情、欲望、懷念。畢贛選擇用長鏡頭表達夢境的完整性、突出夢境的真實性,現實與夢境交叉使這部影片充滿詩意。
四、魔幻現實題材
除了長鏡頭和夢境,在畢贛的這部電影中魔幻現實主義是另一個吸睛之處。在魔幻現實主義中,人鬼難分、幻覺和現實相混,將魔幻和現實融為一體,在魔幻中又不失真實。在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中滿是離奇怪誕的情節和命運,阿根廷著名文學評論家安徒生·因貝特所指出的:“在魔幻現實主義中,作者的根本目的是借助魔幻表現現實,而不是把魔幻當成現實來表現。”
在這部影片中,多次說到從未見過的野人。在廣播中野人的形象被塑造成全身棕色毛發,眼睛發光,喉嚨里發出打雷的聲音的生物,十分奇特,進一步突出陳升生活的這片亞熱帶土地的神秘感和魔幻文化。野人把現實和夢境緊密結合起來,小衛衛害怕在電視上看到的野人,大衛衛送陳升走的時候,教陳升防范野人的方法。廣播里那個在車禍中被撞死的人是老醫生的兒子,在夢境中可以看到肇事司機就是現實中的瘋子,而野人其實是陳升過去的背影。
另一個是火車這個意象。火車第一次出現是在老歪家里。花和尚來到老歪家里,小衛衛問花和尚他家里是不是有很多表,慢慢地出現火車的聲音,且火車的聲音逐漸變大。鏡頭一直向左平搖,一輛綠皮火車在房間的墻上飛馳,火車一直開著,像是沒有盡頭。這個鏡頭極具想象力,讓觀眾耳目一新。人物和火車之間沒有交流,而在火車之后緊接著是陳升夢見母親的繡花鞋。我們從這里可以看出火車是連接現實和夢境的工具。第二次是陳升坐上去蕩麥的火車,陳升來到蕩麥遇到了很多奇妙的事情,明明候車廳里有很多人,但火車上空蕩蕩的只有陳升一個人,這是陳升通向自己夢境的火車,或者說是連接過去和未來的時間工具。
《路邊野餐》是一部才華橫溢的詩意電影,畢贛對情感的理解有著獨特的表達。在畢贛的長鏡頭下,黔東南的語言、琢磨不透的現實與夢境賦予這種亞熱帶鄉土文化沉甸甸的厚重感,值得人們細細品味,令人回味無窮。
[1]于航.淺析長鏡頭在影視作品中的美學特征[J].前沿,2013(6):173-174.
[2]周文萍.詩意蕩漾的《路邊野餐》[J].粵海風,2017(1):92-101.
[3]曹柳鶯.視聽情境建構與長鏡頭美學——論《路邊野餐》作為新影像的可能[J].當代電影,2016(8):25-27.
[4]畢贛,葉航.以無限接近寫實的方式通往夢幻之地——訪《路邊野餐》導演畢贛[J].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16(3):9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