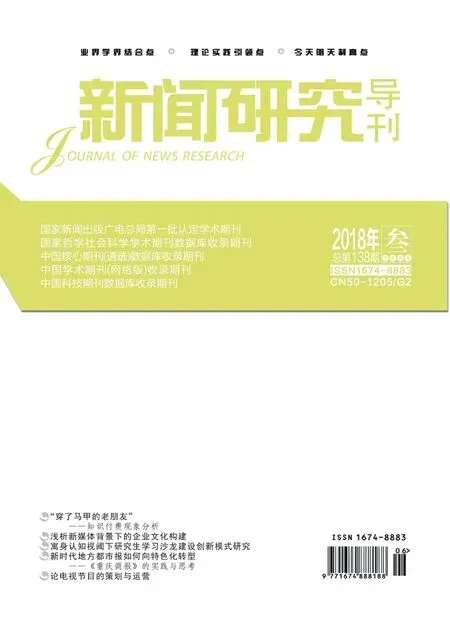紙質閱讀在當代校園中的困境和出路
趙 靜
(讀者出版集團有限公司,甘肅 蘭州 730000)
回顧20世紀的中國,重要時代的開創都是由紙質印刷物來啟迪民智、傳遞思想的。從清末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到五四時期的《新青年》,從朦朧詩到鄉土小說,甚至可以說沒有紙質印刷就沒有中國近代一個個新思潮、新時代的開創。紙質印刷是20世紀思想舞臺上最耀眼的明星。筆者出生于20世紀70年代末,成長于20世紀八九十年代,在整個小學、中學時代,紙質書都是筆者精神世界成長的重要導師。
如今是一個電子產品普遍、碎片化閱讀泛濫的時代。校園里手機已經基本普及,各種電子媒體、社交軟件占據著中學生甚至小學生的業余時間。電子媒介已經充斥于整個社會,學校也未能幸免,甚至稱得上是“重災區”。美國中學生過去的主要社交方式是舞會和派對,而現在的主要社交方式則是各種網絡社交媒體;如今中國學生的社交方式也是如此。一切依賴手機、一切依賴電腦已經是中學生生活的常態。筆者一個朋友的女兒上小學四年級,每天晚上做作業都離不開手機、iPad——看老師布置的作業、查資料、問同學題等。這一代的年輕人對手機有一種天然的依賴。本來要看看新聞,卻順便跟朋友聊兩句;本來要發個文件,卻被騰訊推薦的一個視頻吸引。手機就是導致人們的時間碎片化的元兇。時間就在看似充實、多樣化的生活中不知不覺地流失。我們不帶著手機就去旅游,怎么拍照、怎么發朋友圈?我們不帶著手機就去上班,怎么跟客戶聯系、怎么收發郵件?同樣,現在很多孩子雖然被禁止帶手機上學,但他們每天照樣一回家就發動態、發朋友圈。中學校園雖然禁止使用手機,但智能手機仍然無處不在。時間被碎片化導致的后果之一就是閱讀的缺失。
有人會問:我在網上可以看到更多的文章啊,怎么能說缺失了呢?盤點一下網上最吸引年輕人的文章,歸納起來,網絡閱讀的主要特點是“短、平、快”。首先是題目吸引眼球的,看到《紅與黑》《寒冬夜行人》等書名,大部分學生甚至都不會打開頁面,一翻就過去了,他們也許對《太子妃升職記》這樣直白的題目更感興趣。其次,文章要一下子吸引人,那種先用大段的景物描寫或人物刻畫來開頭的文章同樣會被毫不留情地拒絕,只有文章一開頭就用各種奇詞異句把讀者牢牢套住,才能讓年少的讀者看下去。最后,文章一定要短,校園讀者本來時間就緊張,加之可選擇的文章太多了,如果文章太長,他們往往沒有耐心看下去,會不停地往后翻。以往的人們有耐心去看一本大部頭的書,現在的年輕人卻很少有時間去看一篇稍微長點的文章。木心的一首詩《從前慢》中“從前的日色變得慢/車,馬,郵件都慢/一生只夠愛一個人”,這樣的意境讓人很是向往。現在的人不那樣,不是人變了,是時代變了。紙質閱讀(或者稱慢閱讀)要重新進入大眾視野,也要像這首詩一樣,重新喚起讀者對“慢”的理解以及對“慢”的向往。慢閱讀就是有深度的閱讀,有深度才能有質量、有重量;相對而言,碎片化閱讀有寬度、廣度,卻缺乏力度、深度。有評論指出,碎片化讓閱讀變“輕”的同時,也讓真正有效的閱讀變得艱難,對個人的要求越來越高。有關“碎片化閱讀”,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還專門做了一項調查,受訪人群中,44.3%的受訪者經常通過網絡平臺接受碎片化知識,65.3%的受訪者認為碎片化閱讀方便快捷。
就如萬維鋼在《上網能避免淺薄嗎》一文中所敘述的:“現在已經沒人能看完《戰爭與和平》了。高質量的讀書要把自己沉浸在書中,有的地方反復看,甚至還要記筆記。這種讀法似乎有點喪失自我,好像成了書本的奴隸。而上網則是一個居高臨下的姿態,我們游離在內容之外,面對眾多等著被臨幸的超鏈接想點哪篇從心所欲。可是在 Nicholas Carr的The Shallows(《淺薄》)這本書看來,上網者才是真正的奴隸。相對于讀書,網絡閱讀使我們能記住的信息更少,理解能力和創造力下降,形成不了知識體系。互聯網把我們的大腦變淺薄了。”
在這個碎片化閱讀的時代,是否還有必要提倡紙質閱讀呢?是否還有必要推進學校中的紙質閱讀呢?
筆者認為,喚回校園的紙質閱讀是十分必要的。首先,重網絡閱讀、輕紙質閱讀等現象影響了青年人的讀書興趣,使讀書成為一種被動和強制性的行為,無法感受到蘊含其中的無盡樂趣。閱讀的樂趣和意義就在于全身心地投入,與作者交談。如果只是被標題牽著走,被網絡寫手牽著走,走馬觀花地看熱鬧、看新奇,而缺乏自己的精神參與,閱讀就永遠流于淺薄,缺少收獲。其次,紙質閱讀可以讓學生更加專注于書本,紙質書籍、雜志不給你機會找借口休息一會兒看看視頻、有重要的事情跟朋友聊聊等。紙質書籍決定了讀書就是讀書,你可以在書籍上寫感想,甚至可以像李敖一樣把書撕成一頁一頁歸類保存。讀紙質書帶給人一種儀式感,能夠讓青年人靜下心來,跟自己對話,用自己的頭腦思考,不一定非要看到什么新奇的東西,但是一定會有收獲。
雖然我們都知道紙質閱讀的好處,但是,智能手機還是占領著校園。如何引導學生把視線從手機屏上挪開,轉向紙質讀物,為紙質出版物找到一條出路呢?
第一,應該堅持“內容為王”。不論做書,還是辦刊,內容要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不能盲目迎合讀者,將紙質書做得“速食化”。精彩的內容最終會被認可,面對學生讀者,內容更要精益求精,把好的思想、正確的人生觀作為衡量書籍優劣的標準。與此同時,也要研究讀者群的心理特征。就校園讀者來說,內容要將知識性與趣味性統一起來。以《讀者》(校園版)為例,其創刊時就將趣味性和知識性作為辦刊宗旨,不斷開創新欄目,將體育、電影、軍事、動漫等中學生感興趣的方面做成欄目。同時,貼近中學生的生活,校園版有“筆會”“我的中學時代”“留在時光里的記憶”等原創欄目,讓學生寫自己的生活和學習。還可以開展征文大賽等形式多樣的活動,調動學生的寫作積極性,從自身的寫作著手提升他們對紙質讀物的興趣。4月23日是“世界讀書日”,國內領先的數字閱讀和原創IP孵化平臺——網易云閱讀聯合國內六大高校學生社團,公開發布了《2018校園創作者白皮書》,再次為公眾帶來有關全民閱讀的最新觀察和思考。據白皮書統計,在創作內容上,校園創作者也有自己特殊的喜好,與成年人對都市職場等寫實題材的偏好不同,與二次元相關的同人文最受校園文學創作者歡迎,其占比達到71%;而在創作形式上,他們有73%的傾向于微小說或短篇小說。據介紹,這些傾向也和初、高中生的動漫興趣較為突出相適應,而處于初、高中階段的創作者受限于筆力,在創作中也更依賴于借鑒和其他文字作品的衍生及再創作。紙質媒介應該就這方面組織校園寫作,發現校園寫手。《讀者》(校園版)在2018年舉行了“我的動漫世界”征文比賽,來稿頗豐,充分動員了中學生的寫作熱情。
第二,需要學校和家庭的配合,得到家長的支持。在沒有智能手機甚至沒有電視、電影,只有書籍作為傳遞精神文化的時代,人們會自然而然地被書刊吸引,那時人們依靠想象力來獲取圖像。有了科技提供的各種虛幻的圖像,人們就不需要用自己的想象力去構建圖像了,這正符合人類追求舒適的天性,但也讓人類的想象力逐漸退化。有科學家預言,人類的智力水平正隨著科技的發展而退化,其中包括想象力。所以,我們需要采取行動:去學校給老師和家長們講課,指出紙質閱讀對一個人邏輯思維養成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給學生們講閱讀紙質讀物的重要性、剖析名著經典的有趣之處、講一些關于書的有趣故事,從而激起學生們讀書的興趣。筆者所在的《讀者》(校園版)在這方面就做了很多嘗試,校園版的演講者從學生的興趣出發,然后引導他們去看某本書或某期雜志。我們雜志曾進行過數次全國巡講,反響頗為不錯,很多學生都訂了雜志,并成為我們的校園通訊員。所以,對于學生群體,我們一定要多加了解,知道他們的所思所想,再加以正確引導,才會收到好的效果。畢竟學生的思想是非常開放的,會接受他們認為有價值的東西。對于紙質書籍的優點,他們基本會接受的。
第三,需要借助全民閱讀這股東風推動校園紙質閱讀的宣傳。“全民閱讀”活動是中央宣傳部、中央文明辦和新聞出版總署貫徹落實黨的十六大關于建設學習型社會要求的一項重要舉措。現在全國各地組織了很多書友會,但大多是針對成人的。面向校園的紙媒要開展一些校園讀書會,定期介紹好書給中學生。與校園聯合辦讀書課,與學生一起討論怎樣讀書、讀什么書是很有必要的,這既可以調動學生課外閱讀的積極性,也可以豐富他們的校園生活。形式可以多種多樣:做流動書籍站——將各個學校的讀書角聯系起來,互換書籍;捐贈書刊——將出版社出版的好書捐到學校的圖書角,讓學生們了解更多的好書、好刊;開展讀書研討會——學生們跟編輯面對面地提建議和意見,這樣可以更好地了解消費群體的需求,從而做出符合市場需要的產品;組織校園通訊員——長期關注校園動態和校園文化,增加與校園通訊員的互動,掌握學生們不斷變化的心理。
總之,紙質讀物在當代校園的出路在于“走出去”——走出出版社、走出溫室,走到校園、走進家庭。進入校園和社會后,觀察和了解讀者群、宣傳和介紹自己的產品是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