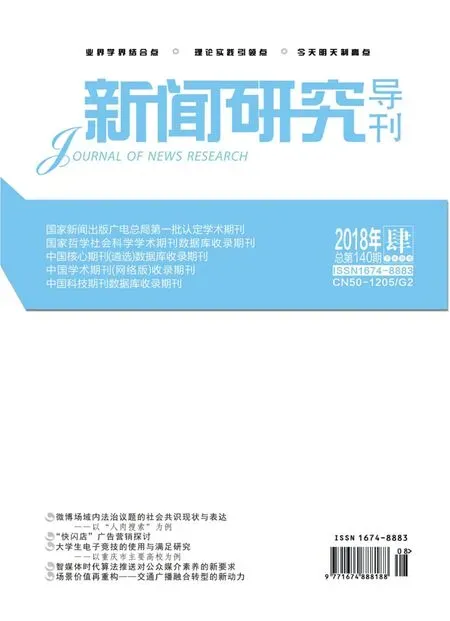新媒體環境下的受眾二重性
楊曦昊
(云南財經大學 傳媒學院,云南 昆明 650221)
新媒體有很強的交互性、即時性、虛擬性,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進入21世紀后,新媒體概念的邊界也在不斷擴大。隨著媒介形態的不斷發展,傳統意義上對于受眾按照職業、地理位置、收入等的劃分方法已經不容易被接受。
丹尼斯·麥奎爾在《受眾分析》中提出受眾二重性概念,即受眾的需求是由媒介創造的需求與受眾自發的需求兩個維度組成。在新媒體環境下,技術賦予了媒介與受眾更多的權力。在受眾需求的產生與發展過程中,不能僅僅考慮到受眾個體本身的因素,更應考慮媒介在這一過程中扮演的角色。
一、媒介創造的需求
受眾通過媒介獲取真實世界的信息,而媒介通過過濾、篩選信息營造出一種虛擬的信息環境,受眾不自覺地認為這一獲取信息的模式完全出于自身的需求與自我的愿景。
(一)媒介的訴求
媒介系統由諸多的媒介組織構成,而媒介組織背后大都隱藏著資本的身影。在傳播信息的過程中,媒介組織通常會使用多種傳播與宣傳技巧,隱藏自身的核心訴求,創造出受眾需求這一概念,借此掩飾其對受眾的影響。這種需求是一種“虛假需求”,是一種被人為刺激出來的需求,這種需求的滿足不過是占據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獲利而已。[1]階級的概念被刻意淡化,媒介潛移默化地灌輸這是一種“自然而成”的思想,也就是受眾對于媒介的需求全部源于自身的需求。既然是“自然而成”的行為,那么它就無須被修正,也無法被修正,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利益沖突也就在無形中被消解了。
達拉斯·斯邁斯的“受眾商品論”指出,受眾在信息傳播過程中,其實質已經是勞動商品,而媒介組織的生存邏輯即剝削受眾的剩余價值。而在當下,受眾不僅是“商品”,受眾通過技術擁有了更多的權力,在獲得權力的過程中,已經演變成了“生產型消費者”。新的角色意味著受眾不再是被物化的商品,而是積極的意義生產者。受眾不再局限于對文本的消費,同時他們也參與信息的流通與文本生產。媒介組織只需適時、隱晦地引導即可,就能將受眾的勞動產品奪走。最后,受眾要額外花費金錢去購買他們自己創造的產品。
(二)資本的創造
從報紙到廣播、電視再到互聯網,資本的媒介組織控制并構建了大眾文化。媒介按照資本的核心利益,引導并培育受眾接受特定的文化,就如赫伯特·席勒的文化帝國主義觀點,國際文化生產與發行結構的不平等通過何種機制,致使一種新形態的超國家范疇的支配現象得以具體展現、流行于世并得到強化。[2]這種超國家范疇存在的形式就是資本。資本控制受眾對于文本的解讀,解讀的方法都是基于之前所獲得的經驗、認知等,而受眾接觸的信息都是被資本篩選過的。
例如,新媒體環境下的泛娛樂化現象,媒介組織在資本利潤的驅動下,不斷地催發受眾個體的自我膨脹,而這個“自我”只遵循單純的快樂原則,盲目追求滿足。受眾的理性思考與自我控制力水平下降。換言之,資本控制的媒介組織在促進強刺激類信息(性、暴力等)泛濫的過程中,更能夠控制和引導盲目的受眾,使之退化為烏合之眾,讓受眾沉浸在媒介組織創造的需求之中,最后得到由資本控制的大眾文化。這樣的大眾文化是資產階級的利益與意志的體現,其目的是讓大眾很難認識到自己是被剝削、被犧牲的對象。
而新媒體環境下的資本形成了多個傳媒集團,如時代華納、迪士尼等,這些超級媒介集團控制并引導大眾文化的發展方向。他們控制媒介的方式多種多樣,如通過投資、控股等方式控制擁有新技術的企業或公司。就世界范圍來說,美國的文化輸出無疑是最好的例證。在新媒體技術的加持下,美國的價值觀被輸送到全世界,并引起很多其他國家人民的共鳴與認同。
二、受眾自發的需求
受眾對于信息、情感等需求是接觸媒介的原始動力,而在新媒體時代,這種需求被放大了。在這個過程中受眾對于自身需求的表達,也因為權力與地位的上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滿足。
(一)個體與群體壓力
受眾自發的需求,從心理需求層面來看,其涉及多種情感的共存而維持的狀態,如紐科姆的對稱理論認為,人都有對平衡狀態的需要,這種需求常常表現為受眾對于群體、信息等的接觸行為。人們對于信息的需求通過媒介獲得滿足,并由此形成了不同屬性、傾向的受眾,而諸多不同特質的受眾則構成了整個社會的基石。在這種環境下,單個、離散的個體自然會形成特定的社會認同模式,遵守在群體中的行為規范,追隨群體的意見,即使這種意見或者規范與他們內心認同的信息相抵觸。
傳統媒體環境下,人們接觸信息的渠道有限。面對來自群體的壓力,媒介組織通常會在其中發揮協調作用,進行調控和引導,借此維持受眾自身虛假的平衡狀態,忽略受眾自身的需求,最終個體的選擇屈從于群體壓力。
而在新媒體環境下,受眾擁有更多選擇信息的權力。受眾對于平衡狀態的需求依然存在,但每個受眾都可以擁有獨特的標準與傾向。群體的壓力不能再迫使受眾被動地接受群體規定的取向與標準,受眾的獨立性不再受到壓制,而是在技術賦權下得到了充分的肯定與支持。
(二)受眾的文化重構
技術的發展實現了受眾自主生產并傳播信息,實現了受眾從單一、被動的信息接收者向傳播者的角色轉變。同時,群體對于匿名受眾的壓力減少,受眾能更自主地闡釋意見。我們可以認為技術使得媒介回歸到原本作為信息傳遞渠道的意義,受眾更多地按照興趣,即個人本身的需求,選擇性接觸與篩選諸多媒介中的信息內容。
而受眾的劃分,也會隨著受眾不同的選擇而發生變化。大眾文化這一概念將會消解,細分成諸多的亞文化,每一種文化都會由不同數量、不同背景,但具有某一相同特征的受眾重構。正如威廉斯指出的那樣,我們所說的“共同”,必須是強調接近于參與的積極社群。就此來說,現存社會實在沒有共同文化,雖然我們仍以共同文化之名對抗現存社會。每一種擁有某一特質的受眾群體都有自己獨有并有高度活躍性的文化。就如赫伯特·甘斯所提及的“品味文化”,受眾以趨于一致的興趣為基礎,而不是基于共同的地域或社會背景。
因此,新媒體背景下進行重構的大眾文化不再是一個完整而規制的整體,而呈現為一系列離散的、各不相同的亞文化。過去的大眾文化就好像一個定制的具有光滑邊緣的模具,而這個模具是由資本控制的媒介設計與制作的,其邊際是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正在重構的大眾文化則是一系列各不相同的小模具,每一個小模具都是不同的亞文化,最后這些小模具有機地構成了一個大模具,這個大模具的邊緣不再光滑,其形態也不可預見,而邊際則是受眾意志的體現。
[1]丹尼斯·麥奎爾(美).受眾分析[M].劉燕南,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17.
[2]丹·席勒(美).傳播理論史:回歸勞動[M].馮建三,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117.
[3]曹海峰.受眾需求與文化認同——試論國產繪本的發展瓶頸與應對策略[J].中國編輯,2017(11):21-25.
[4]孫曉.媒體消費主義與媒介文化[J].青年記者,2016(13):63-64.
[5]姬德強.誰的權力場域?——“韓方之爭”與微博的政治經濟學[J].新聞大學,2013(05):38-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