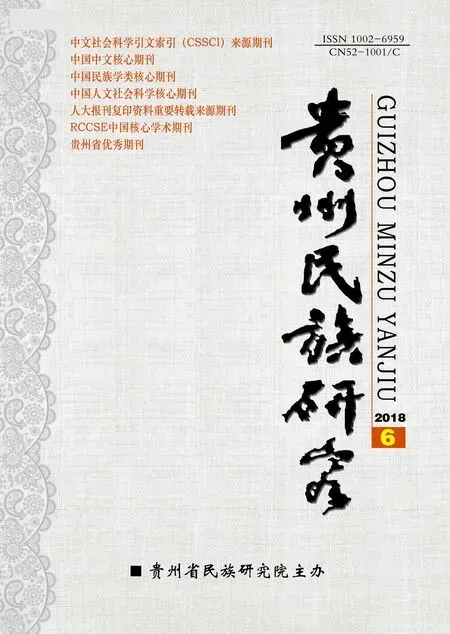略論西部民族地區流域環境保護的法制理論
寇瀟岑 劉 峰
(1.西安交通大學 法學院,陜西·西安 710049;2.西北政法大學 行政法學院,陜西·西安 710122)
一、西部民族地區流域環境保護概述
在地質學范疇中,地下水水線及其地表水域的區域的總體稱謂為流域,一般而言,對于流域的范圍的界定,僅在于其地表部分的區域。西部少數民族群落因其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原始性與封閉性,少數民族常常擇水而居,其生產和生活方式對于其所處的自然環境具有天然的依賴性。而且,西部生態系統常常以河流、湖泊為生態中心,流域生態環境對于西部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西部流域法制理論建設對于西部生態環境保護具有積極的作用。
在現實情況中,西部民族地區生態系統的問題可以歸為兩類:其一,河流生態系統遭到嚴重污染,其二較為頻繁持續的生態破壞。這兩種問題的表現形式為自然濕地遭受破壞,致使其作為生態調節的作用失去效力,進而使得西部少數民族所居地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致使其所依賴的自然資源損失殆盡,嚴重影響了西部少數民族的生存和發展。現代文明的發展,水電開發、水資源的跨區調配等現代經濟對于西部少數民族地區流域環境的進一步干預和破壞,致使西部少數民族地區流域生態環境的現狀不容樂觀。在法制層面上,我國現行的國民經濟考核制度,對于經濟數據增長的關注大于對于環境保護的關注,西部民族地區流域生態數據在國民經濟數據中往往被忽視,使西部民族地區流域破壞問題得不到有效重視。再者,我國關于環保法律對于環境資源的標準效力的規定在上下位法之間存在標準效力的沖突,如我國《環境保護法》和《水污染防治法》對于污染水資源所負責任就有完全不同的表述,這使得對于西部民族地區流域治理在法律監管的層面缺乏切實有效的手段,加劇了流域生態的破壞。這些西部民族地區生態流域破壞的問題急需國家從法制層面上進一步規范和完善。
我國已在區域流域法律治理方面進行一系列的法制保護探索和嘗試,如《額爾齊斯河流域生態環境保護條例》,以及《青海湖生態流域環境保護條例》等法規的實施從一定程度上保護了西部地區少數民族地區流域生態環境。但如上探索的法律模式是建立在區域管理的模式之上,現實當中西部少數民族流域生態環境常常以天然的河流、湖泊等自然水系為中心構成生態系統,在區域管理模式之下,天然整體的河流、湖泊等流域生態系統常常被分別切割成若干區域進行管理,這樣的制度設計造成了流域保護的權責不清、流域治理效率低下以及缺乏整體有效的治理機制等問題,在當今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之間很難找到平衡點。因此,將現有的對于西部少數民族流域治理的法制模式由劃區域的、分割條塊的管理模式轉變為全流域的、整體的法制管理模式,對于現有西部民族地區流域治理模式進行改革、重構具有現實的必要性。對于西部民族地區生態環境法制模式創新的首要的問題就是對法制理論進行研究,對于法制過程中各方參與人的權利義務進行設定,這是西部少數民族地區法制研究的基礎。
二、西部民族地區生態環境保護的流域模式
我國西部民族地區流域資源豐富,分布廣泛。從地理區位進行觀察,我國主要的黃河水系、長江水系均發源自我國西部民族地區,從源頭對于流域生態進行保護與治理對于我國中下游地區、乃至我國整體的水資源保護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流域生態系統并不局限于自然環境本身,它是自然環境與人類經濟社會的綜合體。流域的經過將不同物理條件的地理區域相互連接,進而連接各個地理區域之上的經濟社會系統,并以此為基礎構成完整的流域生態系統的閉環。由此,分析西部民族地區流域生態系統應從自然和經濟社會兩個重要的維度進行分析。西部民族地區內自然流域類型多樣,既有內陸型流域,如塔里木河、黑河和石羊河,其中塔里木河是我國最大的內陸型流域水系,也有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的發源水系。其所在自然環境人煙稀少,大多為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因此其生態環境受到在其周圍聚居的民族生產、生活方式的制約。西部少數民族生產、生活方式常常較為落后,對于自然環境的消耗也較為有限;而且自然環境對于少數民族生存環境具有直接的作用,因此少數民族基于生存的需要對于自然環境具有天然的保護意識。反觀下游的經濟發達地區,生產和生活方式的先進性導致將生態環境與生存環境的因果關系變得模糊不清,這使得下游地區對于流域生態資源的消耗常常是破環型的、不計后果的。
觀察流域上下游的自然和經濟社會的不同情況可以發現流域生態具有整體性和不平衡性,進而可得出流域模式具有三個屬性。首先,流域生態系統具有整體統一性。流域生態系統自然環境、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等因素具有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特征:一方面,流域生態的自然環境是經濟發展的基礎,其為經濟發展提供了物質資源和發展的邊界;另一方面,經濟發展可以促進自然資源的保護和利用。將此種辯證關系推演到流域生態環境系統的其他方面,如地理位置、主體與分支之間亦具有此種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的辯證關系。其次,流域生態系統是分層次的相互連接的系統。流域生態系統以自然屬性為最基礎的層次,經濟、社會層次在其之上又構建出第二個層次,進而在對其進行監管的法律層面又為之構建了監管層次。在網絡性方面,流域生態系統不僅在地理環境上干流與支流形成網絡,在其社會屬性以及法律監管屬性方面,流域生態型也體現為具有網絡性。最后,流域生態系統具有非穩定性。流域生態系統并不是如表面看來的靜止,它體現出一種動態的靜止和平衡,即流域生態系統中的各個因素之間處于相互變化之中,如流域中上游生態資源消耗的數量決定了下游生態自然消耗的限度,兩者資源消耗的總量不變,但在該消耗層次中上下游之間呈現出不穩定的特征。人類因素是流域生態系統中最為活躍、積極的因素,流域生態系統沿途經歷著人類社會不同層次的發展,位于流域上游的西部民族地區,其人類因素多表現為積極地對于生態環境的依賴和保護;而在下游地區,人類工業文明的發展,其人類因素表現為對于生態系統資源的消耗和破壞。但隨著社會文明的發展和進步,下游人類文明在破環自然環境之后,對于自然生態環境的規律有了充分的認識,逐漸意識到自然環境的重要性,隨之加強了自然環境的保護,而在上游的少數民族的生產、生活方式較為原始、落后,這在一程度上加劇了對于環境的破壞,這種破環與保護的動態平衡關系呈現出非穩定的特征,亦是對流域生態環境整體性和層次性的詮釋。
西部民族地區流域生態系統并不等同于西部地區生態系統,生態系統是一定空間和時間里的生物及其所生存環境的集合。西部流域生態系統概念的內涵顯然較生態系系統小。首先,西部民族地區是指我國新疆、廣西、內蒙古、寧夏、重慶、云南、貴州、甘肅、四川、陜西、西藏、青海十二個少數民族聚居的省市和自治區,其流域主要是指以西部地區河流為基礎,各個分支的集水區域內的生態系統的總稱。其次,西部民族流域生態系統不僅包括河流生態系統,河流沿途的濕地森林、草原等生態系統也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如上文所述,流域生態系統是一個立體的、動態的、多分支生態系統,在西部民族地區流域生態系統的層次上,濕地森林、草原等生態系統是其最重要的層次分支,濕地森林、草原等生態系統相互聯系、亦相互影響,又在整體上構成了西部民族地區流域生態系統。最后,在西部民族地區流域生態系統中,河流生態系統具有標志性的指示作用,河流生態系統通過河道、濕地、棲息地等子生態系統發揮其生態功能,這是其在功能上的層次分支。
三、西部民族地區流域生態環境的歷史觀
西部民族地區流域生態環境屬于我國流域生態環境的一個子系統,分析其歷史觀應先從總體的流域生態環境系統角度進行研究。
首先,原始社會人類活動早期對于流域生態環境的影響。人類活動早期主要的生產、生活方式為采集、狩獵等原始的方式,在這一時期,生產力的發展還處于較為低下的階段,勞動工具以原始的石器為主,勞動的對象以自然環境中可取的動物或植物資源為主。生產力的低下造成了人類對于自然擴張能力的低下,同時反向限制了人類自身的生存和發展。由此,人對于流域生態環境的破壞能力較弱,對于流域生態環境的破壞程度較低。但這并不意味著人類活動對于流域生態環境沒有影響,由于人類自身對于知識掌握的匱乏也常常造成流域生態環境的破環,如我國歷史上早期治水“用堵不用疏”的方法,加劇了流域生態環境的破壞。
其次,古代社會人類活動對于流域生態環境的影響。古代人類社會的生產、生活方式分為農耕與游牧。在游牧方式中,人類活動充分利用自然規律,以自然時間、空間資源為出發點為人類獲取更多的生存資源,可以說游牧的生產、生活方式是與流域生態環境相輔相生的,其對生態環境的保護就有積極的作用。但游牧生產、生活發展到后期,隨著生產力的提高產生了定居的畜牧方式,此種生產方式對于生態環境的依賴減少,同時對于生態環境的破壞增加。為此,早期少數游牧民族對于生態環境作出了明確的保護性規定,如蒙古族的《阿勒坦汗法典》 《衛特拉法典》等。在農耕方式中,人類活動以種植和養殖為活動內容,生產力大幅度提升,已經超出種植者自身的需要,進而促進交換的出現以及社會經濟的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超出了自給自足的限制。人類對于自然資源擴張能力的增強,隨之而來的是對于流域生態環境的破環,如流域生態系統內植被的破壞,濫砍濫伐,造成水土流失,進一步危害流域生態環境。
最后,現代社會人類活動對于流域生態環境的影響。現代社會以工業文明為基礎,社會生產力水平較之以前有了大幅提高。同時,人類對于流域生態環境的破壞也達到了歷史上新的程度。科技將人類的生產力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這使得人類對自然資源的索取和利用的程度較之前社會有了很大提升,造成了生態系統資源嚴重的破壞、損失,這造成了生態環境危機。在流域生態環境方面,其河流、濕地等子生態系統相互調節的能力由于人類的過度開發而喪失自我調節、自我修復的能力。生態環境危機的實質是人類對自然資源的所求超出自然界供給,人力開發自然界能力發展超出自然界產出供給速度所造成的危機。這種危機的發展方式常常是沿著流域生態系統逐步擴散,由上游向下游,由社會發達地區擴散到社會文明相對落后的地區。由于人類對于流域生態環境破環的認識就有差異性,經濟社會發達地區對于生態環境的補救措施較經濟社會落后地區更為積極,這使得經濟社會欠發達地區常常是生態環境破環最為嚴重的地區。
西部民族地區流域環境的歷史按人類歷史活動進行分析,亦可分為原始、古代和現代三個時期。與流域生態環境發展的歷史相區別的是,我國現今西部民族地區,生產生活方式呈現出農耕、畜牧與現代工業文明相互交織的情形,一部分西部少數民族的生產、生活方式還遵循擇水而居,并采用原始的生產、生活方式,其對于流域生態環境破壞較小。但在西部相對發達的少數民族地區,現代文明已經成為少數民族生產、生活的主要方式,其對流域生態環境的破壞已經達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因而西部少數民族地區流域生態環境的破壞正經歷著由小到大,由輕微到嚴重的歷史過程。
四、西部民族地區流域生態環境的法制理論基礎
首先,西部民族地區流域生態環境的法制保護應在法律上明確流域生態閥值的概念。如上對于西部流域生態環境的歷史觀的論述,人類活動與流域生態環境的破壞并不必然存在一致性等。人類活動對于流域生態環境的影響,取決于流域生態環境自身生態資源的承載力度,如若人類活動所造成的生態環境資源的破環程度超出了流域生態環境自我調節的程度,則流域生態環境就會遭受破壞,反之,如若人類活動所造成的生態環境資源的破環程度小于流域生態環境自我調節的程度,則流域生態環境保持良好。生態環境的承載度取決于生態系統中土地、氣候、動植物等因素,這些因素在一定作用和影響下達到相互平衡的狀態,這種平衡狀態稱為生態環境的閥值。在西部民族地區流域生態環境中,生態環境的承受度就是其閥值。現行對于西部民族地區流域生態環境的法律,在立法上著重對于危害環境行為的評價和懲罰,但對于生態環境基本的承受能力的規定,往往比較模糊,缺乏操作性。因此,對于西部民族地區流域生態環境的保護,應首先聚焦于西部民族地區流域生態環境的閥值,對其進行定性與定量分析,并以法律手段對其生態環境保護加以規定,明確西部民族地區流域生態在其各個層次的生態閥值,這是西部民族地區流域生態環境法律保護的基礎。
其次,西部民族地區流域生態環境的法制保護應明確公民的生態環境權。在憲法層面上,公民具有生存權與發展權。在西部民族地區,生存權與發展權在現實當中的實現形式就是對于生態資源的開發和利用,這在擇水而居的西部流域地區尤為明顯,少數民族居民因其生產、生活方式的落后,其對流域生態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是其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但法律對于流域生態環境閥值做出了限制,在這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西部民族地區少數民族對于流域生態資源的利用。由此,對于西部民族地區流域生態環境治理在法制的第二個層次,是在西部民族地區流域生態環境的閥值的基礎上建立公民生態權。公民生態權是以公民生存權和發展權為基礎,以西部民族地區流域生態環境的閥值對其進行必要的限制,規定西部民族地區公民的對于生態環境的權利和義務。公民生態權與公民生存權、發展權具有辯證關系,雖然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民生存權、發展權的發展,但這種限制是建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基礎之上的,二者具有相互促進的作用。公民生態權的建立對于西部民族地區公民而言,為其制定了具體的行為準則,在法制的層面上具有實踐的意義。
最后,調節公民生態環境權與生存權、發展權的關系。公民生態環境權在位階上較公民生存權、發展權低,但在具體法制的適用上并不是說公民生存權、發展權可以超越生態環境權的限制。如上所論述,公民生態環境權與生存權、發展權存在辯證關系,兩者既相互制約,又相互促進。但在法制運行當中,環境生態權與生存權、發展權常常體現為矛盾的一面:注重生存權和發展權,則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不計后果地向自然索取,造成自然環境的破壞;而注重生態環境權,則一味保護環境,使得西部民族地區流域居民自身生存和發展受到限制。由此,注重生態閥值和自然規律是處理生態環境權與生存權、發展權關系的關鍵,生態閥值環境承受能力的限度,也是公民生存權、發展權的邊界,公民生存權、發展權的實施應在流域生態閥值的范圍之內。西部民族地區正處于農耕文明、畜牧文明、工業文明三者交匯之中,從低層次的文明向高層次文明的發展是歷史發展的方向,在流域生態閥值的范圍之內,以法制的手段調節公民生態環境權與生存權、發展權的關系是對于西部民族地區流域生態環境進行治理的基礎和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