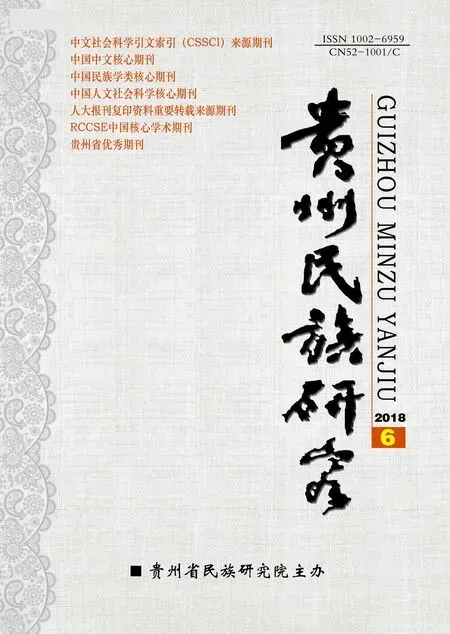西域佛教美術(shù)文化歷史與貢獻(xiàn)
董馥伊
(新疆師范大學(xué) 美術(shù)學(xué)院,新疆·烏魯木齊 830054)
西域處于中國(guó)最西部與中亞腹地,因?yàn)楠?dú)特的地理位置,自古迄今,西方祆教、景教、摩尼教、佛教、伊斯蘭教等宗教相繼入駐此地。其中要數(shù)印度輸入的佛教最為盛行,并以其獨(dú)特的美術(shù)造型形式,彰顯其文化內(nèi)涵,深受西域各族人民的愛(ài)戴與支持。
據(jù)佛教文化學(xué)者陳世良為“絲路佛光叢書(shū)”所寫(xiě)“總序”提及:新疆在地理位置上位于“絲綢之路”的中段,其中有大量的受到中外學(xué)人、游子、釋門(mén)弟子極大關(guān)注的佛教文物。《中國(guó)美術(shù)全集》 《中國(guó)石窟》等大型類(lèi)書(shū)的“新疆卷”中均公布了珍貴的佛教文物圖片,與此同時(shí),國(guó)外一些國(guó)家如德、法、英、日等學(xué)者們均先后刊布出各國(guó)從新疆掠走的與佛教相關(guān)的部分文物照片。這些文物佐證,更是引起了學(xué)界對(duì)新疆的更多關(guān)注。
陳世良先生認(rèn)為:作為中國(guó)佛教中重要組成部分的西域佛教,其目前的研究現(xiàn)狀令人堪憂。整體研究包括其脈絡(luò)的整理以及基礎(chǔ)材料的搜集;佛教文化和佛教藝術(shù)的體系化研究等方面相對(duì)滯后,與西域佛教應(yīng)具有的歷史地位相差甚遠(yuǎn)。[1]
我們追尋古西域佛教美術(shù)中的珍貴遺產(chǎn)與文化基因,可通過(guò)國(guó)內(nèi)外多年來(lái)的諸多研究成果,尤其是對(duì)西域佛教藝術(shù)(美術(shù))與絲綢之路文化的研究,梳理西域美術(shù)的研究重點(diǎn)與解決的問(wèn)題,確認(rèn)西域美術(shù)研究在中外經(jīng)濟(jì)、文化交流中的歷史價(jià)值與現(xiàn)實(shí)作用。
一、豐厚的西域佛教美術(shù)文化遺產(chǎn)
據(jù)《新疆百科知識(shí)辭典》記載:“西域,意即中國(guó)西部的疆域。最早見(jiàn)于《漢書(shū)·西域傳》。此后,以迄于清,歷代著作,多以西域呼之。其界定范圍有廣、狹義之分[2]。按照狹義與廣義西域的史地文化概念,古代新疆為“我國(guó)歷代中央及地方政權(quán)所管轄的地方。”一般為“西域三十六國(guó)”,此論始見(jiàn)《后漢書(shū)·西域傳》。三十六國(guó)分別為:烏孫、龜茲、焉耆、若羌、樓蘭、且末、小宛、精絕、戎盧、捍彌、渠勒、于闐、皮山、西夜、子合、蒲犁、依耐、莎車(chē)、疏勒、尉頭、溫宿、尉犁、危須、墨山、狐胡、車(chē)師、劫?lài)?guó)、依耐、無(wú)雷、難兜、大宛、捐毒、休循、桃槐、蒲類(lèi)、西且彌。歷史上西域諸國(guó)均在匈奴以西,烏孫之南,多在天山南北,蔥嶺一帶。分布于中西文化交流的絲綢之路沿線。
此文所涉獵的西域?yàn)楠M義所指,是古代新疆舊稱(chēng),在兩漢至宋元時(shí)期這里的佛教文化占有絕對(duì)優(yōu)勢(shì)。解放以后,黨和人民政府尊重新疆各族人民的意愿,可以自主選擇宗教信仰,佛教文化仍具有一定的份額。
令人深思的是,20世紀(jì)末21世紀(jì)初,在印度輸入的佛教基本消失的新疆,卻一次次掀起了發(fā)掘、整理、研究古代佛教文化,特別是探索與研究佛教美術(shù)的學(xué)術(shù)熱潮,這為我們研究古代新疆的佛教文化帶來(lái)機(jī)遇。
西域佛教美術(shù)包括古代新疆地理歷史時(shí)空中所產(chǎn)生的佛教繪畫(huà)、雕塑、建筑、器物與相關(guān)的佛教文化遺產(chǎn)。在遺存的無(wú)論是數(shù)量與質(zhì)量都很大與高乘的西域佛教文化寶庫(kù)面前,佛教美術(shù)僅是佛教藝術(shù)的一個(gè)組成部分,它包括佛教雕塑藝術(shù)、繪畫(huà)藝術(shù)、石窟藝術(shù)和建筑藝術(shù)等門(mén)類(lèi)。[3]
相比于林林總總的宗教與世俗文化著述之中,在研究西域佛教美術(shù)的學(xué)術(shù)成果中,如中國(guó)美術(shù)全集新疆分冊(cè)、及其此地佛教繪畫(huà)、雕塑、建筑畫(huà)冊(cè)與學(xué)術(shù)論集中,要數(shù)對(duì)西域美術(shù)文化遺產(chǎn)的介紹與研究成果的比例較大而廣。就拿在當(dāng)今絲綢之路與西域文化產(chǎn)生廣泛影響,享有盛譽(yù)的《絲綢之路造型藝術(shù)》[4]一書(shū)所顯示的重要學(xué)術(shù)數(shù)據(jù),就能掂量出西域佛教文化的重量。
按照其佛教文化總論與分論來(lái)審視:總論文章共四篇:閻文儒《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賈應(yīng)逸、趙霄鵬《藝苑妙境—燦爛的新疆石窟寺藝術(shù)》,黃國(guó)強(qiáng)《西域壁畫(huà)的視覺(jué)形式剖析》,吳焯《從考古遺存看佛教傳入西域的時(shí)間》。分論包括西域佛教美術(shù)所在地高昌、龜茲、和田、中亞文章共十八篇。
其中高昌佛教美術(shù)文章四篇:李鐵《高昌樂(lè)舞圖卷》,譚樹(shù)桐《阿斯塔那唐墓俑塑藝術(shù)》,邵養(yǎng)德《高昌掠影—兼談〈女?huà)z和伏羲圖〉》、賈應(yīng)逸《吐峪溝石窟探微》。
龜茲佛教美術(shù)文章十一篇:張光福《庫(kù)車(chē)的壁畫(huà)藝術(shù)》,霍旭初、王小云《龜茲壁畫(huà)中的樂(lè)舞形象》,姚士宏《克孜爾的佛傳四相圖》 《克孜爾175窟的生死輪圖》 《龜茲佛教與石窟》 《敘利亞畫(huà)家在克孜爾》。王伯敏《克孜爾石窟的壁畫(huà)山水》、賈應(yīng)逸《克孜爾17窟壁畫(huà)藝術(shù)特色》,霍旭初《龜茲舍利盒樂(lè)舞圖》,徐建融《龜茲壁畫(huà)的人體畫(huà)法》,袁廷鶴《龜茲風(fēng)壁畫(huà)初探》。
和田佛教美術(shù)文章兩篇:張光福《尉遲跋質(zhì)那和尉遲乙僧》 《尉遲乙僧的繪畫(huà)及其成就》。中亞佛教美術(shù)文章一篇:吳焯《來(lái)自中亞的北齊畫(huà)家曹仲達(dá)》。從中顯示的西域佛教文化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其中相關(guān)論文以天山以南佛教石窟藝術(shù)研究為主,并以龜茲佛教石窟藝術(shù)研究為主,其他地區(qū)佛教石窟及其美術(shù)家與作品研究為輔。
據(jù)黎薔先生《新疆美術(shù)概說(shuō)》一文將古代西域與新疆美術(shù)分為四大部分:(1)史前原始宗教美術(shù),(2)佛教時(shí)期美術(shù),(3)伊斯蘭教時(shí)期美術(shù),(4)新中國(guó)建立前后美術(shù)。相比其他宗教與世俗造型藝術(shù)而言,西域佛教時(shí)期美術(shù)較為繁榮與發(fā)達(dá),遺存的佛教石窟繪畫(huà)與作品比較多,西域佛教文化曠日持久地影響著中國(guó)內(nèi)地的石窟藝術(shù)發(fā)展。[5]
賈應(yīng)逸、祁小山著《佛教?hào)|傳中國(guó)》一書(shū)亦考述:佛教于公元前后傳入中國(guó)。傳播路線,主要以溝通東西方陸路交通的大動(dòng)脈——‘絲綢之路’為主。地處祖國(guó)西部、位居?xùn)|西方陸路交通——絲綢之路要沖的新疆較早接受了佛教,尤以距印度、罽賓最近的于闐為最早。此書(shū)“概述”闡釋了古代新疆是印度佛教經(jīng)西域輸入中原地區(qū)的天然孔道,并論證了西域佛教?hào)|傳在豐富中國(guó)傳統(tǒng)美術(shù)文化過(guò)程中所發(fā)揮的重要作用:印度、希臘、波斯和中亞文化中的精粹藝術(shù)如繪畫(huà)、音樂(lè)、工藝以及藝術(shù)理念等方方面面、五方雜俎,都借助著佛教?hào)|傳而來(lái)到中國(guó)。
同時(shí)此書(shū)還指出在古代新疆佛教美術(shù)文化區(qū)域,所醞釀、形成的“西域佛教畫(huà)派”的獨(dú)特藝術(shù)風(fēng)格:“古代的于闐人將流傳于自己人民中間的傳說(shuō)與佛教聯(lián)系起來(lái),往往還把這些傳說(shuō)表現(xiàn)在佛教藝術(shù)中。如鼠王、傳絲、毗沙門(mén)天等。于闐的造像風(fēng)格,早期與犍陀羅的石雕相近,也曾吸收了馬圖拉藝術(shù)的成分。但其突起的面型、繪畫(huà)中的鐵線卻獨(dú)具風(fēng)采”。后者大大影響了我國(guó)中原地區(qū)的佛教藝術(shù),以尉遲父子為代表“于闐畫(huà)派”的“用筆勁緊如屈鐵盤(pán)絲”“用色沉著,堆起素絹而不隱指”和“匠意特險(xiǎn)……身若出壁”特點(diǎn)在我國(guó)繪畫(huà)史上享有盛譽(yù)。“于闐畫(huà)派”的美術(shù)特點(diǎn),在現(xiàn)存的龜茲壁畫(huà)中表現(xiàn)最為明顯。[6]
二、西域佛教美術(shù)史學(xué)研究
在我國(guó),關(guān)于西域佛教美術(shù)史的研究與探索興起于20世紀(jì)初,成熟于20世紀(jì)末與21世紀(jì)初。最早的綜合性論著如向達(dá)《唐代長(zhǎng)安與西域文明》,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黃文弼《新疆考古之發(fā)現(xiàn)與古代西域文化之關(guān)系》,王子云《從長(zhǎng)安到雅典》,常書(shū)鴻《新疆石窟藝術(shù)》,閻文儒《中國(guó)石窟藝術(shù)總論》,金維諾《龜茲藝術(shù)風(fēng)格與成就》,蘇北海《絲綢之路與龜茲歷史文化》 《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沈福偉《中西文化交流史》等。
后來(lái)產(chǎn)生的則是較具體的相關(guān)論文與著作,如宿白《克孜爾洞窟階段劃分與年代問(wèn)題的初步探索》,譚樹(shù)桐《龜茲菱格畫(huà)與漢博山爐》,霍旭初《西域佛教文化論稿》,賈應(yīng)逸《高昌石窟壁畫(huà)精粹》,林梅村《漢唐西域與中國(guó)文明》,柳洪亮《高昌石窟概述》,朱英榮《論新疆克孜爾千佛洞形成的歷史條件》,沈康身《絲綢之路與源遠(yuǎn)流長(zhǎng)的石窟藝術(shù)》,吳焯《克孜爾石窟壁畫(huà)畫(huà)法綜考》、《佛教?hào)|傳與中國(guó)佛教藝術(shù)》,趙豐《美術(shù)考古概論:絲綢之路》,張俊《龜茲石窟壁畫(huà)之宗教文化研究》等。
西域佛教美術(shù)有著特殊的史地文化與藝術(shù)特色,故此,需要從文化宏觀與藝術(shù)微觀方面進(jìn)行綜合考察。其理論則倡導(dǎo)從西域歷史文化與美術(shù)藝術(shù)角度予以全面、系統(tǒng)、科學(xué)的構(gòu)建。
閻文儒先生在解放初期對(duì)新疆佛教石窟進(jìn)行實(shí)地調(diào)查與研究,撰寫(xiě)了一系列學(xué)術(shù)考察與統(tǒng)計(jì)的長(zhǎng)篇論文,如在《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中所統(tǒng)計(jì)有:(1)拜城克孜爾石窟,(2)森不塞姆石窟、(3)瑪扎伯哈石窟、(4)克子喀罕石窟(克孜爾尕哈)、(5)庫(kù)木土拉石窟(庫(kù)木吐拉)、6、焉耆七格星明屋與石窟、(7)柏孜克里克石窟、8、勝金口的寺院遺址、(9)吐峪溝石窟、(10)雅爾湖石窟、(11)石窟造像等。還撰寫(xiě)《龜茲境內(nèi)漢人開(kāi)鑿漢僧住持最多的一處石窟——庫(kù)木土拉》。1999年新發(fā)現(xiàn)的位于庫(kù)車(chē)縣城北面,天山支脈克孜利亞山的庫(kù)木魯克艾肯溝谷內(nèi)的“阿艾石窟”。開(kāi)鑿時(shí)間為公元八世紀(jì)安西大都護(hù)府設(shè)龜茲之時(shí)。如洞窟中的“觀無(wú)量壽經(jīng)變”“說(shuō)法圖和觀音”“盧舍那佛像”“藥師佛像”等很有學(xué)術(shù)價(jià)值。
據(jù)閻文儒在《中國(guó)石窟藝術(shù)總論》[7]中論述:“天山以南各石窟群中的塑像,由于宋、元以來(lái),新疆佛教一蹶不振,因而佛教造像俱遭破壞。清末,外國(guó)考古學(xué)家進(jìn)入新疆各地,將還殘存的一些造像又全部劫走。近年來(lái),新疆文物工作者在庫(kù)木土拉石窟新發(fā)現(xiàn)了兩個(gè)洞窟,其中新2號(hào)窟尚有一尊佛像,是新疆石窟中保存至今的唯一塑像……還有庫(kù)爾勒那克沙特拉石窟出土的半身菩薩像……以上造像,最早的當(dāng)四、五世紀(jì),最晚之作品約當(dāng)八、九世紀(jì)的精美的造像作品……至于各期壁畫(huà)的畫(huà)風(fēng),不只可以說(shuō)明龜茲諸地的繪畫(huà)藝術(shù)發(fā)展過(guò)程,而且也可以補(bǔ)證中原地區(qū)佛教藝術(shù)的發(fā)展規(guī)律”。
上述歷史文獻(xiàn)與資料基本囊括了新疆境內(nèi)古代佛教美術(shù)主要文化遺產(chǎn)與學(xué)術(shù)理論基本觀點(diǎn)。當(dāng)然較為完備的是后來(lái)集全國(guó)美術(shù)學(xué)術(shù)理論工作者之力編纂的《中國(guó)美術(shù)全集》 《中國(guó)美術(shù)分類(lèi)全集》等大型類(lèi)書(shū)的“新疆卷”。
仲高在《西域藝術(shù)通論》一書(shū)專(zhuān)設(shè)“西域佛教藝術(shù)”,提及西域佛教美術(shù)的內(nèi)容、形式與重要?dú)v史地位。他指出,因自然與人為原因,于中世紀(jì)“天山以南諸綠洲城郭佛教先后走向衰亡,千年西域佛教藝術(shù)的蹤跡也只能在那些毀壞殆盡的佛教石窟、寺院和雕塑、壁畫(huà)遺址、遺跡中尋覓了。這些遺址、遺跡主要是:于闐熱瓦克,丹丹烏里克,約特干佛寺遺址,鄯善米蘭佛寺遺址,龜茲克孜爾石窟,疏勒莫爾佛教遺址,焉耆佛寺遺址,高昌吐峪溝石窟等”。西域佛教美術(shù)以強(qiáng)大的生命力“不僅存在漢化的諸如于闐、鄯善、龜茲、高昌等區(qū)域性佛教藝術(shù),還存在漢傳佛教藝術(shù)、藏傳佛教藝術(shù)等形態(tài)。……漢傳佛教藝術(shù)也是與中國(guó)傳統(tǒng)的繪畫(huà)、雕塑、音樂(lè)、舞蹈相融合的產(chǎn)物。漢傳佛教藝術(shù)以其巨大的能量足以在西域的佛教藝術(shù)中占有重要地位。”[8]
論及西域鮮為人知的佛教美術(shù)家與代表性繪畫(huà)作品,我們可以參閱張彥遠(yuǎn)《歷代名畫(huà)記》,以及張光福《尉遲跋質(zhì)那和尉遲乙僧》 《尉遲乙僧的繪畫(huà)及其成就》與吳焯《來(lái)自中亞的北齊畫(huà)家曹仲達(dá)》等學(xué)術(shù)論文。
其中張彥遠(yuǎn)《歷代名畫(huà)記》卷九記載:“尉遲乙僧,于闐國(guó)人,父跋質(zhì)那。乙僧國(guó)初授宿衛(wèi)官,襲封郡公,善畫(huà)外國(guó)及佛像,時(shí)人以跋質(zhì)為大尉遲,乙僧為小尉遲。畫(huà)外國(guó)及菩薩,小則用筆緊勁如屈鐵盤(pán)絲,大則灑落有氣概”。另外,《歷代名畫(huà)記》中記載曹仲達(dá):“本曹?chē)?guó)人也。北齊最稱(chēng)工,能畫(huà)梵像,官至朝散大夫。國(guó)朝宣律師撰《三寶感通記》,具載仲達(dá)畫(huà)佛之妙,頗有靈感。僧倧云:‘曹師于袁,冰寒于水,外國(guó)佛像,亡竟于時(shí)’。
吳焯先生指出,曹仲達(dá)的“曹衣出水”式畫(huà)法,是“中國(guó)佛像畫(huà)藝術(shù)發(fā)展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必然結(jié)果”。還說(shuō),“東漢末年,印度佛經(jīng)由中亞傳入我國(guó)新疆,繼而進(jìn)入內(nèi)地,至南北朝時(shí)代,佛教寺院已盛行,圖繪寺壁的佛畫(huà)得到空前的發(fā)展,許多來(lái)自印度和中亞的畫(huà)家參加了繪制佛像的活動(dòng),北齊曹仲達(dá)即其突出的代表”。
魏長(zhǎng)洪在《西域佛教》一書(shū)“繪畫(huà)藝術(shù)”之“尉遲乙僧的佛畫(huà)”中寫(xiě)道:“尉遲乙僧的畫(huà)法對(duì)唐代及唐以后的繪畫(huà)有重大影響,并且其影響遠(yuǎn)及朝鮮、日本,為中國(guó)美術(shù)的發(fā)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xiàn)。”[9]
陳兆復(fù)主編《中國(guó)少數(shù)民族美術(shù)史》談到“西域民族畫(huà)派”勃興原因與歷史文化影響時(shí)指出:“西域民族畫(huà)派與唐代美術(shù)交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唐太宗對(duì)各民族一視同仁的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唐在貞觀十四年(640年)到長(zhǎng)安二年(720年)間把天山南北歸于唐朝版圖中,設(shè)四鎮(zhèn),號(hào)稱(chēng)安西四鎮(zhèn)。但在這里設(shè)立了兩種行政機(jī)構(gòu)系統(tǒng),其一即與內(nèi)地相同的州縣制。另一是專(zhuān)設(shè)于邊區(qū)的護(hù)府領(lǐng)都督府,對(duì)兄弟民族內(nèi)部社會(huì)制度給予保留,而使其同新的行政組織結(jié)合在一起,因此對(duì)西域各族經(jīng)濟(jì)文化發(fā)展起到了促進(jìn)作用。三是西域各族民族文化得到進(jìn)一步發(fā)展。以上因素促使西域畫(huà)派藝術(shù)得到繁榮發(fā)展。”[10]
三、西域佛教美術(shù)文化關(guān)系探索
著名學(xué)者季羨林先生在《佛教與中印文化交流》一書(shū)中論斷:“新疆是全世界上惟一的一個(gè)世界四大文化連接的地方。它東有中國(guó)漢族文化,南有印度文化,西有閃族伊斯蘭文化和歐洲文化。連古代希臘的雕塑藝術(shù),都通過(guò)形成于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一帶的犍陀羅藝術(shù)傳入新疆,再傳入中國(guó)內(nèi)地。……新疆這個(gè)地方實(shí)在是研究世界文化交流的最好的場(chǎng)地。”這里匯聚了不同的西域宗教文化,對(duì)此我們應(yīng)該綜合性比較研究,并且還應(yīng)追溯西域佛美術(shù)文化與國(guó)內(nèi)外相互影響的藝術(shù)關(guān)系。[11]
王子云在《新疆拜城赫色爾石窟》一文中曾發(fā)現(xiàn),天山南麓“赫色爾石窟”(即龜茲克孜爾石窟):“壁畫(huà)的一般造型和技法,屬于犍陀羅的藝術(shù)樣式,即希臘—波斯—印度式。這種樣式的特點(diǎn),主要是表現(xiàn)在衣褶的緊窄和人體肌肉的暈染。以及部分裸體的形象。但在赫色爾,它又結(jié)合了地方成分,并吸取了中原民族的樣式,即有多民族傳統(tǒng)的具有新鮮氣質(zhì)的藝術(shù)。它與中原文化、新疆地方文化,中印度笈多文化,北印度犍陀羅文化,波斯薩珊朝文化,以及希臘羅馬的文化成分,都有著直接的關(guān)系。……它蘊(yùn)含著嶄新的形式,這樣就更值得我們?cè)谘芯窟z產(chǎn)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問(wèn)題上對(duì)它特別加以珍視”。
王鏞先生主編《中外美術(shù)交流史》在“東漸中國(guó)西域”一章中考察發(fā)現(xiàn),在塔里木盆地疏勒地區(qū)圖木休克的木雕《佛陀坐像》,“具有笈多薩爾納特樣式佛教的特征。這尊佛像以禪定姿勢(shì)端坐,袈裟下擺一任犍陀羅舊制呈半圓形在雙膝之間垂落……佛像拇指與食指之間的縵網(wǎng)(三十二相之一),亦屬于笈多式佛像的造型特征。”從而得知“印度、犍陀羅佛教美術(shù)相繼輸入于闐、疏勒、龜茲、高昌等地”。另外此書(shū)還以龜茲、高昌地區(qū)的佛教美術(shù)代表作為例指出:“龜茲地區(qū)的佛教遺跡以石窟為主,包括克孜爾石窟、庫(kù)木吐拉石窟等十余處,其中克孜爾石窟規(guī)模最大,早期克孜爾壁畫(huà)深受犍陀羅藝術(shù)和印度傳統(tǒng)繪畫(huà)的影響。高昌地區(qū)的吐峪溝石窟、伯孜克里克石窟和吉木薩爾高昌回鶻佛寺遺址等地的泥塑、木雕、幡畫(huà)和壁畫(huà),亦受到經(jīng)龜茲、焉耆傳來(lái)的犍陀羅藝術(shù)與笈多藝術(shù)的影響,而中國(guó)內(nèi)地藝術(shù)的影響更為強(qiáng)烈。西域南北兩道最終總湊敦煌、犍陀羅藝術(shù)與笈多藝術(shù)的影響與中國(guó)內(nèi)地藝術(shù)交相匯合”。
說(shuō)到西域佛教美術(shù)文化與唐代藝術(shù)發(fā)生的關(guān)系,及其“西域畫(huà)”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具有“重要的地位”時(shí),陳兆復(fù)主編《中國(guó)少數(shù)民族美術(shù)史》指出:“在唐代,出現(xiàn)來(lái)不少有成就的繪畫(huà)藝術(shù)家。其中尉遲乙僧為代表的西域畫(huà)派尤為突出。西域畫(huà)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結(jié)晶,民族藝術(shù)的奇葩,不僅在中國(guó)美術(shù)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對(duì)今后如何吸收外來(lái)藝術(shù)融化于民族藝術(shù)之中,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借鑒”。
當(dāng)然上述“西域畫(huà)”在中國(guó)美術(shù)史上是一個(gè)大概念,不僅在古代新疆,亦在中原、江南地區(qū)流傳而形成重要流派。西域佛教美術(shù)包括西域人士繪制,人士創(chuàng)作的反映西域古族生活場(chǎng)景的繪畫(huà)作品,如由梁蕭繹所作的描繪西域與外國(guó)貢使的《職貢圖》畫(huà)卷,據(jù)吳升《大觀錄》記載,其原畫(huà):“繪入朝番客凡二十六國(guó),今僅存十二國(guó),如西域龜茲、波斯、胡密丹,以及滑國(guó)、狼牙修、鄧至、周古柯、百濟(jì)、倭國(guó)、呵跋檀、白題、末國(guó)等胡夷古族國(guó)度”。
再有需指出的是西域佛教不僅包括由印度輸入的大乘教、小乘教與密教等,亦包括在中國(guó)生成的漢傳佛教與藏傳佛教,后者俗稱(chēng)“喇嘛教”的藏傳佛教亦為中國(guó)民族佛教的一個(gè)重要分支,與新疆佛教發(fā)生密切關(guān)聯(lián)。關(guān)于藏傳佛教及其美術(shù)文化輸入西域歷史,據(jù)魏長(zhǎng)洪等著《西域佛教史》一書(shū)指出:藏傳佛教傳入西域的時(shí)間,至今仍未發(fā)現(xiàn)文獻(xiàn)的具體記載。今在新疆和田地區(qū)發(fā)現(xiàn)的“歡喜佛”塑像,屬于藏傳佛教的塑像。“歡喜佛”是藏傳佛教密宗的本尊神,即佛教中的“欲天”“愛(ài)神”。經(jīng)專(zhuān)家考定,“歡喜佛”塑像約為10世紀(jì)末或21世紀(jì)初的文物,表明藏傳佛教此時(shí)已傳入和田地區(qū)。近代在新疆吐魯番地區(qū)發(fā)現(xiàn)的11—13世紀(jì)期間的藏文佛經(jīng),進(jìn)一步佐證藏傳佛教在新疆傳播地區(qū)的擴(kuò)大。
意大利著名學(xué)者馬里奧·布薩格里在《中亞繪畫(huà)》一書(shū)對(duì)西域佛教美術(shù)甚為贊賞,他特別指出:“在所有的中亞藝術(shù)中,庫(kù)車(chē)?yán)L畫(huà)實(shí)實(shí)在在可劃入其高水平之列”。根據(jù)國(guó)內(nèi)外所刊布的大量研究成果,在中亞、西亞與西域宗教藝術(shù)之中,不僅龜茲佛教繪畫(huà),天山南北歷代的佛教美術(shù)文化亦“可劃入其高水平之列”。
- 貴州民族研究的其它文章
- 各民族在校大學(xué)生的就業(yè)預(yù)期比較研究
——以東西部四所高校調(diào)研為例 - 南方少數(shù)民族民間音樂(lè)的音聲結(jié)構(gòu)與黏性發(fā)展形態(tài)
——以三種典型案例為中心 - 歐洲語(yǔ)言教師教育及其對(duì)中國(guó)少數(shù)民族雙語(yǔ)師資培養(yǎng)的啟示
- 高校英語(yǔ)專(zhuān)業(yè)英漢翻譯教學(xué)的民族文化融入及應(yīng)用研究
- 應(yīng)用型人才培養(yǎng)目標(biāo)下的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商務(wù)英語(yǔ)教學(xué)研究
- 國(guó)家體育治理現(xiàn)代化背景下民族地區(qū)高校體育智庫(kù)建設(sh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