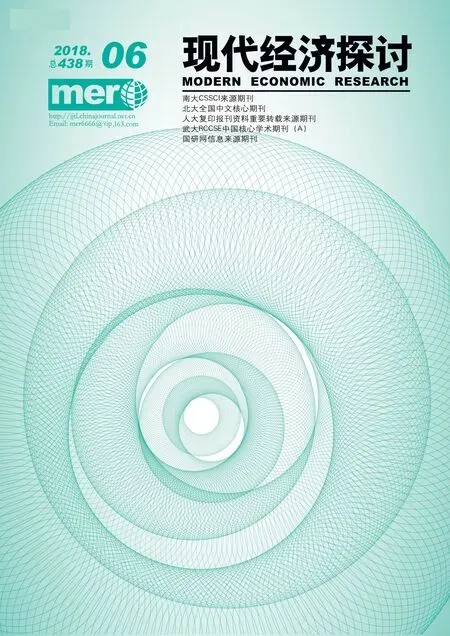供給側結構改革的發生機制研究※
——基于不同經濟學視角
程東祥 朱 虹 王啟萬 陳 靜
一、 引 言
以往的供給學派主張減稅、放松管制等經濟政策,使需求適應供給,而我國的供給側改革則有所不同,推行與“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相關的政策,以降低成本、提高有效供給為導向(劉志彪,2016)。中國經濟運行中,由于體制弊端而出現結構失衡,產能過剩、房地產庫存加大、企業生產成本上升、有效供給不足,所以在制度層面上需要重新設計,解決新常態經濟下的深層次矛盾。
供給側改革就是通過一系列產品、服務、勞動、貿易和金融等激勵政策,減少和清除資源配置障礙,提高市場和制度運行效率,從而提升生產率(SPR’s Macro-structural team, 2015)。我國的供給側改革是在供給側與需求側有效協同的基礎上,加強經濟供給側的結構性調整與改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促進資源要素有效供給、質量提升和高效配置,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這種雙側協調的管理方式是經濟新常態下實現我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必經之路(覃菲菲,2017)。目前國內學術界對供給側改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改革的成因方面,如“三駕馬車”的拉動作用逐漸減弱而科技創新和制度供給不夠(賈康等, 2016),供給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匹配(劉偉等, 2016),創新創業動力不足(文建東等, 2016),要素配置扭曲(劉志彪, 2016),需求管理政策的弊端不斷顯現(江小國等,2016)等;二是改革的思路和路徑方面,較多學者提出了建議,如科技創新、發展實體經濟(沈坤榮, 2016),調整產業結構、重視產品質量、生產的標準化和支持中小企業發展(楊麗君等,2014),通過市場機制的作用提髙要素配置效率(楊麗君等,2014;袁志剛等,2016),以及增加政府支出、減少政府稅收、增加貨幣供給等(李翀, 2016),以實現產業、要素和制度三個層面的轉型(馮志峰, 2016)等;三是具體產業政策方面,如能源(楊競等, 2016)、農業(覃菲菲,2017)、教育(賀芬等, 2016)、文化(鄭海婷等,2017)、旅游(廖淑鳳等, 2016)等產業政策。雖然學術界對供給側改革的動向及內涵已經基本達成了共識,但對于改革的系統性研究仍然有待深入,宏觀政策、產業政策和區域政策之間的內在邏輯和深刻內涵尚未厘清,供給側改革的作用還未體現出來,而這些問題沒有弄清楚,各地方政府在推進區域經濟和產業發展過程中就不知道具體要“怎么做”,無法制定具體的改革目標和主要內容,所以本研究試圖探尋供給側改革的發生機制及其后效作用,挖掘供給側改革的理論內涵及功能效用,為地方政府制定供給側改革政策提供理論依據。
供給側改革的目的在于解決導致“四降一升”的結構性矛盾。“四降”指的是經濟增速下降、工業品價格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和財政收入增幅下降,“一升”則是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四降一升”既反映了未來一段時間我國因需求不足而導致的經濟通縮性下行的趨勢,又是我國要通過一攬子政策和措施致力于解決的問題所在。2015年12月,為了解決“四降一升”的結構性矛盾,中央提出了供給側改革的五項重點任務,即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簡稱“三去一降一補”:首先要降低與需求不相匹配的過剩產能,并讓房地產庫存大幅度減少,化解金融杠桿風險,然后要逐步降低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使其財務成本下降,最后是補足民生、新興產業及社會事業短板。這五項重點任務不是獨立分割的,而是存在一定邏輯關系,相互影響和支撐。圍繞這五大重點任務,供給側改革在不同部門、不同層面都需要采取相應措施。五項關鍵任務的起源及產生過程,與我國特有的經濟發展特點有關,有其獨特的發生機制。
二、 改善總供給結構、減稅、放松管制: 基于供給經濟學的發生機制分析
供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阿瑟·拉弗、羅伯特·蒙代爾、裘德·萬尼斯基、馬丁·費爾德斯坦和保羅·克雷格·羅伯茨等,其主張減少稅收、刺激經濟、創造就業,成為里根時期美國經濟政策的理論支持,使美國經濟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獲得了持續繁榮。里根經濟學主要措施是降低政府支出和社會福利預算,將美元的發行控制在一定范圍內降低膨脹率,減少稅負和政府管制促進企業投資和發展。供給經濟學主要兩大理論基礎,一是法國經濟學家薩伊提出的“薩伊定律”,二是美國經濟學家拉弗提出的“拉弗曲線”。前者給出了“供給創造需求”、“產品會找到購買者”的重要思想,后者發現了稅收與稅率之間的邏輯曲線。古典供給學派和新供給學派在不同時期對西方國家經濟政策制定作出了貢獻。基于供給經濟學對中國經濟現狀的分析,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 總供給結構改善
供給側改革以“結構性”為改革的落腳點,即生產要素供給結構和產品供給結構的改革是此次改革著力點和主要目標。結構性強調各個組成部分的有機協調,實現個體對于整體貢獻度的最大化。在生產要素市場中,結構性改革是要實現各個生產要素充分流動和有機結合,提髙要素配置的效率;在產品市場中,結構性改革是要實現產品的供需平衡,包括實現產品數量結構的平衡、產品質量結構的平衡、產品品種結構的平衡等。結構性改革立足于長遠的經濟發展目標,不斷為經濟的發展提供結構動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一直保持了較高增速,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是中國長期依賴于投資、消費和凈出口這“三駕馬車”拉動需求,在管理上較為粗放,奉行外延式發展模式,這就導致了產能過剩,特別是傳統產業如冶金、煤炭、水泥、化工、造船等,同時,新興產業和服務業仍然處于供給不足的狀態,所以我國的產能過剩應該是“結構性產能過剩”。根據供給學派的觀點,經濟的增長取決于資源和資本的有效利用,很顯然我國的資本和勞動力等要素資源沒有有效配置,從而導致了結構失衡。當前,我國的結構性問題主要包括產業結構、區域結構、要素投入結構、排放結構、經濟增長動力結構和收入分配結構等六個方面的問題,需要改善總供給結構來實現經濟增長。從生產端入手,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側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針對尤為嚴重的產業結構問題,其著力點是定向調控;通過打破產業結構的低端鎖定,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鼓勵環保和服務業,推進傳統制造業轉型升級,實現新興產業和傳統產業協同發展。
2. 減稅
拉弗曲線反映了稅收和稅率的關系,政府稅收并不是隨著稅率的增長而一直增長的,存在一個拐點,到了這個極限值,政府應該減稅,減輕企業負擔。這一重要理論被里根政府采納,企業稅率從50%降到28%,個人稅率從46%降到34%,美國總稅收未減反升,奠定了20世紀80年代美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礎。對于我國企業來說,面臨的問題在于原材料成本上升、融資難,以及政府官員尋租等問題導致的企業成本上升。根據新供給經濟學理論,商品和勞務的供給與投資和消費的積極性正相關,改變稅收能提升企業和個人投資和消費積極性。稅收政策作為政府重要的政策工具,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主要發揮三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是作為“降成本”政策的重要措施,通過較大規模的減稅降費減輕企業負擔,在煥發企業經營活力的同時提高資本回報率,從而起到穩定就業和促進投資的作用。二是通過稅制改革促進稅制完善,矯正要素配置的扭曲,既要努力實現稅制的“中性”,促進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同時還要在資源和環境等“市場失靈”的領域發揮好稅收的調節功能。三是在創新創業領域,稅收要通過系統而有針對性的優惠政策在促進研發投入、提升產業結構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所以,我國需要通過降低稅收來增強企業活力,目前正在實施的是“營改增”稅收改革,還有能源價格改革等,每年可以降低企業稅負9000億元人民幣。但是,相比里根政府的減稅幅度,我國對企業成本的降低支持還不夠。因此,在“營改增”全面推開、地方稅減少、產業結構調整大背景下,需要利用結構性減稅等政策,推動“雙創”和“中國制造2025”“互聯網+”行動計劃,促進服務業、先進制造業發展,扶持小微企業成長,發揮制度創新和技術進步對供給升級的倍增效用,擴大有效供給,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實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
3. 放松管制
薩伊認為,人的欲望是無窮的,只有有支付能力的欲望才能成為需求,所以要通過減少稅收、減少管制來發揮市場機制效用。新供給經濟學與凱恩斯主義不一樣,主張供給側與需求側協同發展,并非不需要需求側管理,而是要讓供給側進行技術創新、結構變化和制度變革,適應需求側結構,使市場機制發揮更有效的作用。中國的結構性糾偏,也是要通過市場的價格機制,倒逼政府進行行業改革。例如煤炭行業,通過國際市場的價格沖擊,倒逼煤炭行業的88種稅費改革,減輕企業負擔,增強企業活力。上海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也發揮了市場機制的作用,倒逼“一行三會”(中央銀行、證監會、銀監會和保監會)的金融改革。由此可通過實施精準協同放權,深入推進商事制度改革,合理擴大高校和科研機構自主權,大力推進政務公開,推進監管體制改革等措施從不同角度加強對簡政放權、放松管制和優化服務的深化。
當然,我國的供給結構改善、減稅和放松管制不同于西方的供給側改革政策,必須適應我國當前國情。首先,在供給結構改革方面,我國要去產能,解決那些效益不佳、扭虧無望、創效能力低的“僵尸企業”,并通過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其次,在減稅方面,我國的政策措施是多方面的,除了中央政策還有地方政策,涉及到銀行、稅務、養老保險、企業用工、政府尋租、國企壟斷等,最終目的在于降低企業交易成本,釋放企業活力;最后,在政府管制方面,我國與美國里根經濟學時期放松石油價格、打破壟斷的政策不同,我國是通過技術創新、簡政放權等措施來調控供給結構,增強經濟市場化水平,實現經濟的空間結構調整。
三、 供需互補、創新驅動:基于政治經濟學的發生機制分析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是研究客觀經濟規律的科學,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矛盾和弊病,以求利用經濟規律能動地改造世界,為人民大眾謀利益。盡管時代背景不一樣,政治體制不一樣,我國經濟發展具有復雜性和特殊性,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對于研究我國的經濟增長仍然有一定參考價值。基于政治經濟學對中國經濟現狀的分析,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 供需互補性發展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范式下,供給(生產)和需求(消費)是相互影響和制約的,通過“交換”和“分配”進行聯結,供給(生產)決定需求(消費),需求反作用于供給,交換和分配也是由供給決定的,同時也反作用于供給,這是四者之間基本的邏輯關系。由此我們可知,供給(生產)始終是物質資料轉移矛盾運動的主要方面。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為我們分析當前我國經濟新常態下社會基本矛盾提供了方法論,但實際上2015年之前我國的經濟主張一直是采用凱恩斯的需求分析法,即擴大總需求,拉動經濟增長,但是,這種經濟增長方式帶來的最大問題就是資源耗費嚴重。“十二五”時期,我國GDP占世界的8%~8.6%,卻消耗了世界40%~47%的煤炭和9%~11%的石油,碳排放量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污染嚴重,除此之外,GDP中第三產業的比重也低于50%,遠遠低于發達國家70%的水平。一些傳統產業產能利用率極其低下,如鋼鐵、水泥、煤炭等行業出現了很多“僵尸企業”,這也是產業結構長期不合理的結果。這顯然已經忽視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對經濟增長規律的認識,沒有重視供給與需求,以及生產資料轉移的邏輯關系,所以重視供給結構的合理性以及體系質量和效率,強調經濟可持續性發展,是我國未來經濟政策的導向。2015年11月和12月,中央先后兩次工作會議上,正式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新常態下健康運行,要求從供給端和生產端管理出發,對生產要素市場和產品市場進行結構調整。生產要素市場主要從自然資源、勞動力、資本和技術等生產要素出發,延伸至微觀企業的生產方式管理和生產成本管理。產品市場是從產品供給數量、產品供給質量和產品供給結構出發,延伸至微觀企業的產品標準化管理和規范化管理。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指引下,我國經濟需要處理好生產(供給)和消費(需求)之間的關系,逐步實現GDP結構平衡和總量增長,建立國民經濟的合理比例關系,包括經濟結構、區域平衡、城鄉關系等。對需求和供給進行功能互補性調節,以政府政策拉動內需、增加基礎投入,并以市場需求刺激供給改革,注重供給的成本、質量及效率,實現經濟運行均衡式持續增長。
2. 創新驅動發展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論述了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之間的作用與反作用關系,實際上強調了兩者之間的均衡發展,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宏觀經濟總量均衡,二是經濟結構均衡。這是當初馬克思基于物質資料再生產是否能夠順利進行的視角進行論證的。現在的情況要比以前復雜很多,中國經濟有其獨特的發展背景和現狀,但是馬克思的論斷仍然有啟示作用,產業組織內部結構和產業間結構應該均衡發展,生產要素在不同產業和企業間合理配置,創造更多的經濟價值。可見,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來源于創新基礎上的效率提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三大發動機”,無論是制度變革,還是結構優化,抑或是要素升級,其核心都是創新。創新解決的是經濟發展動力問題,這正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靈魂所在。可以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質上就是一次重大的創新實踐。因此,要對生產領域的一些企業進行改革,關停并轉一些企業(如“僵尸企業”),通過主動性調整機制與被動性調整機制來解決“僵尸企業”和產能過剩問題(劉志彪,2016),將生產資料轉向那些效益好,能夠產生更多的經濟價值,有利于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企業,進而改變國民經濟整體格局。其次,要通過混合所有制改革完善國有經濟的所有制基礎,切斷國有企業與政府之間的各種軟預算約束紐帶,構建新型平等競爭體系(劉春元,2016)。最后,要堅持實施創新驅動戰略,提供創新創業的良好環境,培育市場發展新動能,增強企業活力,拓展新的增長空間。主要思路是以經濟體制改革為引領,聚焦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和開放環境,在國企、財稅、金融、資源價格、市場準入等領域加快突破,切實打破制約要素在城鄉區域之間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的體制機制障礙,全面提升配置各類要素與市場資源的能力。鼓勵新技術產業發展,培育高端制造業,放松管制和約束,優化服務,保持有效投資力度,著力補齊短板,激發企業積極性,增加有效供給和產出。
四、 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基于演化經濟學的發生機制分析
演化經濟學主要研究經濟發展中數量、質量及結構變化的過程(Northover, 1999)。除了技術變遷,制度也被納入到演化增長理論的要素中,兩者的演變及其關系驅動經濟增長(Foster & Potts, 2009)。基于演化經濟學對中國經濟現狀的分析,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 供給側要素結構的演化
經濟系統是一個選擇適應的過程,各種演化單元在系統中創新成長,并且選擇性的擴散到經濟系統中,隨著時間的推移,那些創新能力高且適應性強的單元在經濟結構中占據的比重將上升,經濟結構發生變遷,不斷演化。因此,供給結構的演化,包含要素單元的演變以及產出結構的演化。供給要素主要包括勞動力、技術創新、資本和制度創新。首先,我國的勞動力要素發生了變化,老齡化時代迅速到來,低成本優勢逐漸衰退,需要通過提升勞動者素質來提高生產率;其次,我國的技術創新要素也面臨巨大的壓力,因為西方的技術保護政策力度越來越大,而且產業價值來源越來越依賴于知識創新,所以創新驅動發展是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再有,資本利用也是我國經濟發展需要提升的要素,人口老齡化使消費結構發生變化,儲蓄率下降使投資減少,加之產能過剩帶來的“資產荒”,資本市場運行的效率就成為我們面對的新的問題,要解決融資難、融資貴的老大難問題,是“十三五”時期金融改革的重要任務;最后,制度創新一直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是驅動需求及供給演化的重要動力,我國的改革需要從制度變革做起,制度創新不足、政府效率不高、尋租行為嚴重等是上一個經濟發展周期出現的一系列問題,推進制度改革是當前最為緊迫的任務。因此,勞動力、技術創新、資本和制度創新構成了供給側的主要要素,這些要素在系統中不斷選擇和適應,使供給要素比例和結構不斷演變,共同推動經濟增長。
2. 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驅動供給側與需求側共同演化
中國經濟一直依賴于投資、消費和出口這“三駕馬車”拉動需求,這是構成我國需求側結構的主要因素。經濟發展中,三者的比例不斷發生變化,反映了社會總有效購買力在不同產業之間的分配比重。在演化經濟增長過程中,供給要素(勞動力、技術創新、資本和制度創新)與需求要素(投資、消費和出口)相互影響,共同進化,決定了經濟增長的方向和速度。首先,供給要素結構的變化影響收入結構,進而改變某些產業或產品需求結構;其次,技術創新也能引導新的消費偏好,技術擴散和消費需求的擴散締造了新的產業和業態,進而影響整個供給側結構的演化;再有,制度作為要素配置的激勵和制約因素,對供給側和需求側都產生重要的影響。制度對勞動力、技術、資本等其他供給要素都有系統性影響,這些要素的價格、交易模式和分配機制都起到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說,制度直接影響這些要素的配置效率,所以制定有效的制度、進行制度深度改革就顯得尤為重要。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一直處于一個高速發展的狀態,無論是供給側結構還是需求側結構,都處于不斷變化中,偏離平衡態,而演化經濟增長理論有助于解釋我國經濟增長的特點和本質。由前文對供給側和需求側共同演化的分析,勞動力、技術創新、資本和制度創新驅動供給側結構的演化,投資、消費和出口則驅動了需求側結構的演化,而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是我國經濟演化過程中的重要驅動力。當前,我國實施創新驅動戰略,就是要建立合理的創新體系,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增強國際競爭力,實現由低成本優勢向創新優勢的轉換。在制度方面,我國在供給側改革頂層戰略設計的引領下,各部委及各地方政府要制定相應制度,進行有效創新,如金融制度、稅務制度、勞動力制度、土地制度、環保制度等,以及產業政策、招商政策、行業規章等。
五、 結論與啟示
基于供給經濟學、政治經濟學及演化經濟學的相關理論,本文分析了當前經濟運行的狀態,梳理了影響經濟增長的需求要素和供給要素及其各因素之間的關系,從不同方向闡明了我國實施供給側改革的原因,并給出了實施供給側改革的主要途徑。
在供給經濟學理論視域下,總供給結構改善、減稅和放松管制是解決我國產能過剩、資源配置效率不高、企業交易成本增高等問題的重要途徑。解決我國產能過剩、資源配置效率不高的問題,需要對產業結構進行變革,改善總供給結構,并實行多渠道稅制改革,加大減稅力度,通過技術創新、簡政放權等措施提高市場化水平。在政治經濟學理論視域下,供需互補、創新驅動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供給(生產)和需求(消費)是相互影響和制約的,并通過交換和分配進行聯結,供給(生產)始終是物質資料轉移矛盾運動的主要方面。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指引下,我國經濟需要處理好生產(供給)和消費(需求)之間的互補關系,建立國民經濟的合理比例,使供給側健康運行,逐步實現GDP結構平衡和總量增長。在演化經濟學理論視域下,勞動力、技術、資本和制度構成了供給側的主要要素,這些要素在經濟系統中不斷選擇和適應,使供給要素比例和結構不斷演變,共同推動經濟增長。其中,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驅動供給側與需求側共同演化。
本文運用供給經濟學、政治經濟學及演化經濟學的相關理論討論了我國供給側改革的發生機制。供給經濟學為總供給結構改善、減稅和放松管制提供了理論依據,政治經濟學解釋了供需互補、創新驅動對我國經濟增長的驅動機理,演化經濟學為技術創新、制度創新提供了政策制定的方法論。很顯然,那種認為西方經濟學理論完全不適用于我國供給側改革的觀點是不準確的,在制定供給側改革相關政策的時候,應該結合我國國情,運用供給經濟學、政治經濟學及演化經濟學等相關理論,借鑒國際經驗,推動我國經濟健康增長。
參考文獻:
1. Foster, J., and J. Potts. A Micro-meso-macro Perspective on the Methodology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Integrating History, Simulation and Econometrics.SpringerBerlinHeidelberg. 2007, 2(1): 53-68.
2. Northover, P. Evolutionary Growth Theory and Forms of Realism.CambridgeJournalofEconomics, 1999, 23(2): 33-63.
3. SPR’s Macro-structural team. Structural Reforms and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Initial Considerations for the Fund. http://www.imf.org. 2015-10-13.
4. 馮志峰: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邏輯與實踐路徑》,《經濟問題》2016年第2期。
5. 賀芬、何碰成: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視角下福建高等教育發展路徑》, 《教育評論》2016年第12期。
6. 賈康、張斌: 《供給側改革:現實挑戰、國際經驗借鑒與路徑選擇》,《價格理論與實踐》2016年第4期。
7. 江小國、洪功翔: 《我國供給側改革的邏輯背景分析》,《經濟問題探索》2016年第10期。
8. 李翀:《論供給側改革的理論依據和政策選擇》,《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6年第1期。
9. 廖淑鳳、郭為: 《旅游有效供給與供給側改革:原因與路徑》, 《旅游論壇》2016年第6期。
10. 劉春元: 《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基礎》, 《人民日報》2016年2月25日第7版。
11. 劉偉、蔡志洲:《經濟增長新常態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求是學刊》2016年第1期。
12. 劉志彪: 《中國語境下如何推進供給側結構改革》,《探索與爭鳴》2016年第6期。
13. 沈坤榮: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經濟治理思路的重大調整》,《南京社會科學》2016年第2期。
14. 覃菲菲: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視角下我國海洋漁業轉型升級研究》,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學位論文2017年。
15. 文建東、宋斌: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
16. 楊競、楊繼瑞: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天然氣分布式能源發展研究——以四川省為例》, 《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6期。
17. 楊麗君、邵軍: 《新常態下德國工業4.0對我國供給側改革的啟示》, 《現代經濟探討》2014年第4期。
18. 袁志剛、饒璨: 《供給側改革——長期增長與短期波動的統一》, 《探索與爭鳴》2016年第5期。
19. 鄭海婷、劉小新: 《供給側結構改革視域下福建文化產業發展研究》, 《福建藝術》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