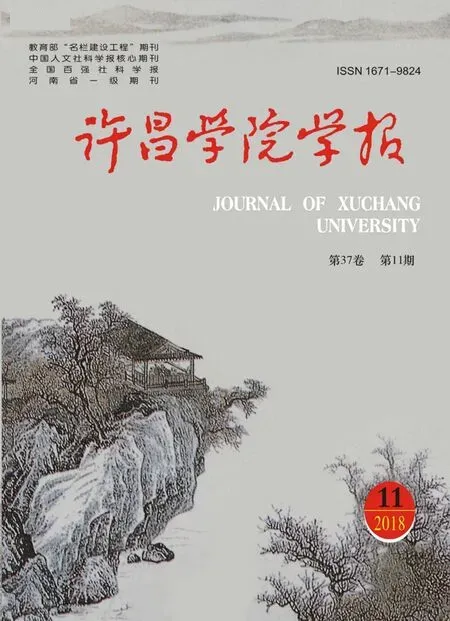陳瓘《尊堯集》的出版控制與作者心態
金 雷 磊
(三明學院 文化傳播學院,福建 三明 365004)
《尊堯集》為北宋南劍州沙縣(今福建三明)人陳瓘所著,該書是陳瓘以芻蕘之言明芻蕘之志的“芻蕘改過之書”[1]123。其著書意圖主要是批判王安石的性命學說及王黨“薄神考而厚安石,尊私史而厭宗廟”[2]281的行為,認為此種行為“變亂是非,不可傳信,宜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3]750-751。該書為我們研究北宋神、哲、徽宗時代政治、文化和社會方面的狀況,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其學術史上的價值不容忽視。宋徽宗時代,《尊堯集》在社會上的流傳和朝廷對《尊堯集》的控制,已經成了當時一個熱門的文化事件和政治事件,研究對《尊堯集》的政治控制及其傳播控制下的作者心態,顯得十分必要和有意義。
一、“元祐黨禁”下之書禁
北宋元祐年間,王安石推崇新學,扶植新黨,排斥異己,黨同伐異,控制舊黨之學術、思想傳播,對于元祐黨人的書籍編輯與出版活動也進行嚴格的控制:
“臣聞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矣。”此王安石之精義也。有三經焉,有《字說》焉,有《日錄》焉,皆性命之理也。蔡卞、蹇序辰、鄧洵武等用心純一,主行其教。其所謂大有為者,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謂繼述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謂一道德者,亦以性命之理而一之也;其所謂同風俗者,亦以性命之理而同之也。不習性命之理者謂之曲學,不隨性命之理者謂之流俗。黜流俗則竄其人,怒曲學則火其書。故自卞等用事以來,其所謂國是者,皆出于性命之理,不可得而動搖也。[4]115
王安石所推崇的新學,就是他的《三經新義》《字說》和《日錄》,追隨和附和王安石學說的,則有蔡卞、蹇序辰、鄧洵武、薛昂等人:“卞、武繼安石之志,昂等述蔡卞之事,而執此欺誕以為國是,豈不誤朝廷之繼述乎?”[5]85(大觀末)“臣聞紹圣四年,蔡卞薦太學博士薛昂上殿,昂乞罷講筵進讀史官書,而專讀王安石《日錄》《字說》”[5]86。陳瓘認為,蔡卞等人提議罷讀史書,專讀安石之書,是把虛妄欺誕當作國是,只會耽誤朝廷政事。
王安石認為以他為代表的新學“皆性命之理也”,而將其他不習此“性命之理”的學問稱為“曲學”,將不隨此“性命之理”的學者號為“流俗”。“今欲制天下之事,運流俗之人,當自拔于流俗之外,乃能運之”[6]391。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新黨“黜流俗則竄其人,怒曲學則火其書”。《尊堯集》被認為是“福建最早被禁毀的著作”,“此書之被禁毀,與北宋歷史上的‘元祐黨禁’有關”[7]381。
二、朝廷對《尊堯集》的出版控制
陳瓘編寫《尊堯集》,得罪了當朝權臣,從政和元年六月初五至六月十九半個月時間內,朝廷連續兩次下牒,取索該書,十分急迫。朝廷下令取書和陳瓘按令上書這一過程,在政和元年十一月《臺州羈管謝表》中有詳細的記載:
臣瓘言:政和元年六月初五日,準通州牒,準編修政典局牒,奉旨取索臣所撰《尊堯集》,請速為檢取,封角交付差去人。續又準通州牒,《尊堯集》系奉圣旨取索,不可遲緩。臣即于六月十九日申通州迄,依圣旨發遞前去,仍申編修政典局云:“上件《尊堯集》先合奏御,今匣內黃帕文字等并題作臣瓘謹封。伏望本局特為進入,于御前開拆。”今于十月初七日,準通州牒,準尚書刑部符,都省札子:“奉圣旨:陳瓘自撰《尊堯集》,語言無緒,盡系詆誣。不行毀棄,送與張商英,意要行用。特勒停,送臺州羈管。令本州當職官常切覺察,不得放出州城。月具存在,申尚書省。”[8]96
皇帝親自過問該書,下令取索,充分說明該書傳播面廣、影響力大。由于朝政為王安石黨人所把持,其言論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書籍也沒有得到公正的對待,陳瓘上交書籍后,朝廷就斷定陳瓘言論沒有頭緒,盡屬詆毀,下令禁毀,并將其貶到臺州羈留看管,陳瓘完全喪失人身自由,張商英也因此書遭罪。
沒過多久,即政和元年十二月,宋徽宗又下詔,官員臣僚不得傳習《尊堯集》:“其《尊堯集》仍令知臺州石誡于陳瓘、衡州于張商英處取。及元降付張商英御批真本并繳速聞奏。”[9]331陳瓘在《四明尊堯集后序》中,非常詳細地記載了該書被禁以及其本人被控制的來龍去脈:
政和元年十一月,始至竄所。二年正月,尚書省札子委臺守取索《尊堯集》副本。副本在明州徐璋秀才家,臺守于朝旨之外遣兵官突來追攝,囚之于石佛寺,然后遣兵官入家搜索,并牒明州遣兵官搜索徐璋之家。初,瓘之所撰《尊堯集》有二,合浦其一也,四明其二也。凡合浦所著,不忍以荊公為非,故其論皆回隱不直之辭。每自覽此書,內愧外汗,是故離家之日,獨取改過一集置于行筐。到臺不敢復閱,即以寄于數百里之外,屬友人藏之。及自石佛寺得釋,又遣仆往通州本家索取前集之稿,以俟再索。五月,果又有旨取合浦集副本。[1]124
朝廷在政和元年追查《尊堯集》后,將陳瓘貶到臺州。到臺州沒過多久,朝廷又于政和二年委臺守繼續查封此書副本,并將陳瓘囚禁在石佛寺。從石佛寺釋放后,朝廷又派兵往通州陳瓘本家索取稿本。該書四明本副本在明州徐璋家,朝廷派兵到徐璋家搜索。合浦本副本則有一集被陳瓘帶至臺州,由于查封嚴格,以致其不敢拿出來讀閱,寄給了百里之外的友人藏匿。朝廷對陳瓘《尊堯集》查封之頻繁、控制之嚴格,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
然而錄取副本,內外紛擾,又半年而后定。方追逮囚閉之時,旨外施行既不可測,顧計日前,因有系吝之意。既而愧且嘆曰:口談致命,而心則動搖,將何以善其死哉?念自離合浦以后,十年之間,光陰精力畢于此集矣,終誤咨詢,聲實俱墮,尚欲操之而不舍乎?初政典局,奉旨取索,瓘以此集未經奏御,非人臣所得先見,故亟封具奏,請于御前開拆,由是徑達一覽。方舜主繼堯之時,聞尊堯之說,舜心開納,留中不復降出,昔者竊聞之矣。[1]126
陳瓘此書立意,來自古人。只不過,書籍在向上傳播的過程中出現了問題,要么官員逮捕書籍作者與收藏此書的人,要么對其搜家。“方追逮囚閉之時,旨外施行既不可測”,表達的就是陳瓘對地方官員倒行逆施行為的擔心,地方官員的這些做法導致陳瓘也加強了警戒和提防,采取“未經奏御,非人臣所得先見,故亟封具奏,請于御前開拆,由是徑達一覽”的辦法,防止因言獲罪。
可見,朝廷及地方政權對《尊堯集》的傳播實行嚴格管控。朝廷對《尊堯集》的控制,顯然不利于以陳瓘為代表的忠義大臣的言論的傳播,也不利于朝廷官員之間不正風氣之轉變。“了翁之辨雖明,其迄不見省者,亦政、宣大臣無以正救為將順者歟”[2]337!岳珂對陳瓘書籍受到管控,不能在官員之間得到順暢傳播的情況,發出了自己的感慨。
三、出版控制下的作者心態
《尊堯集》在朝廷和當朝權臣的打壓與高壓控制之下,其傳播受到影響,甚至牽連到友人。陳瓘身心得到摧殘,也已感到疲憊。但這些打擊并沒有使陳瓘灰心喪氣,恰好相反,陳瓘仍然據理力爭,他一身正氣,愛國、忠君之心始終不變,初心不改。其心態歷程可以從其序文中窺得一斑:
及尚書省取索本副,札子付臺守,乃云:“其《尊堯集》元初進本在張商英家,已下衡州取索,茲乃實封,不下司。”密札之語,非萬方疏遠所可據窺者也。今除副本之外,尚如此稿,不敢復藏于私室矣。欲磬其余語,跋于此集之后,以俟后賢。而心力疲乏,恍惚健忘,每思索文字,則悸眩不寧。臨紙數休,勉強累日,僅能終篇。人知其臲卼且死,而不知其衰耗又如此矣,雖復戀此余生,將何以哉!又況絕祿以來,茍營活路,積垢如山,死有余愧,雖并舉百川之水,其將何以自滌乎?就使鷦鷯之命幸脫寬網,而身心垢憊,亦明時之棄物矣,敢不知乎!敢不知乎![1]126
從“不敢復藏于私室”可以看出,朝廷對陳瓘書籍的搜查很嚴,控制很緊。一旦被搜查出來,連人帶書都有可能不保。“每思索文字,則悸眩不寧”,這是因書籍傳播被控制而給作者帶來的后遺癥。每當想到對書籍及相關人員的查封情景,他往往頭暈目眩,心有余悸,惴惴不安。“臨紙數休”,多次寫作,中途輟筆,“勉強累日,僅能終篇”。即使是辭掉官職,對陳瓘來說,仍然沒有人身自由,處于茍且偷生的狀態。這段材料一方面描繪了地方官員對陳瓘著作的封殺與控制,另一方面也寫出了作者空有抱負,無法施展,擔憂度日,生不如死的窘態。
最初,陳瓘對朝廷報以樂觀態度。作為一名言官,得罪當朝權臣在所難免,一開始他還是堅信自己的冤情能夠得到洗雪,心存僥幸。“臣聞圣人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朝廷以一時之怒,黜忠諫之臣,此如日月之食也”(元符三年九月)[10]59。陳瓘認為朝廷罷黜忠諫之臣的行為如“日月之食”,人人可見,若能改正,則“人皆仰之”。
后來,陳瓘對朝廷不再抱有任何希望。即使生命受到威脅,也毫無畏懼,他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特別是著《四明尊堯集》后,他更加堅定了不顧個人生命安危的決心和意志:
蓋捐書不讀,亦不復為文,冥心待盡,自今日始。嗚呼!生而為太平采薪之民,歿作我宋無憾之鬼,復何事哉!而今而后,真可以忘言矣。此可與知者道,難于不知者言也。[1]126-127
“蓋捐書不讀,亦不復為文”,意味著《四明尊堯集》是陳瓘最后一部作品,他再也不讀書,不著文。“冥心待盡,自今日始”,表明陳瓘已做了最壞的打算,大不了以死殉國。生作大宋“采薪之民”,死作大宋“無憾之鬼”,其精神可謂“驚天地、泣鬼神”。即使是犧牲自己的生命,也不能阻擋《四明尊堯集》的編著和傳播。至于傳播內容,則“可與知者道,難于不知者言也”。事實證明,《四明尊堯集》就如喊向空谷的聲音,立馬傳來回聲,如投入江河的巨石,掀起大片漣漪,傳播效果立竿見影。
元祐黨禁背景下之書禁、言禁,波及到陳瓘及其友人,其實質是新黨、舊黨之爭在出版控制、言論控制方面的集中體現。他們這一行為,完全違背了人類社會言論出版自由的權利。以陳瓘為代表的言官,義不容辭,直言極諫,揭露了王黨虛偽本質,還原了黨爭歷史原貌。但在當時環境之下,陳瓘言論及書籍的傳播卻是極其艱辛的。新黨對陳瓘不斷施加壓力,給予打擊。在朝廷反復打壓之下,陳瓘對朝廷的態度急遽轉變,從希望變為絕望,個人也是從信心飽滿變得灰心喪氣。其書籍編纂、出版及傳播活動,為后人呈現了黨爭政治下具體生動的一面,體現了歷史的豐富性、復雜性。《尊堯集》保存了歷史記憶,使記憶得以永存。陳瓘作為一名言官,其直言、敢言的作風,對于當今也有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