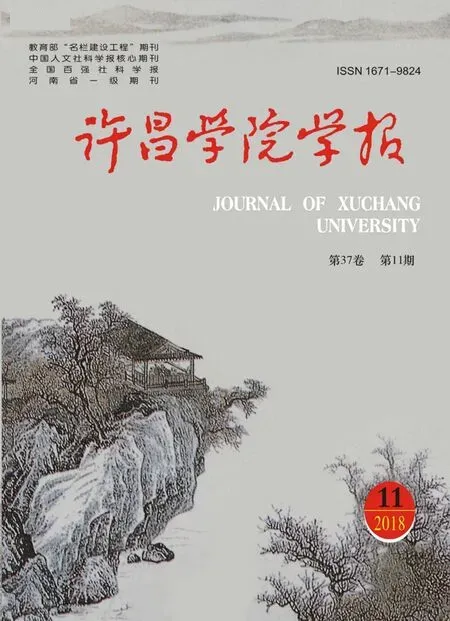痖弦現代詩中的鄉土意象論
司 方 維
(許昌學院 文學與傳媒學院,河南 許昌 461000)
痖弦,原名王慶麟,河南南陽人,1949年隨國民黨軍隊去臺。1954年洛夫與張默開始籌辦刊物《創世紀》,痖弦稍后加入,三人并稱為創世紀詩社的“三駕馬車”。痖弦本人寫詩的時間僅有十幾年,1965年便停筆不再創作。但正如詩人自己所表示的,“一日詩人,一世詩人”,痖弦的詩作不多,卻享譽文壇幾十載。痖弦是臺灣現代詩的領軍人物,但在“橫的移植”中也從未斷絕“縱的繼承”,他提倡“走向西方回歸東方”。在意象領域,痖弦自然也從未拒絕過“傳統”。雖然他寫的是“現代詩”,但詩中依然選用了大量的“鄉土”意象。這些鄉土意象,因詩人的離散者與知識分子等多重身份,呈現出多副面孔的交疊與分離。
一、離散者與知識分子的家鄉想象
痖弦對故鄉有深厚的感情,有書寫故鄉的主觀意愿,而且離家時已17歲,對故鄉的記憶較為清晰,“一個人如果有完整的對故鄉、慈母的記憶,可能夠他寫一輩子”[1]2。遷臺前的痖弦長時間生活于鄉間,離家前的河南雖然已經開啟了現代化進程,但現代工業文明的特征并沒有充分地顯現,所以留在痖弦記憶中的物象多具有鄉土特征。即便他遷臺之后不再長期居于農村,但具有鄉土特征的意象也是信手拈來。
鄉土意象,常見于痖弦的鄉愁詩中。《紅玉米》是痖弦鄉愁詩的代表作,詩人用了戲劇化的手法再現家鄉生活的場景,將難解的鄉愁凝聚于鄉間常掛在屋檐下的玉米這一農作物上,又一一具象化為蕎麥、桑樹、嗩吶、叫哥哥(蟈蟈)、銅環等農家生活常見的動植物及器具。不僅是痖弦,其他臺灣詩人的鄉愁詩也多有此特征。同為河南籍的臺灣詩人文曉村,他的《想起北方》等詩作也是選取楊柳、蘆笛、村邊河流等意象。還有其他詩人的作品,如洛夫《邊界望鄉》中飛起的白鷺、啼火的鷓鴣,蓉子《晚秋的鄉愁》中的雛菊、古老花甕與遠山,舒蘭《鄉色酒》中代表原鄉的柳樹。
痖弦所受的河南文化熏染,不只表現在具有河南鄉土特征的意象上,更在于深植于心的憂國憂民、傷時感事等精神文化內核。詩人不僅敘寫離鄉游子的鄉愁之苦,也在私人化的情感中灌注了作為外省人對流散、戰爭、苦難及人類命運的思考。定居臺灣之后,痖弦又寫了《鹽》《戰時》《乞丐》等以大陸為背景的詩作,寫二嬤嬤、我母親、乞丐等眾多底層人無力應對戰爭、貧困、饑餓等諸多災難,在榆樹、豌豆、蕎麥、酸棗樹、野狗、宗祠廟宇等組成的鄉間,以“鴿灰色的死”[2]58作為生命的終結。
同樣回望故鄉,上述兩類詩中的鄉土意象卻面貌迥異,前者是鄉愁的具象之物,滿溢溫情,后者是底層敘事中的苦難象征物。《紅玉米》一詩雖難掩哀愁,但也正是此種情感反證了痖弦對故鄉的思念。在時光的濾鏡之下,私塾里冰冷的戒尺都有了濃濃的溫情,孩童時滾過的銅環更是承載了人生難得的愉悅與溫馨。銅環是痖弦多次使用的一個意象,如《春日》中“賜男孩子們以滾銅環的草坡”、《斑鳩》里“女孩子們滾著銅環”“太陽也在滾著銅環”。銅環這種孩童玩具雖然古老、簡陋,但卻是童年里最為純摯的快樂,所以能在不同主題的詩中代表了愉悅、美好和希望。同樣的鄉村生活,在《鹽》里卻蒙上一層凄愴。榆樹、豌豆都是鄉間常見的植物,鄉童滾過銅環,也都爬過榆樹,摘過豌豆,但《鹽》中的榆樹和豌豆不像紀弦《一片槐樹葉》中的“槐樹”是故鄉的代言者,也沒有蕭紅后花園里祖孫的笑聲,反而都成了死亡的幫兇,詩中同時還出現了禿鷲和野狗——與死亡密切相關的動物意象。
鄉土意象在痖弦詩中的裂變,源自痖弦多重身份的交疊與歧異。雖然當時生活的鄉間,時局動蕩,土匪橫行,但痖弦年幼時家里有田有地,不愁溫飽,加之年紀尚小,稚嫩懵懂,不知生活苦,原鄉的記憶是美好的。作為被迫離鄉的離散者,離鄉日久,歸家無望,強烈的思鄉之情讓離散者的認知裝置自帶情感濾鏡,產出的家鄉符號更加趨向完美。痖弦還把這種情感符號帶至鄉愁之外的詩歌創作中。除了上述銅環意象之外,春日、蕎麥、地丁花等痖弦詩中的重要意象,也都帶有濃厚的故鄉印記。
痖弦是離散者,同時也是具有強烈自覺意識的知識分子。離散者身份與知識分子身份交疊時,痖弦回望家鄉的視界中出現了底層人的生存境遇。河南苦難極多,所以痖弦年幼時雖然生活尚可,但仍見過非常多的人間悲劇。旁觀的經驗,經過知識分子身份的再審視,成為難得的創作題材。拿著打狗棒的乞丐無田無產,多數時候居住在關帝廟里,有時會把洗好的襪子曬在關老爺的刀上,這些生活細節成為《乞丐》一詩的素材。一九四二年河南發生大災荒時,痖弦已十多歲,見到了由饑餓引發的大規模非正常死亡,于是有了《鹽》里苦求一把鹽而不可得的二嬤嬤。乞丐和二嬤嬤是詩中敘事的個體,但經過知識分子認知裝置重組后,都跨越了地域的局限,成為底層群體的代稱。知識分子“代表所有那些慣常被遺忘或棄置不顧的人們和議題”[3]17,所以痖弦詩中除了有來自河南的二嬤嬤和乞丐,也有唱《玉堂春》取悅貴人、“與白俄軍官混過”的坤伶(《坤伶》)、在戰爭中失掉一條腿的軍人(《上校》)、漂泊海上的水手與他在“煙花院里”討生活的妹妹(《水夫》)等各色底層小人物的悲苦。
二、東方情懷與文化傳統的鄉土呈現
痖弦早期提倡“新民族詩型”,著重于“中國風”與“東方味”。后來轉攻西方現代主義,強調“超現實性”“獨創性”“純粹性”與“世界性”,成為超現實主義的實驗者與探索者,但旋又回歸傳統,致力于熔鑄中國古典詩學與西方現代主義。在意象領域,也能在痖弦詩中看到東西方交融的特征。其中鄉土意象這一分支,部分承擔了中國因素的任務。
痖弦的詩作中,以鄉土意象命名的就有《斑鳩》《土地祠》《山神》《紅玉米》《蕎麥田》等。另外,中西方意象在痖弦詩中經常交互出現。像《春日》一首,以“主啊”開頭,隨后出現的意象則是嗩吶、日晷儀、草葉、地丁花、銅環、月季、毛蒺藜、酸棗樹等。當然,具有鄉土特征的意象并不必然等于東方風情。如痖弦詩中用過的花類意象——薔薇,既是中國文學中的傳統名花,也是西方文學中的重要意象,中國詩人詠薔薇的詩作有謝朓的《詠薔薇》、杜牧的《薔薇花》、顧磷的《薔薇洞》等,西方作品則有西格里夫·薩松的代表作《于我,過去,現在以及未來》中的經典詩句“心有猛虎,細嗅薔薇”(In me the tiger sniffs the rose)等。
鄉土意象本身可能并無嚴格的東西方之分,但在痖弦的詩作中鄉土意象明顯傾向于東方,除了作為“東方味”的重要構成之外,它還有一個重要的職責:與甲骨文、鳳輦、宮墻等具有古老文化氣息的意象一起,共同成為傳統文化的象征物,出現于傳統與現代的膠葛中。
寫于1957年的《一九八〇》預想了二十多年后的生活,彼時“我們”在澳洲有一座童話般的草坡上的小木屋,妻子說這里的生活就是在畫片兒里,而“我”則認為各種顏色的地丁花是“寂寥”的,在山坳里漂泊的云沒有什么事好做,奶牛贈送給我們最好的奶汁,但珊珊不喜歡牛奶里的草味兒,山谷離太遠,沒有什么可送我們的……“我”想要改變這種生活形態,到小鎮上買點畫片兒,在門楣上掛上祙筒兒。這首詩從表面上看表現了一對夫妻生活觀的差異,夫向往的是現代的喧鬧,妻喜歡的是古雅的寧靜。雖然遠在澳洲,但妻子所喜歡的這種由木屋子、地丁花、藍天、白云、手工勞作組成的生活與痖弦記憶中的家鄉生活并無二致,都是農耕文明的復刻。丈夫喜歡的畫片兒則已經不是自然產物,而是工業制品。現代人不認可農耕文明悠長、緩慢、單純的生命節奏,向往沒有“那么多的明天”的快速、駁雜與喧囂。
《一九八〇》中的傳統與現代的矛盾還只是隱身于夫妻之間的玩笑斗嘴,夫妻之間的矛盾還是柔性的,《芝加哥》則直接設置了傳統與現代對立的結構,體現了對現代工業文明的反思。如“自廣告牌上采雛菊”一句,“雛菊”這一來自土地的意象顯然是美好的,“采雛菊”是我們親近大自然、與大自然和諧相處的象征,但“廣告牌”卻是工業社會的產物,或許美麗,但冰冷、虛假、無生命。“刈燕麥”也需“自廣告牌上”。“麥子”意象是痖弦詩中反復出現的重要意象,在《早晨》《戰神》《上校》《三色柱下》《一九八〇》《深淵》等詩中反復出現,此外還有蕎麥、燕麥、黑麥。與地丁花、雛菊、草坡等植物類意象相比,燕麥這種農作物類的意象,不僅與農業文明關系緊密,還關系到民生,卻仍不能在工業社會中占據一席之地,這是現代文明造成的畸變。電纜、煙筒等現代工業文明的產物,帶給現代人物質豐足的生活,但冰冷、堅硬的現代建筑也折斷了天使的翅膀,現代人心理日益貧困化,“靈魂蛇立”[4]167,精神陷入空虛、迷茫與荒誕,身份迷失的同時價值失衡。
“深淵”是痖弦用來定義現代文明的意象,與之相對的恰好是痖弦的故鄉——平原。在《芝加哥》中,“老家鄉”再次鄭重登場。家鄉依然是有草坡、有野狐的舊模樣,與離散者的故鄉想象重疊在一起,依舊是詩人理想生活、理想文化的具象。
三、鄉土裂變:現代文人的文化理想
痖弦對現代文明的反思,視角來自他現代知識分子的身份。他的知識分子認知裝置,一方面驅使他為底層小人物的疾苦奮筆疾書,另一方面也驅使他聚焦于現代工商業社會發展起來后所呈現出的種種負面傾向。在前者,鄉土意象的內涵指向與離散者的家鄉想象分離;在后者,卻又與離散者的家鄉想象交互重疊,老家鄉成為過去的黃金之地,也成為現代人的救贖之地。
回望鄉土以救贖現代工商業文明的諸多弊病,并不是痖弦所獨有的思考方式。比如黃春明——臺灣鄉土文學的代表作家,與隸屬現代派文學的痖弦在文學觀上可能并不相同,但在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關系的解讀上他們卻保持了很大程度的一致。黃春明本身從事過廣告行業,他在《兒子的大玩偶》《兩個油漆匠》等小說中也如痖弦一樣多次用過廣告意象。廣告是現代社會刺激消費主體的重要途徑,廣告背后豐富的商品集聚了現代人的物欲,以此為目標正適宜于批判現代工商業文明對人心靈的異化。物質財富不斷增長、堆積,但“生產資料和服務大量提供的時候,一些過去無需花錢唾手可得的財富卻變成了唯有特權者才能享用的奢侈品”[5]37。生機盎然的自然環境、悠長的時間、柔軟的情感、心靈的寧靜等工業社會的奢侈品,在痖弦等人看來正是在鄉土世界能夠“唾手可得”的。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鄉土被塑造成與城市相對立的理想之地。而且這個理想之地不僅是個人生活方式的選擇,還是文明秩序的象征。
但這種鄉村形象是被簡單化、神化了的鄉土。痖弦也寫鄉土的苦難,但在二嬤嬤、乞丐們的背后,其實也隱藏著一個安穩富足喜樂的鄉土,那是在痖弦看來鄉土世界應有的模樣,是不應該被戰爭、災荒等外在因素摧毀的鄉土世界。就痖弦而言,他因為遷移而失去了與鄉土的直接聯系,他的鄉村回憶是與童年、青春回憶融合在一起的。師陀也曾在《果園城記》中寫過小城:“每一粒沙都留著我的童年,我的青春,我的生命。”這種對童年的留戀之情讓沒有回鄉意愿的“我”都暫時停下了腳步。但從五四文學中成長起來的師陀,是以現代啟蒙者的身份審視果園城的,這種銳利的視線最終穿過童年情感結構揭開小城幸福平和表象下的滯重、封閉與罪惡。雖然痖弦也認可河南是多苦難的,但痖弦對現代文明的態度與寫《果園城》時的師陀已發生分歧,痖弦的認知立場已經傾斜于現代文明批判,而不是國民劣根性反思,所以他的童年情感結構成為鄉村回憶的濾鏡。因為個人的情感通道,田園化的鄉村成為現代人最容易抓到的黃金之地。
神化過的鄉土與現實的鄉土并不重疊,也不與農村人眼中的鄉土等同。就像另一位河南作家劉慶邦在《遍地白花》中所寫的,村里人認為秋收前有葫蘆、有果子、有莊稼的花紅柳綠是美,城中來的女畫家卻認為古舊的門樓、老鬼柳子樹、廢棄的碾盤、快散架的太平車等是美。痖弦詩中多次出現的蕎麥,也是《遍地白花》的核心意象,遍地白的蕎麥花即是女畫家回到鄉村所要尋找的夢中之花。小說的表層結構是用一個城中人的視角去寫鄉村之美,是城里人回鄉下尋找靈魂安棲之地。但女畫家與村里人的關系并不止于此,這一外因的介入,讓懵懂的鄉民開始認識到人與物外表美丑之外的歷史底蘊和文化內涵,啟動了以小扣子為代表的農村人的情感自覺。換言之,女作家扮演了啟蒙者的角色。所以小說以小扣子期盼著畫家再來作為結尾,其實這也是小扣子的“離鄉”,是鄉村變動的預兆。在一篇唯美的鄉土題材小說中,鄉土也從內部裂變了。已經走出鄉土的知識分子,再如何熱愛鄉土,也難以遮蔽知識分子與農民兩種身份之間的差異,他們的田園鄉土夢想并不是農民的夢想。真實的鄉土世界是復雜的、多樣的、變動的,部分老農民固守土地,更多年輕人向往城市。然而不管主觀意愿為何,都不能阻止現實鄉土在現代化的進程中被邊緣化,被同化,另外還衍生出城鄉貧富差距增大、農民工進城等問題,這些內容可以在黃春明以及李佩甫、劉慶邦等作家的鄉土題材作品中看到。
純真的鄉村“是種針對新時代的壓力而產生的鄉村社會的概念”[6]4,是知識分子文化理想的投射。所以田園鄉土只能是“過去式的”,是一種懷舊的傷感。現代知識分子走出鄉土之后,用文人的如花妙筆、用自我的文化理想重塑了鄉土的形象。純真鄉土的虛妄,是知識分子返歸鄉土理想的虛妄,也是知識分子在社會轉型期身份懸浮無法落地的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