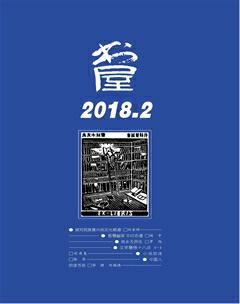冰火豈止二重天(六)
王澄霞
《狐貍庵食道樂》是日本“國民作家”遠藤周作1970—1994年間發(fā)表的散文輯錄,通過描繪各種尋常吃食再現(xiàn)當年事懷念當年人。作者頻頻回望深情眷顧,試圖將那殊可留戀的往昔歲月用筆墨一一定格封存,無奈最美的時光總是走得最急最快。“一切景語皆情語”,在他沖淡內(nèi)斂的筆調(diào)中,流露出的還是年歲徒增的無奈和感傷。
等再讀了遠藤的《丑聞》、《海與毒藥》、《沉默》、《深河》等作品后發(fā)現(xiàn),這些奠定遠藤日本文壇樞紐地位的小說代表作,無一不滲透著關(guān)于生命、宗教、哲學、歷史的強烈思考和沉重追問,與散文集《狐貍庵食道樂》風格迥異:就像一個是眉頭緊鎖面容沉郁的金剛,一個卻是眉開眼笑胸懷敞亮的彌勒;一個恨不能將人的五臟六腑放在顯微鏡下一一解剖審察,一個則嘴角常含笑意、將生活中的一切都視為歲月的饋贈而心懷滿足和感恩;一個用筆狠辣不留情面,猶如濁浪排空劈頭蓋臉無處逃遁,就如《朝日新聞》評價《深河》的那樣“給人巨大沖擊和感動,劇烈的沖擊猶如要擠碎人的身體,無邊的感動則令人窒息”,一個則飽含溫情,不疾不徐娓娓敘說隨風往事,猶如“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同一個作者,散文和小說的風格不啻霄壤之別。所以,臺灣中正大學的郝譽翔教授也“不免要好奇,到底哪一個才是真正的遠藤呢?是道德的神圣使徒呢,還是平凡的日本歐吉桑?也或許,陶然于‘狐貍庵平凡美食之樂的,才是真正的日本之味,也才是真正的遠藤之味吧”。筆者認為,怒目金剛和低眉菩薩是遠藤性格的不同側(cè)面,都屬“真正的遠藤之味”。
一
《狐貍庵食道樂》中關(guān)于“狐貍庵”的得名,遠藤在他的散文《狐貍庵閑話》中曾有提及。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遠藤先生為了養(yǎng)病而遷居至町田市。當時的町田鄉(xiāng)土氣息濃郁,多農(nóng)田果園,并常有狐貍出沒。遠藤先生揶揄自己遠離塵囂、游手好閑于鄉(xiāng)間,遂稱自己的居所為“狐貍庵”,并自稱“狐貍庵山人”。“食道樂”之“食”,遠非滿足口腹之欲的食品那么簡單,在遠藤看來,“食”就是生活之“道”,就是人生觀和價值觀:
想想,為了長命百歲,卻得放棄人生所有的樂趣。
沒有煙的人生,戒了酒的人生,舍棄甜食的人生,只吃喝奶酪或牛奶的人生,想象那樣的人生,我總覺得寂寞。
結(jié)果發(fā)現(xiàn),原來這只是價值觀的問題,完全取決于個人。究竟是為了長壽而舍棄人生種種樂趣,只是為了健康過生活呢,還是想著人終將一死,縱使短命,也要過著吃好吃的、過自己喜歡的生活。
如何選擇,其實只是人生觀的問題。而我呢,我想吃好吃的、喝好喝的東西,也想繼續(xù)抽煙、喝酒,還想要長命百歲。但是兩者能否兼得呢?根據(jù)K博士的說法,是不可能的。
既然長命百歲與縱情享受口腹之欲不可得兼,那還是選擇好吃好喝充分享受世間美味。因為美好的“食物”及其“食”用過程充滿快樂和意趣,“妙處難與君說”,即使因此縮短壽命,還是在所不惜。
其實,在追求精致美味已蔚然成風的今天,遠藤筆下傾注濃情的那些“美食”譬如竹筍、蠶豆、烏冬面、櫻桃等等,都只是尋常食物,食材易得,烹制過程也無須多少技術(shù)含量;而像“湯豆腐”、“關(guān)東煮”、“燉里芋”、“芹菜沙拉”這些作者眼中的至味,以今天的口味品來也幾近簡單粗糙。再如,遠藤記憶中的美酒其實只是酒精勾兌品,因為二戰(zhàn)結(jié)束后日本生活條件艱難,酒成了絕對的奢侈品,“回想起來……我在二十歲以前,沒有喝過酒。不是不喝,而是那時戰(zhàn)事方酣,就連那些有權(quán)有勢的大人都無法輕易取得酒,更遑論我們這些窮學生,甚至連私酒都買不到,于是只好拿酒精摻水喝。……但那滋味卻是至今也忘不掉”。遠藤回憶當年眾人常常蜂擁至那個彌漫著尿臊味、嘔吐物臭氣以及廉價食用油味的小街,有時還因囊中羞澀被店主趕了出來;但只要喝到了“猶如洗米水的Kasutori,感到無比開懷”,當年生活之簡陋令人心酸,實在缺乏美感可言。但時過境遷,經(jīng)濟窘迫物質(zhì)匱乏的時代已經(jīng)一去不返,而關(guān)于“食”的回憶與遠藤的青春歲月相牽系,當年朋輩的音容笑貌、師生間的體恤關(guān)愛、店家少女的暗中示好都被一一凸顯,這一切都令步入暮年的遠藤回想起來溫馨甜蜜又無比惆悵。
遠藤認為“每個人的心中應(yīng)該都存有某個能喚醒少年時代記憶的食物,只要聞到那食物的氣味,那些時光已遠去的閃亮回憶,那些點點滴滴的情感,甚至那時的風景都能歷歷在目。而且,仿佛再也沒有其他東西比得過那些食物的美味”。無獨有偶。魯迅在《社戲》中也表達了同樣的感懷:“真的,一直到現(xiàn)在,我實在再沒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戲了。”其實,六一公公家的蠶豆第二天吃就覺著不過如此;而那場夜戲只是殘戲,只是小旦、老旦、很老的小生輪番咿咿呀呀地唱,連“最能翻筋斗的鐵頭老生也不肯顯本領(lǐng)給白地看”。可這些都成了時年四十二歲的魯迅童年記憶中的至味和最美。
朱自清的記憶中也有至美的“白水豆腐”:
說起冬天,忽然想到豆腐。是一“小洋鍋”(鋁鍋)白煮豆腐,熱騰騰的。水滾著,像好些魚眼睛,一小塊一小塊豆腐養(yǎng)在里面,嫩而滑,仿佛反穿的白狐大衣。鍋在“洋爐子”(煤油不打氣爐)上,和爐子都熏得烏黑烏黑,越顯出豆腐的白。這是晚上,屋子老了,雖點著“洋燈”,也還是陰暗。圍著桌子坐的是父親跟我們哥兒三個。“洋爐子”太高了,父親得常常站起來,微微地仰著臉,覷著眼睛,從氤氳的熱氣里伸進筷子,夾起豆腐,一一地放在我們的醬油碟里。我們有時也自己動手,但爐子實在太高了,總還是坐享其成的多。這并不是吃飯,只是玩兒。父親說晚上冷,吃了大家暖和些。我們都喜歡這種白水豆腐;一上桌就眼巴巴望著那鍋,等著那熱氣,等著熱氣里從父親筷子上掉下來的豆腐。
遠藤的美食回憶中也有類似的“湯豆腐”:“小鍋以酒精燈溫熱,鋪上昆布,準備好湯豆腐,等到湯滾時再倒進些許的酒,豆腐吸足了酒味,真是好吃。……我吃著湯豆腐,啜飲著酒,緬懷的卻是年輕時的光景。對別人來說,或許是無謂的事,但對我而言卻是人生中的重要一幕。”筆者后來如法炮制了“白水豆腐”和“湯豆腐”,味道實在不過爾爾。endprint
事實上,記憶中的美味往往遠非舌尖上的真實感受,更多的還是帶著個人的主觀情感。記憶是有選擇性的。時間流逝歲月留痕,距離產(chǎn)生美。在回憶的網(wǎng)篩過濾之下,有一些東西分別被放大或被汰除。留下的、放大的是對一切美好的追懷,汰除的、過濾的是與往事相隨的種種辛酸、苦難和眼淚。時空距離造就并越發(fā)地強化了這種美好,這就是為何故鄉(xiāng)、童年或初戀往往在回憶中最為溫馨詩意和甜美。沈從文筆下的湘西鳳凰令多少讀者心馳神往,只有作者本人知道他曾一朝踏上歸途,真的把故鄉(xiāng)盡收眼底,他是何其的失落迷惘并深悔那次回鄉(xiāng)之行。
二
平心而論,本書文風平和沖淡溫馨內(nèi)斂,但是其中《美哉“吾家傳統(tǒng)的好味道”》(1974)一篇卻是例外,文中遠藤對女性的歧視和敵意溢于言表,對現(xiàn)代日本女性走出家庭走向社會,與男性/丈夫平起平坐疾首蹙額扼腕頓足;對所謂日本傳統(tǒng)美德“荼毒媳婦”的日漸式微無比失落不勝唏噓。
最早把武士道介紹到西方世界的日本男性新渡戶稻造(1862—1933)在其《武士道》一書中這樣介紹日本女性:“日本女性所受的全部教育都圍繞著家庭,無論是學習武功還是藝術(shù)。她們永遠不會忘記自己在爐灶邊的責任。……從小,她們就沒有自己獨立的意識,她們的一生就完全在奉獻。”“女子為她的丈夫和家庭舍身……女子否定自己的價值,傾其所有幫助其夫,是家庭存在的基礎(chǔ)……女子心甘情愿幫助丈夫,是她存在的價值。”新渡戶將日本女性的卑微處境視為當然,并以“心甘情愿”、“傾其所有”、“奉獻”、“幫助”、“價值”等“高大上”用詞相敷飾,仿佛日本女性的生活充滿了幸福感和成就感,這真是不折不扣的“將屠戶的兇殘化為淺薄的一笑”了。
深受歐風美雨洗禮的二十世紀的遠藤,固持同樣的男權(quán)觀念和對女性的刻板印象,一心期望女性被固化在灶臺邊,以盡情享受作為男性/丈夫的絕對權(quán)威,于此亦可窺見日本大男子主義何其根深蒂固,遠藤認為女性的全部職能和所有價值就是相夫教子打理家務(wù)包括練就精湛廚藝。在他眼中,女性/妻子依然只是家政事務(wù)的天然的勞作者,而且只應(yīng)做得更好而不該有些許差池。如果身為妻子卻做不出一手令丈夫滿意的好飯菜,還逼得一些日本大男人去學烹飪,那她就簡直罪大惡極天理不容。他非常贊賞前輩日本男人的大男子主義作派:“日本男人回家后只會開口對老婆說三句話,那三句話就是:‘洗澡、‘吃飯、‘睡了。”……“只說這三句話,實在堪稱日本大男子主義的表率。”
遠藤還將永井荷風“女人啊,若無管束,不是變成懶婦就是奸婦”一語推崇為至理名言;遠藤感慨“日本的媳婦之所以變得如此懶惰,為所欲為,完全是因為日本自古流傳的美德‘威嚇媳婦、‘荼毒媳婦已經(jīng)消失殆盡了,難道不是嗎?”他認為自己母親一輩的好廚藝、“吾家傳統(tǒng)好味道”皆仰仗于婆婆的“荼毒”:“婆婆愈像魔鬼,愈能成為教育出好媳婦的專家。”“婆婆沒了骨氣,媳婦才會使亂。”遠藤贊美母親們的廚藝,從未設(shè)身處地體察當初母親們所遭受的“荼毒”之苦。遠藤欣賞和留戀婆媳之間的“荼毒”循環(huán),即婆婆“荼毒媳婦”、媳婦升格成婆婆后繼續(xù)“荼毒”她的媳婦:“媳婦與婆婆就如狗與猴子,彼此的關(guān)系建立在憎恨上”;“狐貍庵認為,應(yīng)該再度賦予婆婆應(yīng)有的權(quán)威,再度喚醒‘威嚇媳婦、‘荼毒媳婦美德,而這也是日本女子教育中不可欠缺的,事到如今實有重新檢討、納入的必要。”呼吁身為婆婆的婦女“應(yīng)該共組婆婆聯(lián)盟,借此研究該如何荼毒媳婦的課題”。
美國社會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二戰(zhàn)末期在她著名的研究日本民族文化的《菊與刀》一書中有如下陳述:“在社會生活中,日本的女性從小就處于劣勢地位。小時候,她們要盡力維護兄長的權(quán)威,長大后則要努力侍奉好自己的丈夫,只有老年時,等自己的兒子長大娶了妻子,她才能有一些權(quán)威的資格。”“對于夫妻關(guān)系,傳統(tǒng)日本絕且對是男權(quán)主義的。女人不僅要在家相夫教子,而且一切都要聽從丈夫的安排。甚至是丈夫到妓院玩樂的賬單寄到家里,妻子也會毫無怨言地付賬。”雖然陳述同樣的事實,身為女性的本尼迪克特顯然對日本婦女的卑微處境充滿同情。在中國,以趙樹理為代表的男性作家也在《小二黑結(jié)婚》、《孟祥英翻身》等作品中對山西太行山區(qū)“娶到的媳婦買到的馬,由人騎來由人打”、“十年媳婦熬成婆,婆婆再把媳婦磨”等陳規(guī)陋習都痛加批判,體現(xiàn)了一種樸素的人文情懷。遠藤周作身為日本男性,自然對日本女性的生存狀態(tài)更加了如指掌洞若觀火,可他卻毫無了解之同情,有的盡是對日本傳統(tǒng)婦女廚藝的津津樂道和對日本現(xiàn)代婦女的種種怨責。當然,遠藤也時時懷有與美女櫻花樹下同行或良夜對酌這樣的綺夢或渴盼;他甚至另有閑情來深究女性小便使用衛(wèi)生紙“擦拭時從前面往后擦還是由后面往前擦”這樣猥瑣無聊的細節(jié),還自詡為這是解悶的冶趣,這就實在讓人驚詫莫名了。
日本婦女的溫馴謙恭其實早已世界聞名。林語堂先生就曾調(diào)侃說“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國的鄉(xiāng)村,屋子里裝有美國的水電煤氣管子,有個中國廚子,娶個日本太太,再找個法國情人”,這種享樂人生觀中同樣有著男性中心主義的清晰烙印。
平心而論,隨著婦女解放運動的世界性展開,二十世紀以來日本婦女的生活內(nèi)容生活重心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她們早已走出家庭走向社會,走向自主獨立,與男性平起平坐平分秋色,這是社會文明發(fā)展的必然。遠藤身為著名作家,性別歧視盤踞頭腦,居然呼吁重揚“荼毒媳婦”的悠久傳統(tǒng),一廂情愿希望歷史開倒車,著實令人震驚。
遠藤周作擅于洞察和剖析人類心靈深處黑暗大陸,而這本書則讓讀者得以清晰窺見作家本人靈魂的陰暗一角——對女性根深蒂固的偏見和敵意。這倒真是體現(xiàn)了遠藤性格的多面性和復雜性。當然,指出這一點,并不因此妨礙我們對這位著名作家應(yīng)有的敬意。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