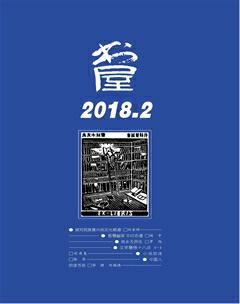小說如詩
韓秀
一
長久以來,我堅持文字的高雅、純凈,感覺上,那是寫作者人格的一種體現,不容輕忽。年輕時走過苦難,那時的世界黑暗而殘酷,面對丑惡,未曾改變自己所使用的語言,依然溫文爾雅,不肯向粗俗低頭。人到中年,有了機會提筆書寫,更是抱定宗旨,描寫人間地獄不必使用惡俗的文字。因之,對于抱持著同樣宗旨的作家們,心生敬意。
柳德蜜拉·烏利茨卡婭出生于1943年,親眼見證了蘇聯時代的種種倒行逆施。她的專業是遺傳科學,在這個領域工作多年。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蘇聯解體之時,將近五十歲的烏利茨卡婭開始了文學創作,而且一炮而紅成為當代俄羅斯文壇最受歡迎的女作家。這絕非偶然,心細如發的烏利茨卡婭感覺到機會來臨了,她有了自由書寫的可能性,于是全力以赴,在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黃金時代的沃土上,栽種起一株株風姿綽約的參天大樹,《索涅奇卡》便是其處女作。她以認真嚴謹的文風自律,優雅的筆觸飽含對筆下人物深刻的關懷。樸實、簡潔、內斂的文字張揚了俄羅斯文學傳統的圭臬,于是,小說如詩。熊宗慧教授的譯文忠實傳達出小說的原汁原味,使得華文讀者能夠領略原作的風采。
索涅奇卡不僅是一條書蟲,而且是一位書癡,她讀一本書的時候幾乎處于“昏迷”的狀態,從第一頁的起始到最后一頁的終了,她都處在這樣一種全身心投入的半昏厥的狀態中。夜間的夢也是在持續的“閱讀”中,這種閱讀熱情在睡夢中尤其變本加厲,“她就是理所當然的女主角和男主角,循著早已熟知的作者意旨和自己希望的情節來發展,朦朦朧朧地演出……”
這樣的一位讀者,從七歲到二十七歲瘋狂讀書,對于書籍這樣一件物事必然地有著她獨特的要求。果然,“隨著歲月飛逝,她學會了如何從浩瀚書海里分辨波濤巨著和微浪凡書”以及“拍岸碎沫”。書是有著高下之分的!索涅奇卡在圖書館地下藏書庫暗無天日的環境里自得其樂地整理著無數的目錄卡、應付著來自樓上的無數的借書單、搬運著沉重的大部頭書籍的同時,相當篤定地對書籍有了非常清醒的認知。
終于,她下定決心要進大學念俄國語文系。就在這關鍵時刻,蘇聯投身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為了避開戰火,索涅奇卡同她的父親搬遷到歐亞接壤處的斯維爾德羅夫斯克。搬遷帶來的困擾阻擋她的閱讀只有一個極短的時間,稍一安定,她馬上走進一家圖書館的地下室,在那里工作,持續閱讀,并且遇到了很快成為她的丈夫的那一個男人。
羅伯特需要的是法文書籍,索涅奇卡帶他來到自己熟悉的書庫地下室,地下室里的寶藏讓羅伯特心花怒放,索涅奇卡也對自己引發的這一番驚喜感到震撼。
心靈的某種因為書籍而產生的交會,使得四十七歲的羅伯特充滿激情地向年輕的索涅奇卡求婚,結婚禮物是一幅索涅奇卡的肖像,遠較本人的外形美麗,是羅伯特意念中的索涅奇卡。于是,我們知道這是一位現代派畫家,他有過復雜的西方經歷,最終從法國返回俄國,他的畫作從未被世俗世界理解、贊譽。他是一個追求自由的人,可以背叛任何妨礙其自由的信仰、傳統、人情道理。當然,他也從未容忍女人變成一種束縛,雖然他不斷地從女人那里獲取靈感。然而,此時此刻,他準備“套上枷鎖”,準備結婚了。我們也知道,索涅奇卡的心靈卻是被厚重的書頁層層禁錮住的,這種禁錮是美麗的,如詩,“在希臘神話的漫漫煙塵和波濤海浪之中起伏,在中世紀文學尖銳又催眠的笛音里迷茫,在易卜生起霧多風的憂愁中徘徊,在巴爾扎克無聊乏味的細節描寫里感動,在里爾克和諾瓦利斯如海妖之歌的尖銳動詞里擺蕩,在偉大的俄羅斯作家的道德訓誡和通向絕望之中受到誘惑”,索涅奇卡不可能意識到她正面臨著人生重大的關頭,她很幸福地在兩個星期之后成為羅伯特的妻子。
羅伯特從一位猶太教徒到科學家到藝術家的過往還伴隨著勞改與流放,流放的生涯并沒有因婚姻而結束,于是懷著身孕的索涅奇卡同丈夫一起來到流放地烏法。貧窮、寒冷、焦慮都抵擋不住索涅奇卡的幸福之感,因為丈夫的博學、因為丈夫的才華橫溢,“索涅奇卡的信任從無止境。丈夫的天分一朝被她當作信仰來看,她終生都以虔誠的贊賞對待一切出自他手上的東西”。我們不能不說,無止境的深層閱讀在如此這般的現實生活中展現了無與倫比的力量,使得索涅奇卡能夠在她并不理解的丈夫和一點人文素養也無的女兒之間辛苦持家卻仍然過著她“幸福”的日子,且歡喜贊嘆。
這時生活中出現了一個可人兒,女兒的善解人意的閨蜜,丈夫靈感的泉源、丈夫的情人。這個可人兒的母親被流放,她在十二歲的年紀就懂得用自己稚嫩的身體去換取保護,她是一個心機深沉的美人兒,楚楚動人。她與羅伯特的關系水到渠成再“自然”不過了。索涅奇卡是在丈夫的工作室從丈夫的畫作里看出了這種關系。她默默地走回家,感覺著內心的空蕩蕩、輕飄飄,然后從書架上隨手抽出一本書,坐下來,打開書本的中間頁,正是普希金的《鄉村姑娘》,埋頭讀了起來,“這幾頁內容里完美的遣詞用字和高尚氣度的體現,照亮了索涅奇卡,帶給她平靜的幸福感受”。烏利茨卡婭這樣告訴我們。啊,普希金!他同時照亮了我們,我們靜默無語,內心充滿酸澀的幸福之情。
丈夫腦溢血發作死在情人懷中。情人終至遠離,女兒終至遠離。丈夫五十二幅遺作使他在藝術史上留下了名字,他早期在巴黎的十一幅畫作更是收藏家們垂涎的獵物……
這一切都與索涅奇卡無涉,她在獨居的公寓里還有漫長的人生。她會到墓園去,在丈夫墳上種些不服水土的白色花朵。夜間,她會戴上眼鏡,“然后隨著腦海思路走入甜美的書本世界的深處,走進幽暗的林蔭道中,走入漫漫的春水里”。小說依然如詩,余音裊裊。
二
正是明麗的春天,法國南部普羅旺斯鳥語花香。穿過一片又一片火紅的郁金香田,來到洛瑪冉(Lourmarin),街巷靜好,餐館眾多,絕對是寫作人隱身的好地方。我坐在一塊古羅馬時期留下來的大石上,這種帶著歷史香氛的石頭稀稀落落散布在主要街道的人行道旁,供行人閑坐。手里捧著一本書,是卡繆1946年的作品《瘟疫》,作者1960年車禍去世,葬在此地。
這本書記錄了一場瘟疫的始末,充滿看似荒謬實則極富人性的書寫,切實地告訴我們,當我們面對永無止境的失敗——比方說一場恐怖瘟疫的時候——我們能夠學習到什么。endprint
與法國南部隔海相望,阿爾及利亞北部小城俄蘭,一個位于高地上的丑陋小城,擁有二十萬人口。一場猝不及防的鼠疫瘋狂來襲,使得小城中人的生活步調、生活方式、思考模式都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卡氏毫不留情,巨細靡遺一一道出。
當老鼠成批死去,在樓道里走路,腳下會踩到軟綿綿的鼠尸的當兒,李爾醫生送走了病弱的妻子,迎來了自己的母親。媳婦身體不好進療養院休養,母親前來照顧工作忙碌的兒子,完全順理成章,天經地義。但是當我們將整本書讀完,我們才能了解,在這毫不起眼的一送一迎之間,李爾醫生的生命軌跡發生了怎樣驚人的變化。
四月下旬的一天,新聞社報道該城在這一天共收集到八千只死老鼠的時候,人們只是覺得“稍有不安”,責成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李爾老太太反而處之泰然,“這就像那些時候一樣”,她語意含糊地說。這位睿智的老人家這樣對她的兒子表達她的心情:“我真高興能夠跟你在一起。無論如何,連老鼠也改變不了這一點。”醫生沒有完全聽懂母親的話。事實上,這位初來乍到的老人家已經想到了歐洲歷史上的黑死病——鼠疫。在災難來臨之時,她義無反顧,站在兒子身邊,盡自己的力量支持兒子,因為她唯一的兒子必定要站在抵御災病的最前線,因為他是醫生。換句話說,在擁有二十萬人口的俄蘭城,在三分之一到半數人口將要在年內死滅的關鍵時刻,只有這位老人家意識到即將來臨的浩劫。
李爾醫生相信的是科學,當看門人死在他面前的時候,他面對了這一年第一個病例,是否鼠疫則需要實驗報告來證實。但是,政府負責醫藥衛生的部門卻不太愿意積極去正視災情,不愿意“打亂”這個城市的穩定。然而,死亡本身是會帶來驚恐的。一位比較富有的外來者塔霍住在旅館里,他似乎很喜歡這里的海灘,喜歡游泳,也喜歡此地的西班牙舞者和樂手。他有寫日記的習慣,因此,俄蘭城面對災變所發生的事情便在一本日記本里留下了紀錄。而且,從他的日記里,我們看到了李爾醫生的行止。他從更多的死亡病例中看到了災病的共性。然而,人們是這樣難被說服,他們相信,某種惡病是偶然發生的,它們一定會被克服,一定會消失,日子也一定會循著正常的軌道按部就班地過下去。
于是,當“鼠疫”已經被確定,而政府高層仍然抱著僥幸心理無所事事“等著瞧”的時候,李爾醫生站出來指出這種政策絕對不智,當務之急便是要阻止細菌在數月之內消滅全城一半人口。
不幸而言中,鼠疫狡猾而瘋狂地進襲席卷全城。城市封鎖,不得進出,抵御鼠疫的血清明顯供應不足。年事已高的卡斯特醫生正是世間為數極少的真正的救人者,他洞悉一切,絕不盲目樂觀,他更不相信那些平庸的官僚,于是穩扎穩打,積極投身試驗、制造血清的工作。甚至,連李爾醫生都感覺無助、感覺恐懼的時候,卡斯特醫生毫不動搖,繼續自制抗疫血清。卡繆在這位智者身上著墨不多,但我們卻從他的言行看到當我們面對強敵、面對永無止境的失敗之時,我們應當具有的智慧、勇氣、信心,以及永不歇止的持續奮斗。
死亡人數每周從三百多直線上升,俄蘭市民從被封鎖,不得與外地的親友走動聯絡中感覺到孤獨、失落與不平,但他們仍然撐持著,希望能夠保持基本的生活方式。終至在大規模死亡來臨時,頹然承認瘟疫“殺死了一切色彩,否決了一切快樂”,而徹底地安靜了下來,接受了命運的殘酷宰割,城市陷入了死寂。塔霍的日記寫道:“瘟疫的第九十四天,死亡一百二十四位。”
李爾醫生忙得腳不點地,筋疲力盡。塔霍站出來組織救援隊,按照醫生的指示為患者家屬接種,做必要的各種預防與隔離工作。不僅是年事已高的公務員參加了救援隊,連一心一意準備逃出城去的記者,都戰勝了“我不屬于這里,我被陷在這里真是委屈”的心理而勇敢地加入救援隊伍。也就是說,更多的人都明白了一個真理,抵抗災病不再是某些人的事情,而是大家的事情,一定要團結起來,共同努力,而且不計個人安危。
終于,李爾醫生發現,他已經不像是醫生,不是在救治病人,而是在做一個宣判者,被病人家屬召喚到病榻前,診斷其親人確是罹患鼠疫,確實死亡,寫下紀錄,召喚運尸車,將其家屬送往隔離營地……因為死亡人數激增,死者已經不再有保持尊嚴的告別儀式,不再被換上壽衣妥善埋葬,而是被運尸車運往一個大坑,灑上石灰,層層堆棧,草草掩埋……
大家都累了,這種逐漸襲來的疲勞與絕望不但增強了一種漠然的情緒,而且使得需要支付大量勞力的事情變得更加的不可行。在這樣決然看不到希望的苦境中,塔霍的自省逐日加深,他認為,積極抗疫的行動是贏取和平唯一的方法。在贏取和平的過程中,我們必須持有同情之道。塔霍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當來年元月底鼠疫開始退卻的時候,他這位曾經大量接觸病人的英勇戰斗者卻被擊中了。李爾同母親守護著他,直到他死去。
卡繆是非常徹底的唯物論者,他告訴我們,鼠疫桿菌絕不會就此消失,它們將潛伏下來,伺機而動。而我們,當從他的書寫里學習到應對之道。
三
這不是珍·奧斯汀溫婉、浪漫的愛情小說,《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是一部緊密貼近今日世界嚴酷現實、引發我們思考的文學作品。作者是1971年出生于巴基斯坦第二大城拉合爾的莫欣·哈密。他在拉合爾長大成人,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受教育,在哈佛法學院拿到博士學位,在曼哈頓著名的財經公司工作多年,曾經成為“紐約客”,目前定居倫敦。
這樣的一位作者,可以說是“新移民”中的佼佼者,他得到了令無數青年艷羨的教育,他得到了令無數人艷羨的工作。但是,他離開了,他用一部小說來說明這樣一個“離開”本身所隱含的萬千曲折。小說就是小說,再富于自傳性質的小說還是小說,并非自傳。小說主角“成吉思”沒有遷居倫敦而是回到了家鄉拉合爾,在一家茶館里向一位陌生的美國來客細述他的心路歷程。于是,整本小說便成為“我”——“成吉思”的獨白,深入剖析了這位巴基斯坦青年同美國之間或即或離的關系,以及存在于雙方的偏見與傲慢。
成吉思的家族在拉合爾曾經是顯赫的,到了他的父親這一輩家道中落已經沒有錢來負擔孩子的高等教育了。但是,成吉思是成績優異的好學生,不但拿到美國名校的入學許可,得到獎學金,而且瞞著人在校內打三份工。在他的心目中,美國并非他的尋夢之所,他來到這里,為的是贏回“本來屬于他的東西”,骨子里的居高臨下,使得他在某些時候將曼哈頓公司里“花錢如流水”的同事視為“暴發戶”。才智相當的“破落戶”與“暴發戶”之間自然產生情緒上的隔閡,處境優渥的年輕同事們卻并沒有覺察到任何的異樣,只不過很喜歡“他這個外國人”而已。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