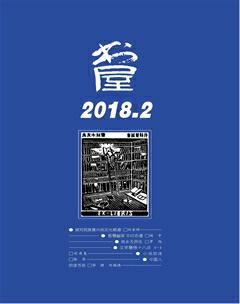“走出鄉土”:尚未完成的對話
張龍
“我家想養幾只羊,但買不起,我姨家有羊,就把一只老母羊借給我們養著,下了小羊羔,再把老羊還給她家,我們留下小羊。”這不是某個小說的開頭,而是旅美社會學者陳心想對兒時生活的回憶,這種“借羊”的經歷,在“留洋”的中青學者中大概并不多見。或許也正是這種從農村走向城市又最終走出國門的人生經歷,讓陳心想對中西、城鄉間的比較尤其敏感,并最終促使他寫出《走出鄉土:對話費孝通〈鄉土中國〉》這本書。方才所引的“借羊”情節,就是書中討論“人情與貨幣”時舉的一個例子。
陳心想的著作名為“走出鄉土”,與他要對話的“鄉土中國”恰好形成呼應。在看到“走出鄉土”的書名時,讀者可能會好奇:誰走出鄉土?走出什么鄉土?走出鄉土是一個將要到來的趨勢、正在進行的過程還是已經完成的事實?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需要首先了解費孝通的“鄉土中國”是什么意思。
費孝通先生的經典著作《鄉土中國》出版于1948年,至今已經歷時近七十載。凡是讀過《鄉土中國》的,想必對這本書的第一句話印象深刻:“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說完這句話后,費孝通緊接著做了解釋:“我說中國社會的基層是鄉土性的,那是因為我考慮到從這基層上曾長出一層比較上和鄉土基層不完全相同的社會,而且在近百年來更在東、西方接觸邊緣上發生了一種很特殊的社會。”從這句話可以看出“中國社會”的不同層次。《鄉土中國》成書于上世紀四十年代,因此費孝通所說的“近百年”正是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被迫打開國門、接受西方影響的百年,在“東、西方接觸邊緣上”形成的社會形態前所未見。而在受西方影響之前的社會中,從“基層上長出”的一層又不同于基層的鄉土社會。這里面由此可以看到縱橫兩個維度:從縱向的時間維度上,中國社會因和西方的接觸與比較而有了“傳統”和“現代”之分,而從橫向的空間維度上,中國內部則有城市與鄉村之別。
但是,費孝通的野心似乎沒有停留于講述一門“鄉村社會學”(《鄉土中國》最初乃是這門課程的講義),而是在更大尺度上進行著中、西文明的比較。《鄉土中國》英譯者、美國著名學者漢密爾頓(Gary Hamilton)曾說:“鄉土中國乃是整個中國社會的隱喻(metaphor)。”他進一步認為,該書最核心的理論貢獻不是對中國內部城鄉關系的分析,而在于中、西文明之間的整體比較,或者說是“中國傳統”與“西方現代性”之間的比較。換言之,在費孝通的比較方法中,從中國鄉村中發展出來的分析構成了中國傳統社會的“理想型”(ideal type),受西方影響較大的城市(如上海)則近乎對這種理想型的偏離。正因為比較的重心在于中、西之間,所以,費孝通在書中其實并不吝于使用中國城市的例子。比如,在書中講到“公”與“私”的問題時,他舉的就是蘇州城的例子。陳心想在《走出鄉土》中指出,費孝通有些地方似乎在拿中國的鄉村和西方的城市比,在方法上可能存在問題,他的質疑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將中國鄉村視為傳統中國的典型形態,而將其與代表現代性的西方都市進行比較,似乎也無可厚非。
因為費孝通所講的“鄉土中國”有更多“傳統中國”的意思,而“鄉土性”更多時候與“西方現代性”形成對照,所以,當陳心想與之進行對話并說“走出鄉土”時,他絕非僅僅在陳述“個體離開鄉村”這種意義上的事實。從宏觀而言,“走出鄉土”更近似于中國社會從傳統到現代的變遷。而從微觀個體來說,這一過程則近乎從所謂“傳統人”到“現代人”的轉變。誠如陳心想在“后記”中概括的:“‘走出鄉土的豈止是村民們——‘農民工們,那是整個中國在走出鄉土,向現代化轉型。”
當陳心想談論“走出鄉土”時,問題的起點都從費孝通的分析開始。盡管兩本書的寫作相距近七十年,但是費孝通建立在中、西社會比較之上的概括大都依然有效。最重要的例子,大概就是《鄉土中國》中所說的“差序格局”了。這一概念與“團體格局”形成對照,指的是中國社會那種以個體為中心、向外層層擴散、邊界具有彈性的結構。而“團體格局”中的個體之間具有相對的平等性,并且團體邊界也更為清晰確定。“差序格局”的概念,現在看也是抓住了中國社會結構的要害,且助于我們理解許多“中國特色”的現象。
比如,陳心想在《走出鄉土》中提到,在中國的人際關系尤其是親戚關系中,向來不缺“見風使舵”的“勢利眼”這號人。如果按照費孝通的分析,這或許不應歸于“世風日下”或“道德敗壞”,而更像一種“社會結構性”產物:“在鄉下,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錢的地主和官僚階層,可以大到像個小國。中國人也特別對世態炎涼有感觸,正因為這富于伸縮的社會圈子會因中心勢力的變化而大小。”換言之,親戚關系中“勢利眼”的盛行或許可以歸因于中國社會關系的伸縮性特征,即是否稱得上“親戚”是依情況而定的。一旦得勢,八竿子打不著的都會攀關系,乃至于“雞犬升天”;而一旦失勢,則馬上樹倒猢猻散,唯恐避之不及。但在一個更加講究個體權利與彼此界線的社會,人和人之間的關系可能就不會如此模糊不定。陳心想針對這一現象評價:“這種勢利眼在西方社會難道就不存在?不是。但在鄉土社會里,因為利益是隨著親疏厚薄關系網分布的,所以更為明顯。”
生活在同一情境下的人,容易將周遭的很多事情當作“理所當然”并將其忽略,但對不同情境的比較卻可以照亮不易察覺的事實。與費孝通類似,中、西不同社會的經歷給了陳心想作比較的基礎,而比費孝通(更準確地說,是發表《鄉土中國》時的費孝通)更有“優勢”的,則是后者寫作時經歷了又一場新的社會劇變,可以將“改革開放”后的鄉村社會與七十年前做一比較。如果說“差序格局”所概括的屬于鄉土中國中具有延續性的部分,那么,發生變化的那一部分同樣不難發現。
比如,在費孝通寫作的年代,家族與長老的權威尚在,“父子軸”還是牢牢占據著重于“夫妻軸”的重要位置。但是,到了陳心想的筆下,夫妻軸的重要性開始逐漸壓倒父子軸,孩子結婚就分家幾乎成了常態,家庭規模越來越小,老年人淪為新的弱勢群體。除此之外,從鄉村精英的變遷,到基層治理的演進,再到道德觀念的更新,一起構成鄉村變化的立體圖景,這也是陳心想在書中試圖呈現的內容。endprint
陳心想在《走出鄉土》后記中說,這是一次“缺席的對話”。這種對話只能是針對文本,并且主要還是單向的。而在這次“缺席的對話”中,我認為最大的亮點有兩個:一是作者本人的生活經歷,二是作者針對費孝通的觀點提出的自己的思考。
作者本人的生活經歷是相對獨特的。就像我開頭所說的那樣,既“借過羊”又“留過洋”的研究者能有多少呢?而在寫作中,他不時地舉出自己生活中的例子,讓他的敘述更為生動。比如,在談到鄉村精英時,他講到村中負責婚喪儀式與糾紛調解的“頭人”;而講到地緣觀念時,他則舉出自己在美國加油站的遭遇,說明美國人也認可“老鄉”。
論辯是“對話”的應有之義。在書中,陳心想提出了一些不同于費孝通的意見,從而展現出了一種寶貴的批判精神。比如,在第十章討論“無為政治”時,陳心想就直言費孝通關于傳統中國“無為政治”(即“皇權不下縣”)的說法“更像一種理想的無為狀態,正如詩人筆下美麗的田園生活,只在藝術家的想象和作品里吧”。而他質疑“無為政治”的理由有四:一,紳士只能保護自家和親戚,不在“紳權保護圈”的百姓大有人在;二,紳權在基層治理上是代理皇權的,紳士代替政府要錢要人;三,按照費孝通的定義,“皇權”范圍輻射至普通官僚,不以皇帝本人“無為”與否而改變;四,進貢體系在持續不斷地從百姓那里汲取財富,年復一年對基層“有為”。類似的討論還有很多,在此不一一舉例。
但是,如果說這本書有什么不足,我覺得這不足和優勢恰好是一枚硬幣的兩面。陳心想在“前言”中說到寫作此書的目的:“這是一本札記,重要的不是解讀《鄉土中國》,而是在于理解現實變遷中的中國社會,尤其是鄉村的變遷。”換言之,這種對話原本只是方法,最后的目的則是認識中國社會的變遷。然而,綜觀全書,我認為《走出鄉土》在觀點上的對話似乎遠遠超出對現實社會的關照。或者說,作者在理論層面上的發散與思考很多時候壓倒了對于經驗現實的把握。盡管陳心想曾經有著長期的農村生活經歷,并且做過至少兩項完整的農村研究(書中提到的“土地調整”與“計劃生育”研究),但是,他對書中涉及的一些社會現象還是有點“印象式”風格,缺乏深入系統的經驗研究。比如,對于“信訪”的評價,我認為就是太過于簡化與草率。他只提到信訪制度的“有效”,并未提到信訪導致的治理成本劇增、法治理念受阻甚至政權合法性受損等同樣嚴重的負面效應。這種對相關爭論的直接忽略,容易給缺乏背景知識的讀者帶來一些誤導,仿佛書中所談已是各界共識。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