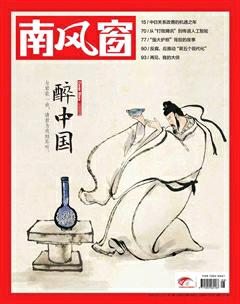你的錢收回來沒有?
韋星
借錢是現實而永恒的話題,上世紀80、90年代的農村社會,借錢幾乎是每個家庭的生活常態,看病要借錢,讀書要借錢,人情往來要借錢,甚至家里碾米也得借錢。
在我印象中,農村社會的很多家庭—包括我家在內,都是在鄰里和親友的幫忙下渡過難關的。我幾乎只字不落就能背出的,就有兩件事:
一是母親因為要給我們繳學費而和她堂弟借錢時,她堂弟沒錢,但在屋里,他指著腳下的木地板說:“你讓我姐夫來把它賣了。”
他住“干欄樓”—就是上面住人,下面住牛,中間用木板隔著的房屋結構。意思是,讓我父親把他家的牛牽到集市賣,換錢后給我們讀書。
81歲的父親對很多往事早已淡忘,但這個經歷,他還在念叨。因為他牽著牛去賣時,母親的堂弟沒跟著去賣,“說多少錢就多少錢。”
另一件事也和堂哥有關,那是我堂哥。上學前,我們家幾兄弟都需要籌集學費,籌不到錢的母親只好把眼光轉向豬圈,豬圈有頭還沒來得及長成但我們就要開學的百來斤小豬。
那天父親外出,我們都還很小,母親把我堂哥喊來。接著,從殺豬、退毛、解剖,再花一個小時挑到集市去賣,這些工序,都是堂哥一人完成。
那天很晚堂哥才從集市回來,把1塊、2塊、5毛的一大堆零錢拿到我家。我清楚記得,在搖曳煤油燈光下,堂哥點著一張張的零鈔。完了,他把錢和數都交給我母親。堂哥一個人回家,手里空蕩蕩的。
那個曾很拮據的年代正在遠去。如今,母親在城里幫我看小孩,由于她不會講普通話,交際圈很小,我又經常出差。所以每次我出差回來,飯桌上,她有累積很久的話要說,很多是她念叨“誰誰曾對我們好”的話。
受這種氛圍影響,一旦有鄉親遇到困難求助,我總是力所能及地幫助,比如借錢。但我發現,借錢的結果常讓我為難,因為我真心想幫助的一些對象,到后來總不準時還錢,讓我“催也不是,不摧也不是。”結果是,借了錢,給自己添堵。
當不少外債很難追回時,我對別人借錢產生恐懼。以致于,有次,一個好朋友向我借錢時,我拒絕了,理由是“沒錢”。事實上,那時我有,但我被之前借的人給拖欠怕了。
但因這次沒給好友借錢,這么多年來,我一直對自己的這種行為耿耿于懷,總感覺對不起和虧欠這位朋友。
表面看,因為拒絕幫忙,我辜負了這位朋友對我的信任,讓我感覺“欠了朋友”,但根源在早前我相信的其他人接二連三傷害了我的善良,破壞了我對他們的信任,進而“誤傷”到真正需要幫助的朋友,或是造成大家都受傷的結局。
我相信不少人也有我一樣的經歷,但所有的傷害都源于我們的信任和善良,因為我們曾善良地相信他們會兌現承諾,即便因種種原因沒得及兌現,他們也會愧疚地給我們解釋,但始終沒有,年年沒有。
可我們從小生活在比較困難的環境中,我們也曾多次借過別人的錢,也曾得到別人的幫助,我們都是在鄉親的溫暖中走過困難時光。
只是那時,我們父母兌現了承諾,如果預計到期沒能兌現,我們父母做法通常是:借別人的錢來還之前承諾到期所要歸還的對象的錢。不斷拆借中,一環扣著一環,共同度過艱難但有溫情不斷支撐著的歲月。
我們都懷念那種充滿溫情的歲月,也感恩所有幫助過我們的人,所以即便在力所不能及的時候,我們甚至會通過借朋友的錢來借給需要幫助的困難親友—事實上,我們可能還欠銀行一大筆債,但我們仍像在自我救贖一般,努力給別人提供幫助。
但最后我們發現,我們最終只能感動自己,無法感動被救助者。到了今天,有時候我們常常困惑和迷茫,因為我們似乎找不到一種力量和理由,讓我們相信自身努力和堅持幫助別人的必要,因為時代已經變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