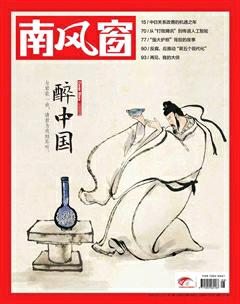“強大護照”背后的故事
雷墨
春節出國(境)旅游,已經成為許多中國人的生活方式。隨著阿聯酋、摩洛哥、塞爾維亞、波黑、巴哈馬等國對華免簽,以及卡塔爾、文萊、印尼、埃及、伊朗、尼泊爾、斯里蘭卡、緬甸、泰國、越南、柬埔寨、烏克蘭等更多國家對華落地簽,中國護照的“含金量”越來越高,也是不爭的事實。
護照作為權力機關向公民或國民頒發的身份證明,在功能演變中逐漸變成國家間關系的一個表征。但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來看,護照“含金量”與國家實力之間都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其背后的故事多維且復雜。
護照實力
在國際上評價和研究護照的文獻中,有“護照實力”(passport power)一說,主要指一國頒發的護照所對應的免簽(含落地簽)國家數量的多寡,即所謂的護照“含金量”。
英國亨氏顧問公司(Henley & Partners)基于國際航空運輸協會的數據,自2005年以來,每年都發布世界約200個國家和地區所頒發護照免簽數量的排行榜,成為國際社會評價某種護照“含金量”的一項關鍵指標。
根據亨氏顧問公司2018年發布的數據,德國護照以能免簽進入177個國家和地區高居榜首。位于第二梯隊的是新加坡和瑞士(176個),新加坡也是連續兩年世界排位最靠前的亞洲國家(此前一直是日本)。第三梯隊的國家有丹麥、芬蘭、法國、挪威、瑞典、意大利、英國、日本,均為175個。美國與奧地利、比利時、盧森堡、荷蘭、西班牙一道排名第四(174個)。

世界排名墊底的是索馬里、巴基斯坦、敘利亞、伊拉克和阿富汗。
加拿大咨詢公司阿爾頓資本(Arton Capital)也有一個較知名的“護照實力”排行。由于數據依據和來源的差異,該公司的榜單在免簽數量上與亨氏顧問公司略有不同,但反映的“護照實力”排行并無太大差別。
根據其2018年的數據,排在首位的依然是德國(161個),第二梯隊的是新加坡、丹麥、瑞典、芬蘭、意大利、法國、西班牙、韓國(160個)。美國仍處于第四梯隊(158個)。排名末位的國家,與亨氏顧問公司的結果一致。
亨氏顧問公司的數據顯示,中國“護照實力”(僅限中國大陸,下同)的排名,2018年排在第75位(60個)。根據阿爾頓資本的數據,2018年中國的排名是第65位(64個)。
根據中國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的數據,截至2018年1月,與中國簽訂全面互免簽證協議的國家有11個。此外,還有15個國家和地區單方面對中國公民免簽入境,41個國家和地區單方面允許中國公民落地簽入境。這三類加起來是67個,與上述兩家公司的數據接近。
中國“護照實力”近年來有了明顯提升。比如在亨氏排行榜中,2016年中國排名是第87位(50個),兩年后躍升到第75位。但總的來說,目前中國“護照實力”依然在世界上處于中等偏下的位置。在亨氏顧問公司總共104個排名對象中,中國位列第75位。阿爾頓資本總共94個排名對象中,中國排在第65位。中國不僅落后于世界主要大國,在金磚國家中也僅高于印度(亨氏排行榜第86位;阿爾頓排行榜第72位)。
從這些年“護照實力”排行來看,盡管具體國家和地區排名略有變化,但總體來說保持了高度的穩定性。比如,排名靠前的絕大多數總是歐美發達國家,而且能進入護照“高含金量”行列的國家,絕對數量一直不多。此外,護照免簽數在國家間的分布,呈現明顯不均衡性。根據亨氏顧問公司2018年的數據,所統計的201個國家和地區,平均免簽數量是97個,有104個國家和地區在這個平均數以下。
力量之源
現代意義上的護照誕生于歐洲,更具體說是法國。美國學者約翰·托爾佩寫過一本名為《護照的發明》的書。根據他的研究,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首次喊出了個人遷徙自由的口號,但隨著革命演變成內戰和對外戰爭,防止敵對勢力破壞的需求取代了遷徙自由。出于管控人口流動的需要,法國當局簽發了針對個人旅行的官方證明;直到19世紀中后期,英國等主要歐洲國家簽發的護照都以法語書寫。
19世紀末,西方國家相繼進入工業革命高潮期,“機器吃人”導致了普遍的就業危機。這些國家的勞工團體紛紛向政府施壓,控制外來人口的流入。法國和德國率先利用護照制度,加強對人口遷徙、拘留與務工的管控。一戰在歐洲范圍內制造的國家安全危機,進一步強化了護照制度控制人口流動的功能。
由此可見,護照雖然是一種個人的身份證明,但從一開始就被賦予了國家控制個人流動的功能。
1920年10月,來自22個國家的代表在巴黎召開了一次關于護照制度的國際會議。這次會議的初衷,本來是為了逆轉一戰造成的國家間限制人口流動的趨勢,促進個人遷徙自由。但最終達成的結果是,承認國家對安全與就業的合理擔憂,繼續對人口流動實施控制。
這次會議事實上成了護照制度國際化、標準化的分水嶺。如今護照上所包含的個人姓名、出生地點、簽發地等信息,甚至內頁32頁的規定,都是在那次會議上做出的。
由此可見,護照的誕生及其功能的賦予,都是一種國家行為,而且以西方中心為特征。西方國家在護照以及隨后的簽證體系發展中,所扮演的游戲規則制定者角色一直延續至今。歐洲的“申根簽證”,已成為護照制度發展的“黃金標桿”。被申根成員國承認免簽,也是衡量一國“護照實力”的重要指標。以此來看,“護照實力”強大的國家幾乎都是歐美發達國家,制度根源是不容忽視的因素。
總的來說,相對富裕的國家,護照的免簽國較多。這與全球化的深入不無關系。全球化促進了商品、投資、技術等的自由流動,但在很多情況下,只有伴隨著人的流動,才能產生更大的經濟效益。這就是為何很多欠發達國家,愿意向經濟、技術實力強的西方國家單方面免簽的重要原因。土耳其的最大貿易伙伴對象是歐盟,安卡拉向來對歐盟不對其護照免簽不滿,但自己依然向所有歐盟成員國的護照免簽。endprint
“護照實力”排行的另一個事實是,其與國家實力并非正相關關系,有的情況下還是負相關關系。換句話說,有些國家“護照實力”強,不是因為其國家實力強,恰恰是因為國家實力弱。東南歐小國摩爾多瓦,人口不到400萬,人均GDP不到2000美元,但其護照免簽國(110個)卻與俄羅斯(113個)相當。這種小國、弱國具有較強“護照實力”的現象,在上述排行中相當普遍。
某種程度上說,這反映了國際護照免簽格局中,強勢國家對絕對優勢的“合理”利用。比如,德國以對等原則與摩爾多瓦互免簽證后,德國護照持有者能便利地免簽進入摩爾多瓦。但這種便利,對普通摩爾多瓦人來說幾乎沒什么意義,因為有財力入境德國的“高凈值”人,數量少得可忽略不計。歐盟不對鄰近的土耳其免簽,但卻對諸多拉美小國和欠發達國家免簽,也是同樣的道理。
所以從現實情況看,“護照實力”并不絕對以國家實力為后盾。2017年世界GDP排行中,中國和印度分別位居第二與第六位,但這兩個國家的“護照實力”卻都在世界平均水平以下。根據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教授亞當·路德特克的研究,人口超級大國在這一點上帶有天然弱勢。“以潛在的人口流動來看,人口眾多的國家可能造成‘人口潮汐擔憂,從而導致人口相對較少的國家不愿意對其護照免簽。”
源于差異
“中國公民,當你在海外遭遇危險,不要放棄,請你記住,在你身后有一個強大的祖國。”電影《戰狼2》中展現的“中國護照”上印的這句話,很多人都明白那是劇情的需要,并非現實存在。但“強大護照”與“強大國家”之間的直接因果關系,很可能仍是不少人堅信的理念。
托馬斯·弗里德曼說“世界是平的”,在護照免簽格局層面,這一說法只對少部分人成立。自護照制度誕生以來,西方人就享有更大的“行動自由”。有數據顯示,1840年至1914年,歐洲向世界其他地區“凈輸出”人口6000多萬。護照制度國際化、標準化后,這種更大的行動自由在制度上得到了強化。對于更多的非西方國家來說,躋身護照免簽頂端,面臨著諸多難以逾越的高墻。
這當然是一種不平等,但僅用不平等難以解釋護照免簽格局現狀,更“中性”地說,或許應該是“差異”的存在。
排在“護照實力”前20位的國家,幾乎都是經合組織成員國。這些國家相互間都互免簽證,但對非經合組織國家護照免簽較少或較為謹慎。這里的“差異”是經濟發展水平。

西歐、北美的西方國家都互免簽證,但對于非西方國家,簽證政策開放度有限。這里的“差異”是“文明”。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在護照問題上也有解釋力。
擁有巨大石油財富的海合會成員國對彼此互免簽證,它們的護照在絕大多數阿拉伯國家都享受免簽待遇,但卻不對后者免簽。這里的“差異”不再是文明。
某種程度上說,海合會成員國與其他阿拉伯國家間的護照免簽格局,是整個世界現狀的微縮版。這種現狀既反映了不平等,也體現了差異,而且差異的主要指向是財富。文明范疇上不屬于西方國家的新加坡,能攀升至護照免簽榜頂端,國民富裕程度是一個重要因素。
“差異”還有更微妙的體現:被列強殖民的歷史,會對“護照實力”有“加分”作用。根據亞當·路德特克的研究,曾是英國殖民地的國家,總體上護照免簽數量會增加10個。曾被西班牙殖民統治過的國家,數量會增加18個。從亨氏排行榜看,那些曾被同一宗主國殖民統治的國家,相互間護照免簽的比例,往往比對其他國家要高。這一點在拉美體現得尤為明顯。
著名奧地利猶太裔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曾在著作《昨日的世界:我的自傳》中寫道:此前人們只有身體和靈魂,如今還要有護照,如果沒有它,將不會被視為人類。
茨威格以自己坎坷顛簸的人生經歷,訴說了護照制度對普通人尤其是弱勢群體的禁錮。某種程度上說,護照是“地球人”對世界現實的感知器。通過它,你能感受到何為優越,何為弱勢,何為“我者”與“他者”的差異。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