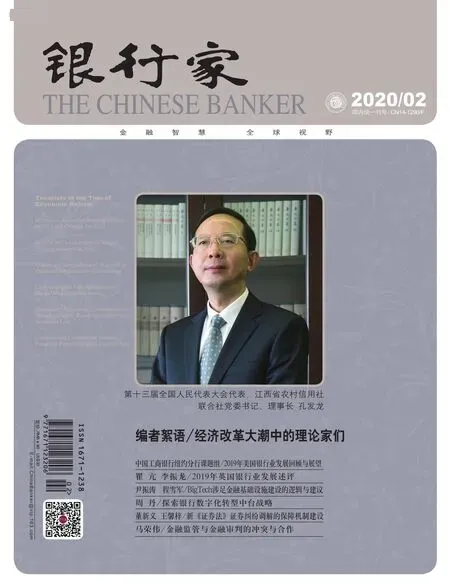改革之前我們為啥那么窮
2018-03-02 00:48:32
銀行家
2018年2期
關鍵詞:經濟
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的歷史節點,我們這些曾經親身經歷改革前20多年又目睹改革40年歷史變遷的一輩人,特別是理論工作者,尤其需要總結。我很想寫下一組系列文章,對改革開放40 年這前前后后的一些事兒說一說自己的感受。
有關改革開放的話題如果是深入思考并且是教科書式思考, 那么,我們碰到的第一個問題肯定是——改革之前我們為什么那么窮。
“我們”是誰?當然是指中國,改革之前的中國是一個實行了近30年計劃統制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曾用一窮二白形容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的中國經濟,經歷了28年浴血奮戰奪得政權的中國共產黨人也想在經濟建設上大顯身手,但是,曲折的探索經歷說明,中國經濟建設的發展道路既不是知易行難也不是知難行易, 而是知難行難,在理論認識上,我們曾長期在錯誤的方向上流連忘返;在發展實踐上,我們又付出了高額的學費或成長代價。
1978年是中國現代歷史上的改革元年,這一年,五一勞動節放了三天假,我應邀到長春市大姐家為大姐做家具。順便說一句,我是1968年全國第一屆知青,下鄉兩年,1970年從農村抽調回城,被分配到吉林省前郭縣木器廠,成為一名木匠學徒。通常是三年出徒。學徒工資第一年每月16元,第二年每月17元,第三年每月19元。我每月19元還沒掙到手就于1972年12月參軍去了海軍北海艦隊,1977年3月復員,半年后被分配到前郭縣木材公司,在政工組工作,每天干些寫標語寫材料之類的事兒。……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今日農業(2022年14期)2022-09-15 01:44:56
民生周刊(2020年13期)2020-07-04 02:49:22
商周刊(2019年18期)2019-10-12 08:51:16
商周刊(2019年18期)2019-10-12 08:51:10
中國外匯(2019年23期)2019-05-25 07:06:20
華人時刊(2018年23期)2018-03-21 06:26:00
西部大開發(2017年7期)2017-06-26 03:14:00
中國工程咨詢(2017年5期)2017-01-25 15:22:24
大社會(2016年6期)2016-05-04 03:42:05
金色年華(2016年13期)2016-02-28 01:4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