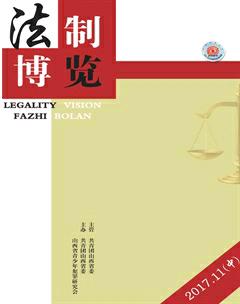法官說理改革路徑新探
摘 要:中國法官一直因“不說理”而受到質疑。對其原因進行梳理,可分為主觀上“不愿”說理與客觀上“不能”說理兩種,對這兩類原因都應當加以重視。據此檢驗學界提出的法官說理改革進路,可發現“美國模式”和“德國模式”都不能在我國有效推行,原因是法官解釋權受限以及法官威信不足。通過法律解釋方法法典化對“美國模式”加以改造,可以使其更好地適應國情,是推進法官說理改革的一個折中方案。
關鍵詞:說理;法律解釋方法;法典化
中圖分類號:D9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4379-(2017)32-0075-01
作者簡介:趙心荷,女,山東沂水人,本科,山東大學(威海),研究方向:刑法學。
一、為什么不說理?——“不愿”與“不能”
本著對實踐負責的態度,我們必須一視同仁地對待可能導致法官“不說理”的各種原因,由此設計一套可以兼顧各種可能性的應對策略。要完成這一任務,首先必須對當前法官“不說理”的原因進行體系化的整理。從目前學界提出的各種觀點來看,所有的原因大致可按主客觀的二元區分方法分為法官“不愿”說理和“不能”說理兩部分。“不愿”說理是法官基于對各種現實因素的考量對說理做出的“消極避讓”的負面評價進而導致不說理的狀況,“不能”說理則更多關涉法官的說理能力。這樣區分的意義在于,我們既可以從中發現能夠通過制度上的努力立竿見影地使之消弭的矛盾,又必須意識到實現法官說理裁判并不是一項一步到位的事業,不可能通過一次改革便一蹴而就。那么接下來的問題就在于,有哪些阻礙因素是我們可以通過改革立竿見影地加以解決的?有哪些需要長期的努力?當前學界提出的改革方案是否足以應對這種需求?
二、問題的闡明與方案的檢討
改革的當務之急是運用制度手段清理可能挫傷法官說理積極性的現實阻礙,以求用“當前的方法解決當前的問題”;同時又必須警惕“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危險,防止當前采取的措施為日后改革進程設置新的障礙。檢視當前學界提出的改革進路,凌斌教授將其分為兩類:“模仿德國模式”和“模仿美國模式”。中國受大陸法系的影響在制度設計上對法官的解釋權進行了嚴格限制,與此同時,不同于西方法官尤其是美國法官的高度權威,中國法官的權威則“微乎其微”,這導致了,一是法官囿于職權沒有能力過多修辭,二是修辭可能會成為當事人“質疑”的籌碼,給其帶來極大的職業風險。這兩點足以抑制法官進行法律修辭的積極性。
這隱含了對于法官素質的兩個要求:一是法官必須系統地掌握修辭方法;二是法官必須系統地掌握修辭方法的運用策略并能在司法實踐中靈活運用。毋庸置疑,這對于當前法官群體而言是個考驗,對于法學教育也是一個尚待探索的課題。這意味著法官開始追求法律所賦予的司法權的由“合法性”向“正當性”的轉變,也就是說我們正在尋求一種“修辭性的權力”。“呼喚一種‘修辭性的權力,是增強權力的說服性和可接受性而非暴力性和強制性,這其實是對權力赤裸裸暴力的約束。”在這種理念下,法院不僅僅給了老百姓“說法”,還額外“贈送”了為什么會有這種“說法”,這對于我國司法權威的建立以及法治的實現是具有極大的積極意義的。
三、一個折中的方案——法律解釋方法法典化
從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不論是“德國模式”還是“美國模式”,在中國難以推行的核心原因有二:一是法官威信不足;二是法官解釋權受限。這導致了諸如法官“為預防職業風險而不肯說理”“溝通比說理更重要”等其他一系列原因。那么,法律解釋方法法典化如何應對上述問題?要應對第一個問題,首先要搞明白法官威信來自何處。我國《法官法》第二、第三條分別規定:“法官是依法行使國家審判權的審判人員”;“法官必須忠實執行憲法和法律,全心全意未人民服務”。這表明法官是國家審判權的執行者,其權力的最終來源是國家權力,其威信最終來源于司法公信力。
其次,針對法官解釋權受限的問題,整個大陸法系國家都對法官的解釋權進行了嚴格的限制。將法律解釋方法法典化,可以妥當地解決上述問題。與此同時,法律解釋方法法典化將各種法律解釋方法的內容、適用條件、適用順序等變成了實定法上的規定,符合了司法制度對于“法官行使其法律解釋權的時候,這種權力的行使總是要受到各種法律淵源的限制,使法官在法律解釋中的各種活動具有合法性”的要求,又沒有超越法律對于法官解釋權的限制,消除了法官解釋法律的后顧之憂。
需要注意的是,法律解釋方法法典化能夠確保法官運用各種法律解釋方法對法律進行解釋從而進行說理(解釋的過程本身也就是說理的過程),但它并不是法官說理的全部,而只是說理的第一步或者說關鍵一步。對絕大多數需要說理的案件來說,最大的風險和困難即在于法律的解釋,解決了解釋上的難題即基本解決了說理的難題,但它仍然需要其他說理方法的配合以完成從解釋到適用的過程。所以它并不是一個一步到位的方案,更不是一個一勞永逸的方案,而僅僅是制度移植與中國實踐產生緊張關系時的一個折中的方案。
[ 參 考 文 獻 ]
[1]焦寶乾等.法律修辭學導論——司法視角的探討[M].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2012.
[2]魏勝強.法律解釋權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