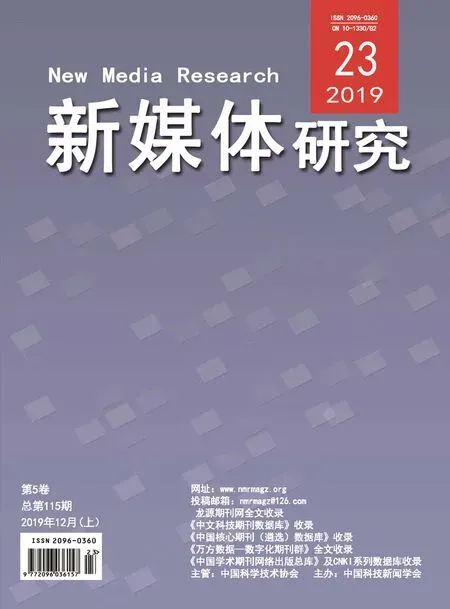從原型視角看“老人碰瓷”事件中的公共敘事
摘 要 原型制約著人們的認知與傳播活動。在近年來頻遭熱議的“老人碰瓷”事件中,“彭宇案”作為一個集體建構的“世俗神話”具有不可忽視的原型意義。受其制約,老人群體的形象往往在二元對立的敘事結構中呈現,并作為標出“異項”被不斷污名化。因此,有必要對此類話題傳播過程中的敘事邏輯進行分析,從而更為深入地解讀這一現象。
關鍵詞 原型敘事;二元結構;老人碰瓷
中圖分類號 G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6-0360(2018)23-0022-02
網絡新媒體的發展使其成為輿論傳播的重要平臺。回顧近年來的網絡公共事件,“老人碰瓷”話題是網民長期關注的熱點,每每此類事件進入公眾視野,便引起負面輿論沸反盈天。這一方面與話題本身的敏感性有關,同時也是因為事件講述者所用的敘述策略起到了原型激活的效果,從而釋放出強大的輿論召喚力。
1 “彭宇案”:激發輿論傳播的原型敘事
“原型”,或稱“原始模型”。在瑞士心理學家榮格看來,“與集體無意識的思想不可分割的原型概念指的是心理中明確的形式的存在”[1],其中凝聚著超個體的經驗與情感記憶,并且只有外化為儀式、敘事等具體形式才能為人們把握。加拿大文學批評家弗萊將原型界定為文學中可獨立交際的結構單位,“它或是一個人物、一個意向、一種敘事定勢,或是一種思想[2]。一種敘事原型通常與人們的深層心理相聯系,它的出現也勢必造成某種認知定勢與情感能量的喚醒。
從源頭上看,時下熱門的“老人碰瓷”話題可以追溯到“彭宇案”一事。此事發生后,一些媒體采用《做好事反被誣》《見義勇為反被告》等標題進行報道,在許多網民的言論中,此案更是被喻為現代版的“農夫與蛇”,當事人彭宇因此得到普遍同情。在這場眾多媒體帶頭、網民共同參與的集體敘事實踐中,“彭宇案”不僅被描述為一個道德越軌的奇觀事件,也作為一起“忘恩負義”的典型事件喚起人們的集體無意識,使其具有原型敘事的意義。
回顧那些耳熟能詳的古代寓言與歷史典故,類似“農夫與蛇”“東郭先生與狼”的故事屢見不鮮,這些真實或虛構的事件被賦予相似的深層敘事結構,故事參與者亦顯示出相近的角色特質,于是不同的敘事文本成為同一類原型模式的多種表現。而對“彭宇案”的報道、傳述也意味著古代故事在現代生活中的重新演繹,由于其講述的本質上是早已為人們熟知的事件,因此能夠迅速激發相應的道德情感,引發強烈的負面輿論。
隨著網民對“彭宇案”的長期傳播與反復評述,對于“老人碰瓷”這一現象的認知與道德情感也通過集體記憶的沉淀獲得近似“原型”的地位,成為網絡時代“一個扭曲的社會‘神話”[3]。縱觀近年來的“老人碰瓷”話題,盡管已事隔十余年,網民在講述、評價此類事件時,仍會頻頻提及“彭宇案”一事,并以相似的解釋框架理解、傳播各地或真或假的“老人碰瓷”事件,使之成為“彭宇案”的再度演繹。
2 二元對立敘事模式下的身份歸類
面對形形色色的“老人碰瓷”事件,即使真相未明,許多人仍習慣以“彭宇案”的敘事邏輯對其進行事實重構,二元對立的敘事結構則是慣用的敘事策略。在結構主義思想中,二元對立的概念占有重要地位,“其認為一個事物不屬于目類a就屬于目類b,人們便是以這樣的分類方式面對世界并且認知世界的”[4]。通過簡單的歸類方式,敘事者將復雜事實納入非黑即白的敘事框架,并將老人處理為“罪惡與無辜”這類二元關系中的反方。而要達到歸類效果,除了給老人貼上“碰瓷”標簽之外,敘事者還會通過對雙方言行的對比描寫、對事件的傾向性評價等方式完成老人身份的建構。
在關于“老人碰瓷”話題的傳播過程中,對于老人、“被碰瓷者”雙方言行進行對比描寫是常見的敘事策略。有媒體在報道“彭宇案”時寫道:“當得知是脛骨骨折要花費幾萬元換人造股骨頭時,徐老太太一拍大腿對彭宇說:‘小伙子,就是你撞的啊!”對于當事人彭宇的描寫則是“出于好心,他忙上前將其扶起”“當時就蒙了”。這類描寫也出現在“北京大媽碰瓷老外”事件中。最初披露事件的網民對大媽的描寫是“突然摔倒自稱被撞傷”“死命抱住對方”,[5]同時以“衣服被撕爛”“急哭了”描述外國小伙的無助。這類帶有強烈主觀傾向的對比描寫使老人的無賴形象與“被碰瓷”者的無助形象得到建構。諷刺的是,隨后出現的媒體報道與目擊者說法均證明,老外撞人并辱罵大媽才是事實的真相。
除了言行描寫之外,敘述者還通過進一步的事件評價來對涉事雙方的身份性質進行界定,這些評價通常是以直接引語或間接引語的形式出現。例如,在“大媽碰瓷玩具車”事件中,一些網媒轉載原視頻的同時也對前因后果不明的視頻內容作了文字概括,同時還對網民觀點進行了摘錄。但從內容上看,對視頻的概括援引的是網絡謠傳的說法,摘錄的網民觀點更是對老人一邊倒的嘲諷與批判。又如“中國老人日本碰瓷”事件中,網媒在報道時引用了所謂的醫院說法“根本沒受傷”,引用了當地警察的評價“這是威脅恐嚇。是犯罪”[6],唯獨缺失了老人的說法。通過引語的使用,老人被自然而然地定義為“碰瓷者”,另一方則被界定為“被碰瓷者”,雙方之間的對立關系也通過這類策略的使用得以強化。
3 “異項標出”與老人群體的污名化
根據文化符號學的理論,在二元對立的關系中,正項與異項之間總是存在不對稱的關系,中項則是兩者之間的第三項,其特點是“無法自我界定,必須靠非標出項來表達自身。不參與中項的成為異項,即標出項”[7]。中項偏向哪一邊,便意味著那一邊正常,另一方則被排斥,成為社會文化領域中邊緣化的對象。關于“老人碰瓷”事件的二元對立敘事促進了網民敘述與認知模式的類型化,這不僅強化了其原型意義,使“老人碰瓷”作為網絡時代一個“世俗神話”的地位愈漸鞏固,也使老人群體作為“異項”被不斷標出。
從本質上看,其實在這類事件中真正被作為異項標出的是碰瓷行為本身,中項認同社會主流道德,為網民批判行動的合理化提供支持。但是,在相關的敘述中,碰瓷行為成為老人群體的專屬,作為涉事一方的老人被迫與“碰瓷”綁定。對這種綁定關系的自然化主要通過以下幾個方面的措施實現。
一是對“老人碰瓷”事件的傾向性報道、夸張式描述乃至杜撰虛構。
二是對同類道德失范事件的不斷強調,例如近年來同樣熱門的“老人讓座”“廣場舞大媽”等話題。而對這類事件的敘述同樣是通過對老人的無理與另一方的無辜形象刻畫,在老人與年輕人、老人與小孩等二元對立結構中展開,這和關于“老人碰瓷”事件的敘述起到了互文效果。
三是對老人群體的身份進行重新詮釋。一些言論認為“不是老人變壞了,而是壞人變老了”,并將當下的老人與文革時期“打砸搶斗的年輕人”相等同,這類說法得到許多網民的轉發復述。通過上述手段,老人群體幾乎成為道德失范的代名詞,其與碰瓷行為的綁定也就順理成章,于是自然而然地作為“異項”標出,被污名化為社會文化領域中的另類。
4 結束語
“原型”反映了人們認知活動中的類型化思維,這種思維外化為對一類事物的程式化敘事,又反過來強化了原先的思維定式。在眾多“老人碰瓷”事件中,“彭宇案”作為一個深入人心的當代“原型”制約著人們對同類事件的傳播與認知,并使老人在二元對立的敘述模式中作為“異項”被不斷污名化。對此,在“彭宇案”已被澄清的今天,一方面我們應重新審視這一“原型”的合理性,避免認知視角受其遮蔽,另一方面,媒體在報道此類事件時,也應堅守職業規范,以更為審慎、客觀的方式引導網民進行理性解讀。
參考文獻
[1]榮格.集體無意識的概念[M]//葉舒憲.神話——原型批評.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100.
[2]李紅.網絡公共事件中的敘事原型[J].符號與傳媒,2014(1):123-135.
[3]苗艷.新媒體事件話語研究[M].四川:四川大學出版社,2015:238.
[4]曾慶香.西方某些媒體“3·14”報道的話語分析[J].國際新聞界,2008(5):25-31.
[5]“大媽訛老外”:一場集體盲人摸象[EB/OL].(2013-12-09).http://opinion.people.com.cn/GB/363551/372232/index.html.
[6]獨家:日方稱“中國老人在日碰瓷索賠10萬”屬實[EB/OL].(2015-10-05).http://news.ifeng.com/a/20151005/44784646_0.shtml.
[7]趙毅衡.文化符號學中的標出性問題簡介——代主持人的話[J].江蘇社會科學,2011(5):136-137.
作者簡介:鄭宏民,研究方向為文化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