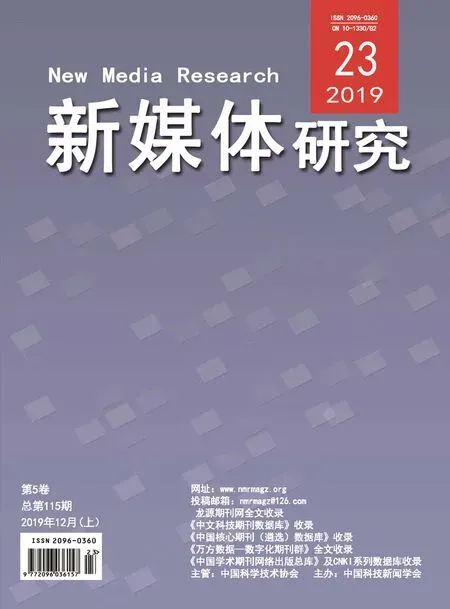維系與認同:藏族與漢族大學生微信朋友圈使用比較研究
摘 要 網絡信息化的迅猛發展為大學生提供了新的社會活動空間,通過考察藏、漢族大學生的微信朋友圈的使用動機與線上人際交往特點,發現藏族大學生在使用微信朋友圈時,自我呈現的遮蔽策略運用笨拙、關注實際利益、重視人際情感維護,呈維系式特點;漢族大學生在使用微信朋友圈時,能夠嫻熟的運用自我呈現的遮蔽策略、關注線上情感認同、重視他人認可,呈認同式特點。
關鍵詞 維系;認同;藏族大學生;微信朋友圈
中圖分類號 G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6-0360(2018)23-0042-02
1 問題的提出
從學界對高校少數民族大學生的研究上看,現階段關于少數民族大學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媒介素養、文化適應、身份認同、國家認同等問題上,研究學科主要涵蓋民族學、教育學、心理學、傳播學、社會學等,是個典型的交叉學科研究領域。對高校少數民族大學生的媒介使用方面的研究主要針對該群體的微博使用與互動、網絡行動與交往、新媒體使用與身份構建等問題展開,將該群體自帶的民族文化烙印與新媒介技術結合討論,對目前我國某些地區少數民族大學生的媒介接觸與使用做了一個宏觀描繪,但缺乏專門針對藏族大學生與漢族大學生的新媒介使用自我呈現的比較研究。新媒介技術的發展為每一個社會成員提供了新的自我呈現場域,各種新媒介也深深滲透到藏族大學生的日常生活與學習中,大學生游離于現實與虛擬共同交織的傳播網絡中,多元身份交叉重疊,虛實之間,藏族大學生如何利用新媒介,進行自我展演、維系并拓展人際關系、在大學環境中逐步完成自身的社會化?而要討論藏族大學生的新媒介使用情況,需以漢族大學生的新媒介使用情況作為參考,差異在對照中才會得以顯現。
2 藏、漢族大學生朋友圈使用的工具理性比較
歐文·戈夫曼的擬劇理論認為社會是一個舞臺,每個人都是在這個舞臺上表演不同角色的演員,他們都在互動中“表演”自己,塑造自己的形象并更好地達到自己的目的。在朋友圈這個線上舞臺,藏族大學生與漢族大學生在進行電子化自我展演時,他們的訴求是否存在差異?與傳統網絡社交模式不同,微信朋友圈為受眾提供的是一個“窄播深交”、強關系的互動平臺,由于軟件本身的不斷更新和功能的開發,對個人信息的私密性的保護增強,營造了一個互動、多向、半開放的、能給受眾更多主動性和安全感的展演空間。
本研究以江西省高校藏族大學生及漢族大學生為研究對象,以線上為觀測點,結合這兩個不同族群的文化背景及新媒介接觸使用習慣,以微信使用為例,秉承受眾研究的社會文化取向,探尋與對比藏、漢族大學生的新媒介實踐特點。基于此,本研究以江西某高校為例,采用問卷調查法,共計派發720份,藏、漢族大學生各360份,有效問卷回收率分別為99.2%與97.8%。問卷包括基本信息、微信朋友圈使用情況、微信朋友圈的互動情況三大部分。通過對兩類問卷的整理與對比,研究發現,藏、漢族大學生在朋友圈使用習慣、特點及動機方面呈現出諸多不同。
2.1 線上自我呈現時展現出不同程度的“遮蔽”策略:嫻熟與笨拙
戈夫曼將自我呈現的環境比作舞臺,有舞臺就有前臺和后臺,人人都是演員,而自我呈現的過程就是呈現主體對呈現行為進行管理的過程。微信朋友圈的分組功能賦予了個人操控前臺與后臺表演區域的權力,前后臺的隔離即部分內容的選擇性遮蔽,關閉了他人對自己形成印象的技術閘道,保證了個人的隱私,規避了不必要的展演后果,增強了用戶對線上人際關系的主動力與控制力。
在“是否會設置分組可見”及“分組可見的原因”的選擇方面,與藏族大學生相比,漢族大學會出于想要“隔離小部分人,減少不必要的誤會”而更傾向于選擇“設置分組可見”或經過其他設置如“提醒誰看”來做到“特定的內容只想給特定的人看”,漢族大學生深諳以漢族受眾為主要消費群體而設計、使用的漢語語言體系及專業話術,他們對微信朋友圈的丁點技術更新都異常敏感和雀躍,總能在技術的有限賦權下,嫻熟地將其應用到準確的線上自我呈現中,以求有限的隱私保護與臨時有效的自我遮蔽。
藏族大學生雖然在“基本信息的呈現真實度”的簡單操作上,不會將真實的個人信息暴露出來,偏向于“遮蔽”自己,但是在“是否會設置分組”及“選擇分組可見的原因”方面則顯得坦誠得多,他們在正式成為江西高校的大學生之前,還要參加為期一至兩年的大學補習班,即“預科生”,在補充一些基礎教育尤其是漢語言文化知識后,才會進入到高校與非少數民族的大學生一起學習與生活。藏族大學生的漢語基本聽說讀寫大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難,在“一般如何編輯文字”的選擇上,藏族大學生呈現出更加謹慎的狀態,漢語語言的難關也許是一個較好的解釋。在以漢語語言話術及邏輯框架的媒介使用過程中,往往需要轉換語言思維后進行再加工理解,如此一來,能夠真正理解到、表達出的意思早已打了折扣。相較于漢族大學生而言,他們的“語言遮蔽策略”使用顯得生澀又笨拙。
然而在“一般如何選擇或處理圖片”的選擇上,藏族大學生對自己朋友圈里的照片的要求更高、即可視化自我呈現的要求更高,相較于“語言遮蔽策略”短板,“圖片修飾策略”是他們采取的補充措施。
2.2 朋友圈使用中不同主要功能需求:精神娛樂與物質利益
在朋友圈的使用情況時長方面,雖然漢族大學生更新微信朋友圈的頻率較高,但是問卷調查結果卻顯示,藏族大學生使用朋友圈的時間更長,每日打開次數更多,呈現出更強的媒介依賴。在看待網絡主要的功能方面,在異域他鄉求學的藏族學生,相較于大多漢族大學生追求的“社交娛樂”,獲取更多用以消除環境的不確定性的信息對他們來說是更加實際有用的,這是他們的朋友圈工具理性。藏族大學生發朋友圈的最重要的目的在于“刷存在感,穩定社交關系”,而對于漢族大學生來說,“分享及記錄生活”則是最重要的目的;除了共同選擇的“情緒表達”外,藏族大學生有稍強的新聞敏感性,他們關心家鄉新聞時事、想念遠方親人,甚至因為要回家采蟲草掙錢而耽誤學業,國家單位是他們的熱門職業追求,他們對大學生活及未來規劃有更加實際的期望——物質利益。
歸納而言,漢族大學生更樂于更新朋友圈,主要是為了社交與娛樂、分享及記錄生活,這也符合威廉·斯蒂芬森在《傳播的游戲理論》一書中所論及的觀點——媒介融合時代用戶們最重要的動機之一,仍然是娛樂。藏族大學生主要是為了“刷存在感,穩定社交關系”并在“使用分組可見功能的原因”的多項選擇上,更多的將朋友圈當作承載物質利益的商業途徑,但同時又十分擔心這種利己行為會對朋友圈中的“朋友”造成視覺負擔,利益與情誼,二者通過簡單的“分組可見”這一“遮蔽”策略得以平衡,與漢族大學生相比,藏族大學生的媒介使用帶有更強的實用主義色彩。
2.3 朋友圈互動中不同人際交往傾向:維系與認同
在“發朋友圈時猶豫的原因”的多項選擇上,藏族大學生中,選擇“擔心他人評論冷嘲熱諷,說我矯情”和“擔心自己刷屏,被朋友們嫌棄甚至屏蔽”的人最多,而漢族大學生選擇“擔心他人評論冷嘲熱諷,說我矯情”和“擔心他人不敢興趣,忽視我發的內容”的人最多。可推測,藏族大學生更擔心他人的“反向”解讀,違于自己本意,且擔心過多的信息投放會影響線下的人際交往。漢族大學生則更擔心線上的自我呈現得不到他人的“反饋”,如果是“正向反饋”的話,那就再好不過,說到底,是在求關注、博認同,而這種認同,就簡化為一個簡單但寓意頗豐的計算機語言符號——“贊”。
在“會對什么樣的內容點贊”的選擇上,藏族大學生給“點贊”賦予了個人喜好及維系人際關系的寓意,真心摻雜著禮貌,他們以誠待人,無論是線上還是線下的朋友,都誠心維系。而漢族大學生則傾向于將“點贊”看作是一種簡單直接的“認同”,或是對好友的線上表達方式、文字編輯、圖片處理的贊賞,或是對好友的處事態度、生活方式的認可,或是對好友經歷的感同深受,都凝聚在一個小小的“贊”里。在“樂于點贊還是評論”的選擇上,漢族大學生表現出更強烈的使用“點贊”功能偏好,或許,對漢族學生而言,點贊意味頗多。一顆小小的愛心符號,勝過評論區的文字交流。表達“認同”比表達“看法”,甚至比“溝通”更簡單高效。
在“點贊目的”的選擇上,藏族大學生選擇“出于認可與關心”和“維系人際關系,禮尚往來式點贊”的人最多,在漢族大族學生中,選擇“出于認可與關心”的人最多,其次是“維系人際關系,禮尚往來式點贊”。可推斷,藏族大學生朋友圈使用更加注重人際關系的維持,漢族大學生則更加注重尋求認同。
3 結論與討論
“人們彼此都是一面鏡子,映照著對方”,在藏族大學生和漢族大學生的微信朋友圈使用對照中,可以發現族群新媒介使用的不同動機與偏好及原因。對藏族大學生而言,通過新媒體的使用,他們主動“出場”,但作為新技術的“非主流”使用人群,他們的媒介踐行受到一定約束,相較于難以確定的他人認可,他們更在乎技術下的實際情誼,體現出謹小慎微、維系式人際交往特點;對于漢族大學生而言,大學是他們社會化的關鍵期,他們利用新媒介完成個人電子形象的自我想象和構建,積極展演自我、尋找認同,體現出積極拓展、認同式人際交往特點。
參考文獻
[1]歐文·戈夫曼.生活中的自我呈現[M].北京:北京工業出版社,2008.
[2]華維慧.“秀”:技術“中介化”與人際傳播中的“自我”分析[J].編輯之友,2017(8):57-60.
[3]童慧.微信的自我呈現與人際傳播[J].重慶社會科學,2014(1):102-110.
[4]劉旦旦.微信朋友圈中的自我呈現研究[D].濟南:山東師范大學,2017.
[5]盧曉華.新媒介使用中的少數民族身份認同研究[D].武漢:武漢大學,2014.
基金項目:江西省社會科學規劃項目“‘一帶一路背景下江西國際媒介形象構建研究——以陶瓷文化傳播為突破口”(項目編號:17xw11)。
作者簡介:熊霞余,助教,研究方向為新媒體傳播、文化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