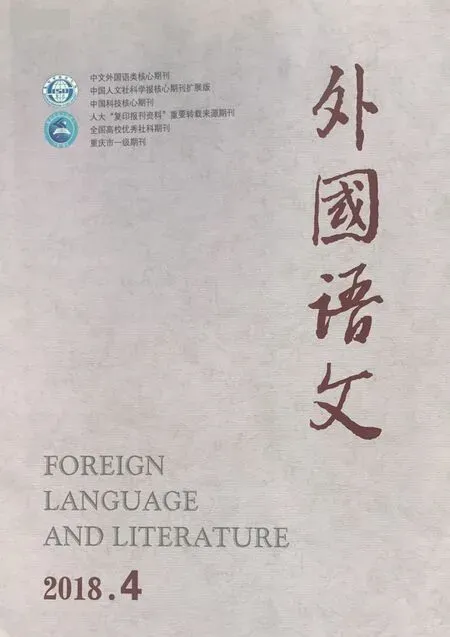我國語言學交叉學科界面研究回溯與展望
劉麗芬 陳代球
(1.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翻譯學研究中心,廣東 廣州 510006;2.南方醫科大學 外國語學院,廣東 廣州 510515)
0 引言
界面研究(interface studies)是近年來國際學術研究的一個新熱點,由俄羅斯大全俄語數據庫以及yandex.ru檢索可知,俄羅斯只檢索到6篇有關界面研究的文獻,第一篇以стык(接口)為關鍵詞的文獻出現在1966年,文章提及詩學處于語言學與文藝學的接口處。由知網檢索關鍵詞“界面”,再按“學科—外國語言文字”和“中國語言文字”檢索,共獲語言界面研究文獻42篇;檢索篇名“界面”,再點擊“學科”,無“外國語言文字”和“中國語言文字”學科;檢索篇名“接口”,再按“學科”—“外國語言文字”和“中國語言文字”檢索,共獲語言界面研究文獻147篇;最后剔除重復與不相關文獻,有關語言界面研究的文獻共154篇,加上其他無“接口”或“界面”關鍵詞篇名,但內容為界面研究的文獻以及專著和論文集,有關語言界面研究的文獻共161(專著和論文集)篇/部,發表刊物級別較高,有份量的論文大多匯集于《外語教學與研究》《外國語》《當代語言學》《外國語文》《中國外語》《外語教學》《外語研究》等刊物。研究內容主要集中于某些學科,跨學科界面研究微乎其微。學科內界面研究除主要集中在傳統語言學的句法—語義、語義—語用界面外,應用語言學中的接口理論研究也較多,多為介紹或深化國外某一界面理論,或將其理論用于外語教學中。限于篇幅,本文只綜述語言學交叉學科的界面研究。
1界面的基本問題
“界面”不是一個傳統術語,英語interface最早出現于19世紀,但不具當代含義。當代意義的interface首次出現于1962年。其出現和使用與計算機科學的發展同步,指不同系統之間的結合轉換技術。國內將interface譯成“界面”或“接口”,指不同或相鄰物相間分界面的系統產生的效應。界面研究的方法起源于西方,在西方認為是不同“界”,因而屬于界面研究,在我國漢語中不一定是兩個“界”。我國的語言研究自古并不存在“界”,自《馬氏文通》以西方語言理論研究中國語法以后,結構主義也逐漸滲透到語言研究中,“界”才逐漸區分。
進行界面研究,首先需弄清界面的定義、性質、范圍乃至學術定位等基本問題,但目前這一問題仍處于探索之中。學者們有以下闡述:
所謂“界”,即領域,“面”指兩個界的交接處,研究時的切入點和角度(潘文國,2012:1),界面指兩個不同體系和結構之間的相互配合和相互關聯(張俊凌,2012:160)。它是一事物的兩個或兩個以上接觸面或接觸點線,是相互密切關聯甚至相互融合、不易切分的部分(王克非,2014)。
就界面的性質及定位,潘文國(2012:2)、熊沐清(2013)、劉正光(2014:6)等大多數學者認為界面研究是一種語言研究的方法論,黃國文還認為界面研究是一種視角、一種路徑;董洪川(2012)認為界面研究是一種學術立場,一種學術態度,一種自覺的學術研究意識(張俊凌,2012:158);王文斌認為界面研究是一種研究對象;朱躍、伍菡(2013:20)指出界面是一種關系,一種同一學科不同分支間以及不同學科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聯系、相互互動的關系。界面的精髓在于其具有包容性、。劉正光(2014:6)指出,界面研究宏觀上主要是不同理論范式之間相互借鑒,或是不同研究途徑的相互結合;微觀上,是對學科內的本體問題進行深入全面的研究;應用上,是將某一學科的理論方法或工具運用到其他學科的研究中去,產生或形成新的學科領域。
有關研究范圍,劉世生認為,界面研究可以是多學科、復式學科、交叉學科、跨學科或者是超學科的;黃國文認為,從語言學內部本身來看,界面研究包括句法、語義、語音、韻律、語用等之間的界面研究(張俊凌,2012:158);外語界面研究既包括外語學科與其他學科的跨界研究,如語言與認知科學、語言與哲學、文學與社會學、文學與科學、語言與科學、文學與人類學、文學與傳播學、文學與環境學,也包括外語學科內部的跨界研究,如文學與語言、語言與翻譯、文學與語言教學等(董洪川,2012:3)。
學者們指出了界面研究的外延,但對界面的內涵陳述不清。給一個概念下定義絕非易事,需要對本學科理論體系有較為深刻的認識和理解,需要充分搜集并掌握已有的對相關概念的解釋和說明。結合學者們的闡述,我們給界面和界面研究下個定義:界面,又稱接口,即物體和物體的接觸,在人文社科中指不同學科間以及某一學科各分支間的交融,可構成點、線、面;人文社科中,界面研究指兩個或以上學科或某一學科內部兩個或以上分支對同一事實、問題、觀念、理論的合力探索。
2應用語言學界面研究
近年來,接口問題在二語習得研究中引起了關注和爭議。二語習得中隱性知識和顯性知識之間的接口問題主要有三種觀點:無接口說、強接口說和弱接口說。所謂“接口”,是指學習者“習得的語言知識”與“學習的語言知識”之間能否雙向流通的問題。一是語言與認知系統存在接口,二是語言內部模塊間存在接口。無接口假說認為兩種知識之間不存在轉換關系,而接口假說(強接口假說和弱接口假說)則認為外顯知識可以轉換成內隱知識(戴曼純,2014a:73),兩種知識實現動態轉換關系,即動態接口假說。Rod Ellis歸納隱性知識學習過程圖示為“輸入—吸收—發展中介語—輸出”學習過程框架(丁政,2011:141)。Tsimpli、Sorace(2006)以及Sorace、Serratrice(2009)對接口假說作了進一步補充:二語習得中純句法知識能完全習得,內接口語言知識也能習得,但外接口語言知識很難完全習得。弱接口說由Rod Ellis(1993)提出,他承認外顯知識和內隱知識是兩種獨立的知識體系,但強調不能用兩分法看待,應將二者視為一個連續體,顯性知識向隱性知識轉化是有條件的。國內對接口理論的研究分為三塊。
2.1 評介國外理論
趙中寶(2010)簡評了Alderson的《診斷外語水平:學習與評估的接口》一書,他認為其貢獻主要體現在:首次系統提出診斷性考試的假設性特征;以DIALANG為實例探討了診斷性考試的開發和研究;展望了診斷性考試研究的發展趨勢。
2.2深化接口理論研究
戴曼純(2014a:72)從生成語法角度討論二語習得研究所涉的接口及其常見類型,結合語言模塊間的映射及特征組裝等概念闡述二語接口的理論問題,分析了句法—語義、句法—形態、音系—形態、句法—語用等接口類型以及相關二語習得研究,認為內接口是發生映射或特征組裝之處,外接口則是信息傳遞之處,二語習得者無須習得接口,但需掌握不同語言模塊在接口處進行特征組裝的模式;揭示了接口假說存在的幾個問題,如表述的模糊性、證據的局限性和解釋力。他認為由有意識過程和潛意識過程獲得的語言系統之間有接口,但沒有證據表明是一一對應的先“學得”后“習得”的強接口關系,而是一種可能相互滲透的關系。常輝(2014)剖析了“接口假說”存在的問題和對“接口假說”的一些誤解,并對“接口假說”的適用范圍和研究范圍進行了說明。
2.3 理論的運用
2.3.1 將接口理論用于教學實踐
隱性知識和顯性知識間存在的是知識提取路徑的轉化,而非知識本身的轉化(顧琦一,2005)。顯性的語言知識經強化練習可轉換為內隱知識,內隱知識為新的外顯知識的學習奠定了基礎,提供了條件。當學習條件較有利時,這兩種形式的學習可相互轉化,也可同時進行,學習者既可理性地學習顯性知識,也可憑直覺學習隱性知識。吳明軍(2016:67)通過實證研究討論接口范疇對中國學習者習得英語照應語的影響,認為不同的約束特性對L2學習者的難度不同,因為它們涉及不同的接口。成分統領和近位主語約束特性,只涉及純句法,或句法-詞匯接口,更易更早習得。PRNP的約束特性涉及句法—語義接口,習得難度大于成分統領和近位主語約束。賓語約束涉及句法-語篇外接口,最難習得。他提出接口范疇對二語學習者的約束特性習得的影響,在二語習得中是否具有普遍性,能否推廣到移位和關系從句等其他句法知識的習得等有待研究的問題。邵士洋、吳莊(2017:11)采用誘導產出法考察了中國學生的英語冠詞習得,發現在低水平學習者的誘發語篇中普遍存在冠詞缺失現象,定冠詞the的過度使用則在中、高級學習者的中介語中仍然存在。一方面說明漢語重實指性的特征對冠詞指稱信息的習得有重要影響,也印證了接口假說關于語言接口知識特別是句法—語用等外部接口知識難以習得的觀點。
2.3.2 學得與習得的界面研究
外語學習過程是一個既有學得又有習得的過程,學得可向習得轉化,即學得與習得有“接口”的觀點。語言學習的最終是習得的發生,學得是促使習得發生的手段,學得的知識可以轉化為習得系統的知識。高育松(2009)通過調查中、韓英語學習者對英語中動句和非賓格結構的習得,檢驗二語接口現象習得中母語模塊遷移說并不成立;袁博平(2015)圍繞“界面假說”,從漢語的“非賓格動詞與非作格動詞”“存在極性詞”“疑問詞話題化”“到底……”類疑問句等語法點入手,依次考察了英語母語者在習得漢語時對“句法—語義”這一內界面和“句法—語篇”“句法—語用”這兩個外界面的習得情況。雖然界面會給二語學習者帶來習得困難,但并非像界面假說所預測的那樣永遠難以習得。界面本身可能并不是造成二語習得困難的根本原因,界面所需的信息處理量才是決定二語學習者在多大程度上習得各種界面的關鍵因素。
2.3.3 測試方面的界面研究
主要討論以下三個問題:1)二語習得與語言測試。二語習得和語言測試存在不少相通或接口之處:二者均關注語言能力的建構,著力研究的核心問題是如何描述和解釋二者行為中出現的差異。研究方法上,二者為了揭示學習者中介語的能力,均采用定性或定量法對學習者的語言行為進行系統的觀察(孔文,2006)。要使二語習得和語言測試之間可能存在的接口轉變為現實,需拓寬語言測試的評估手段,關注學習者能夠真正使用的語言及其使用過程,語言測試應該與教育環境協調一致。(陳紀梁 等,2005)2)跨文化交際能力與語言測試。劉寶權(2004)用文化測試實例考察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證明了文化測試的重要性,但未進行接口研究。3)語料庫語言學與語言測試。語料庫與語言測試的接口可從真實性、科學性和對計算機技術的依賴性三方面進行研究(張文星,2013)。
2.3.4 教學之間界面的研究
學者們有以下觀點:語言實踐是課堂教學與獨立交際之間的接口(李同路,2012);專門用途英語教學是大學基礎英語和雙語教學之間的有效接口(閆素萍,2006);設計出起到橋梁作用的過渡性課程和教案,是做好由大學英語教學向雙語教學過渡的接口工作的基礎(葉建敏,2005);雙語教學與公共英語教學的界面問題可從課程設置、教材編寫、教學方法的使用、師資隊伍的建設四個方面探討(王海華 等,2003)。以上研究均未進行界面互動討論。張新玲(2009)探討了批判性思維培養和讀寫結合寫作教學的界面問題,認為二者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寫作促進批判性思維發展,批判性思維影響寫作能力和閱讀能力。陳偉(2009)從意義哲學(本體論)、二語習得屬性(認識論)與教學機制(方法論)三個層面分析了詞典與外語教學對接界面的學理歸因。
3認知語言學、篇章語言學、翻譯的界面研究
認知語言學主要探討了隱喻和轉喻的問題。隱喻和轉喻的認知視角和認知范疇因認知相對性而發生改變,隱喻和轉喻因此發生相應的相互轉化,由此產生隱轉喻界面。在認知相對性的作用下,隱喻和轉喻之間因存在界面而產生連續體關系,隱喻與轉喻認知功能的互相轉化需要認知視角的轉變、認知對象的重新范疇化以及范疇化認知相對性的作用。(龔鵬程 等,2014)在隱喻、轉喻和隱轉喻理論框架內,有學者對比考察英漢語中含有“mouth”/“口(嘴)”和“fire”/“火”的表達,在對隱喻識別與詞典義項區分的界面研究基礎上提出了義項區分模式。
篇章語言學主要探討了兩個問題。一是詞匯銜接與語篇連貫問題。詞匯銜接為篇章的連貫提供了基礎,篇章的正確理解需經語用推理才能挖掘其蘊含意義,關聯理論解釋了交際者如何在話語理解過程中根據語境信息及其事物的關聯性進行語用推理,從而得出符合邏輯的結論(江景,2005)。二是話輪接口問題。張雪(2006)闡述了話輪接口產生的主要原因及其假設、對話體語篇話輪接口的類型(話題推進中的話輪接口、話題轉移中的話輪接口、話題回逆中的話輪接口)、篇際對話中的接口問題(篇際對話關系中常見的接口標記)。
翻譯所涉及的界面主要有兩大類,第一類是翻譯轉換中不同語言文化間的界面,其中有翻譯與原文的界面,有譯文與母語的界面;第二類是翻譯與不同學科間的界面,指人們可以從語言學、文藝學、社會學、傳播學、心理學等多個學科角度去認識翻譯問題,使翻譯學在本質探討和方法探討上得以拓展(王克非,2014:1)。翻譯語言界面研究包括三個方面:所有翻譯產品的屬性,即翻譯共性;特定語言間翻譯產品的屬性,即翻譯語言的屬性;某個或某類翻譯產品反映出來的語言特征(張俊凌,2012:160);肖宏德(2013)用實例探討了語內翻譯和語際翻譯的界面。他認為,語內翻譯在語際翻譯的理解階段和表達階段均起重要作用,語際翻譯借助語內翻譯構建源語言和譯入語之間的協調和對話。
4 學科間界面研究
外語界面研究的切入點要從一個中心、兩個維度和三個層面進行研究。一個中心即以語言為中心——以語言為邏輯思維的起點來研究文學、翻譯、教學和文化,反向亦可;兩個維度指從理論和方法兩個維度來研究上述五大領域的關系;三個層面指在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研究。(彭青龍,2014:7)
語義學與語用學界面。21世紀是意義研究的世紀,作為20世紀末的“顯學”的語用學,其微觀語用學基于語義學等語言學基礎學科將更加深入,其宏觀語用學由于其廣大的應用性、多維性和跨學科性將更加廣袤,語用學將更為“顯學”(侯國金,2013)。語義學和語用學一直是語言研究的重點。關于語用學和語義學二者的關系,有三種不同的觀點:語用學是語義學的一部分;語義學是語用學的一部分;語用學和語義學是兩個獨立又互為補充的部分。目前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的是第三種觀點(沈家煊,1990)。語義學和語用學的區別是語言的兩種不同類型知識的區別:一是語詞意義和邏輯形式結構的知識,一是如何在交流中使用這些結構的知識。(殷杰 等,2002)語義—語用界面研究分為兩塊:1)理論介紹。張韌弦、劉乃實(2007)評介了《規約含義的邏輯》一書,認為它是語義語用界面形式化研究的新突破。2)理論運用。用某一理論討論語義—語用界面問題。仇瑤宇(2009)從認知語言學角度研究語義和語用界面問題,語義是語言表達形成的一種意象,這些意象的分布應該是以“語義”軸為縱軸的正態概率分布,在語義意象正態分布的兩端,由于形成的語義意象越來越偏離語言規約含義,所以需要啟動和借助于人的認知能力進行語用交際推理;伍思靜、劉龍根(2012)以Bach的觀點分析語義語用界面,Bach堅持語義學/語用學清晰劃界觀,否定兩者之間存在交叉重疊,提出“界面”說是一種“誤導”,盡管這一觀點過于簡單化,但他對語義學與語用學之區別以及兩者在言語產生和理解過程中不同作用的揭示,為深入探析語義學/語用學之關系、推進意義理論研究提供諸多啟迪。姜濤(2010)用雅茲寇爾特提出的默認語義學模式解釋現代漢語將來時助動詞的語義—語用界面意義。從語義角度看,一個默認的將來意義始終保持不變;從語用角度看,推論性的情態意義,表達說話者對話語事實內容的態度,如不確定性、確定性、模棱兩可和可能性。
語法學與語用學界面。語法和語用的關系建立在規約性和意向性相互作用的基礎之上,語法是實現語用的資源手段,語用是語法在使用中的具體實現,即語用是對語法在語言情境下的選擇。(張紹杰,2010:74)語法學與語用學兩學科之間的界面研究主要以句法—語用界面研究較多,句法—語用界面主要涉及兩個層面,即“前邏輯形式”層面和“后邏輯形式”層面,句法和語用在“邏輯形式”形成前發生互動,其互動有兩類:復雜事體結構中外在論元和內在事體結構之間語義鏈的語用推理。在句法生成過程中,外在論元與內在事體結構的聯系不是動詞或句法結構賦予的,而是語言使用者的語用推理所產生的,因此在句子生成過程早期,語用推理就已經介入其中了。在“后邏輯形式”層面,句法—語用界面研究要解決的問題主要是有定效應問題。這兩個層面的語用分析均在關聯理論的總體框架內進行(胡旭輝,2010)。韋理、戴煒棟(2010)分析了大學生英語定冠詞的習得情況,尹洪山(2012)考察了學生習得英語三類前置句式的情況,發現語境對前置句式可接受性的影響既與前置句式的類型特征密切相關,也與學習者的目的語水平具有一定的關系。
語言與社會的界面。社會文化語境、語言變體、話語和兒童語言能力是語言與社會界面研究的主要對象。社會語境影響了說話人做出的語音、詞匯語法和語義選擇。系統功能語言學把語言置入社會文化語境來研究,把語言看作一種行為潛勢,語言上的一種意義潛勢。在語言與社會的界面研究上,系統功能語言學提供了很好的理論接口(楊信彰,2014)。杜冰研(2006)在對言后行為的研究中發現,言后行為是語言與世界相互作用的界面,語言的實現程度決定了與世界相互作用的程度與結果。該界面可以通過心理活動、言語行為、身體行為單方面或任意組合的方式體現。
語言與文學界面。該類文獻不多,楊金才認為,文學研究,如果離開了語言學只能是空中樓閣,所以文學研究和語言學一直以來就是相結合的,只不過是結合得不緊密或不太好而已(楊紹梁,2012:144)。喬國強(2012)指出,文學的界面研究本身強調的是“界面”,即強調其整體性,文學作品與文學理論、社會思潮、意識形態等相關問題共處于一個“渾然一體”的整體之中,在實踐中注重使用相互關聯或互動的方法。有關語言與文學界面研究文獻不多,論文集《文學和語言的界面研究》共收論文25篇,主要從語言學入手研究文學或從文學語言出發研究語言學,實質是幾個問題結合起來討論,真正進行界面互動研究的很少。
認知語言學與語篇分析界面。批評隱喻研究是一個綜合了認知語言學、批評話語分析、語料庫語言學,甚至社會語言學的交叉研究領域。(徐瑩 等,2013)魏在江(2006)從隱喻認知與語篇的界面探討隱喻的語篇功能。隱喻在語篇的生成與發展中,既可引出新的話題,與上文構成銜接關系,也為新信息的引入提供切入點,使語篇構成一個前后銜接的整體。隱喻在語篇連貫機制中起紐帶作用,制約整個語篇信息的發展;語篇是理解隱喻的重要載體,是隱喻意義的體現形式。
翻譯與其他學科界面。曾文雄(2012)評析了莫娜·貝克(Mona Baker)編著的《翻譯研究批評性讀本》一書,該書從全球化、國際化、文化社會學、民族志學、文化人類學、文化生態學和社會認知理論等界面考察翻譯,所涉及的研究界面具有顯著的前瞻性。閆麗俐(2014)將語境理論、話語特征理論和信息結構理論應用于語篇翻譯過程中,構建了基于翻譯過程的話語分析與語篇翻譯接口的模型,結合實例展示了該模型在語篇翻譯實踐中的應用。李雪芹(2014)從音形結合、音義結合、文化與意境結合三方面探討了美學在商標翻譯中的體現,但未真正進行界面互動研究。
5 語言學交叉學科界面研究展望
綜上,我國宏觀應用語言學及交叉學科界面研究以應用語言學二語習得中的接口假說研究較多,其他方面研究較為薄弱,有些方面仍為處女地。因此,我國語言學界面研究頗具潛力,可挖掘的課題頗多,可為我國今后的語言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方向,可從以下幾方面深化、加強與拓展界面研究。
第一,界面概念及定位。
進行任何研究,必先弄清其概念、內涵與外延,學者們對界面的基本問題研究不多,一般認為界面研究屬于語言研究的方法論。對它的性質、任務、范圍乃至學術定位等有待進一步明晰化。
第二,界面互動研究。
大多文章冠以界面,卻未探討界面之間的交叉互動關系,對某一語言現象分割開來闡述,因此,在今后的界面研究中,需洞悉界面研究的實質,探求界面的關聯與融合,切實進行界面互動研究。
第三,內界面研究。
界面研究主要為應用語言學二語習得中的接口假說研究,其他學科內界面涉獵較少甚至為零。因此,今后的研究除深化現有如應用語言學內界面研究,加強認知語言學、篇章語言學、翻譯學等內界面研究外,還應拓展如語言哲學、社會語言學、心理語言學、計算語言學等其他學科的內界面研究。
第四,各學科間的界面研究。
目前的研究主要是某一學科各分支之間的界面研究,跨學科層面上的界面研究很少。因此,要拓寬研究領域,加強各學科間,尤其是語言學與哲學、認知學、計算機學科、心理學、傳播學、生態學、協同學等以及其他學科間的交叉互動研究,促進這些學科之間的互動與融合,催生新的邊緣學科,推動我國語言學研究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