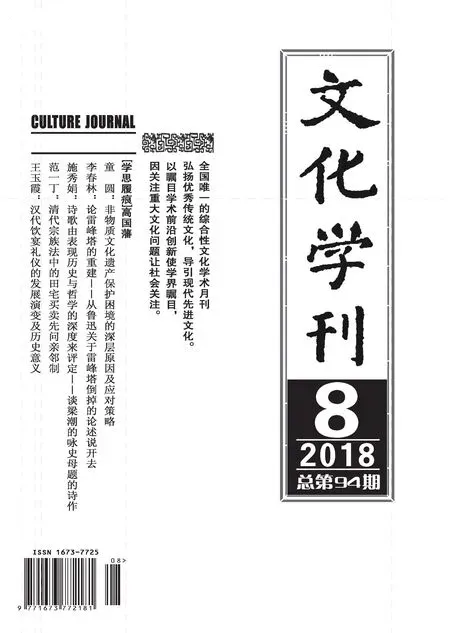論庫爾德工人黨的暴力化演變
宋小超
(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陜西 西安 710100)
一、庫爾德工人黨的成立
自1923年土耳其共和國建立起,凱末爾等國家精英為構建現代化單一民族國家,否認庫爾德人的少數族裔特性,強制同化庫爾德人,為土耳其民族國家的構建埋下隱患。20世紀50年代,土耳其開始了政治民主化進程,一黨執政轉變為多黨競爭參與政治的格局,孕育出了一批受新式教育的中上層庫爾德政治階層。在1961年憲法的支持下,新左派團體紛紛成立,庫爾德工人黨(以下簡稱庫工黨)孕育于具有青年運動激進傳統的土耳其青年革命聯合會。同一時期,全球左翼思想盛行,大多數新興政治力量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左翼思想的影響。[1]左翼話語體系的主題之一是民族主義,在此影響下,土耳其庫爾德左派不僅要求賦予庫爾德人文化權利,且要求改變庫爾德斯坦地區的社會經濟制度及不公平的等級社會。自土耳其共和國現代化改革以來,東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懸殊,東部庫爾德人聚居地區長期貧窮落后,新興政治力量將東部地區貧窮落后的現狀歸結于統治階級強制民族同化的社會經濟政策。左派基調為庫爾德人發動革命提供了思想基礎,新興社會政治力量的出現和世俗化,與現代化過程中產生的民族主義思想相結合,為叛亂提供了充分條件。
魅力型領導人厄賈蘭對庫工黨的建立起到了關鍵性的引導作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土耳其國內經濟危機造成大批工人失業,社會暴力盛行,庫爾德斯坦地區時常發生左右派之間的沖突,安全態勢與社會穩定遭到破壞。在此背景下,厄賈蘭趁勢而起,于1974年組建“阿波會”(庫工黨前身,因厄賈蘭小名阿波而得名),至1975年“阿波會”基本成型,1977年起草了革命宣言《庫爾德斯坦之路》,次年正式成立庫爾德工人黨,設立宣傳刊物《星期六》,堅持馬列主義,強調武裝革命,主張依靠無產階級力量進行民族和民主的雙重革命,建立“獨立,民主、統一的庫爾德斯坦”。該組織將庫爾德人族裔認同明晰化、政治化,使庫工黨的活動具有了民族和民主的雙重屬性。然而,建立獨立國家的政治目標明顯與土耳其民族國家構建背道而馳,勢必受到土政府的嚴厲鎮壓。
二、庫工黨的暴力化及其特點
庫爾德工人黨的暴力化演進大致分為四個階段。從1979年庫工黨刺殺正義黨成員布卡克未遂至1983年為第一階段,此階段是庫爾德工人黨從事暴力活動的開端,是其經歷從合法到暴力的轉變,革命宣言從理論發展到實踐的過程。布卡克事件后,直到1983年庫工黨并未對與土耳其政府相關的目標進行襲擊,而是專注于與其他民族組織開展斗爭。這一時期,庫工黨在激進的左翼思想和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指導下,通過暴力手段排擠打壓其他庫爾德組織,試圖成為土耳其庫爾德人的唯一代言人。在東南部地區極端貧困、庫爾德人政治和文化權利遭到粗暴剝奪、庫爾德人對政府日漸不滿的背景下,這一戰略為新生的庫工黨發展壯大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條件。
1984年庫工黨成立武裝部隊至1999年厄賈蘭被捕為庫工黨暴力化的第二階段。1980年,土耳其軍方以嚴重的分裂主義問題發動政變,加強對庫爾德人組織的打擊,軍方“以暴制暴”的激進政策迫使庫爾德左派組織采取極端行徑。庫工黨于1984年8月成立庫爾德斯坦自由旅,同日分別在埃魯赫和謝姆丁利發動武裝對抗土耳其的游擊戰,揭開了庫工黨暴力反抗土耳其政府的序幕。截止1985年8月,庫工黨已制造70多起武裝沖突,導致200多人死亡。1986年,歐洲的庫工黨成員對土耳其在西德和挪威的辦事處等目標進行了襲擊[2],標志著庫工黨暴力活動的擴大化和歐洲化。而土耳其政府對庫工黨的暴力活動應對稍顯遲緩,直到1985年政府才開始在東南部加強軍事守備,但其軍事應對策略收效甚微,加入庫工黨的人數依舊呈上升趨勢。蘇聯解體和海灣戰爭之后,庫工黨開始調整策略,一方面強調伊斯蘭主義和民族主義,建立伊斯蘭影子黨,以適應國內的伊斯蘭主義氛圍,吸引庫爾德人的支持。另一方面擴大在歐洲的暴力活動,破壞土耳其的外在形象,激起歐洲庫爾德人的認同感。[3]1999年,厄賈蘭被土耳其逮捕,其暴力活動暫告一段落。
從厄賈蘭被捕到2004年庫工黨宣布重啟武裝斗爭為第三階段。1999年,隨著厄賈蘭被捕,庫工黨宣布停火及土耳其獲得歐盟候選國資格,和平解決庫爾德問題的曙光似乎已經可以窺見。厄賈蘭甚至表明愿意放棄建立獨立的庫爾德國家的目標,轉而在統一的土耳其國家內追求土耳其人與庫爾德人的平等。厄賈蘭提出庫爾德人將以自治、聯邦的方式爭取一個真正民主的土耳其。[4]這一時期,庫爾德工人黨的暴力活動大為減少,開始要求通過政治途徑解決庫爾德問題,同時大力加強其在歐洲的宣傳攻勢,庫工黨通過在庫爾德人聚居區組織團體游行、節日慶祝等方式強化庫爾德人民族凝聚力來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歐洲的土耳其政策,力圖使土耳其加入歐盟與庫爾德問題相聯系。由于庫爾德人大量移民歐洲國家,歐盟不得不考慮庫爾德人的訴求,使得土耳其外交往往為庫爾德問題所挾持。[5]戰爭的結束并不意味著庫爾德工人黨的終結,也不意味著土耳其庫爾德問題的結束,一直在土耳其庫爾德人中居于領導地位的政治組織庫爾德工人黨依然保持其控制權和影響力。而土耳其囿于國內民族主義的羈絆,不顧新的和平機遇,無法從根本上正視庫爾德問題,這使得庫爾德問題依然存在。
從2004年6月1日庫工黨重新宣布武裝斗爭至今為其暴力化的第四階段。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凸顯出庫爾德斯坦在中東地緣政治中的戰略地位及其對美國的重要性,伊拉克戰爭導致伊拉克主權國家的分崩離析和庫爾德地方勢力的日漸壯大,伊拉克庫爾德自治政府“準國家”地位極大地鼓舞了土耳其庫爾德人,同時也為土耳其庫爾德工人黨的跨境活動提供了便利的條件,庫工黨在伊拉克北部建立起反擊土耳其的基地。與此同時,土耳其政府在過去的數年間在庫爾德問題的解決上無所作為,始終不愿承認庫爾德人獨特的民族特性,對庫爾德人的政治訴求也避而不談,這使得大多數庫爾德人對政府日漸失望。2004年,庫爾德工人黨重新組建部隊,2006年沖突再次上升。
庫工黨的暴力化呈現出以下幾個特點:一是組織訓練正規游擊武裝對抗土耳其正規軍隊,一度將土耳其拖入低度戰爭,極大地阻礙了土耳其政治經濟的發展;二是襲擊或綁架對象一般為土耳其境內平民,加重了其暴力化色彩;三是在歐洲的和平宣傳活動吸引了大部分歐洲庫爾德人的關注,獲得了歐洲民眾的同情,也給歐洲政府反對庫工黨帶來無形的壓力;四是20世紀90年代庫工黨暴力活動在歐洲擴大化,加之海灣戰爭中庫爾德難民造成的國際影響,使土耳其庫爾德問題進一步歐洲化和國際化,導致土耳其面臨空前的外交壓力,也給土耳其加入歐盟的進程增添了庫爾德人新維度;五是20世紀90年代后期庫工黨在國內的暴力活動遭到土耳其的打擊日益減弱,但以新的自殺式炸彈襲擊方式出現,給土耳其政府的應對策略提出了新挑戰。
三、庫工黨暴力化的原因
歐洲民族主義在中東的傳播喚醒了庫爾德人的民族認同感,庫爾德民族主義的覺醒使其開始追求政治和文化上的權利。歐洲在對中東進行殖民掠奪的過程中,無論是其主觀上為加強統治而采取的“分而治之”政策,還是客觀上帶來的先進的政治制度及民族主義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喚起了中東地區的民族意識。一戰后,尤其是《洛桑條約》的簽訂,使得之前《色佛爾條約》中計劃建立的庫爾德國家化為泡影,庫爾德人的民族反抗情緒加劇,民族獨立呼聲高漲,在土耳其共和國早期多次武裝叛亂,均被土耳其平定。土耳其共和國建國之初在構建單一民族國家目標的指引下,在各個領域強制同化庫爾德人,引起了庫爾德人的強烈不滿,強化了庫爾德人的民族意識。且土耳其政府局限于單一民族國家構建的理論,未從根本上對本國的民族政策做出調整,從而也就無法解決庫爾德問題。土耳其庫爾德問題的根源在于,土耳其共和國在奧斯曼帝國多族群、多宗教遺產基礎上所采取的強制性同化措施,損害了庫爾德人的文化權利,且向民族國家轉變又過于倉促,進一步激化了矛盾。[6]而20世紀50年代開啟的民主政治轉型又在某種程度上激化了各民族之間的矛盾,各大政黨對庫爾德人的合理訴求并沒有進行充分考慮,且幾次軍人干政時期對庫爾德人的嚴厲鎮壓又使得采用其他合法途徑解決庫爾德問題的希望幻滅,因此,庫爾德人只有依靠武裝斗爭才能避免遭到同化的命運。
出于對選票政治失望的緣故,在左翼思想的影響下,庫工黨轉向激進化的方向,并且逐漸瓦解了其他競爭者,使庫工黨成為土耳其庫爾德人的唯一代言人。這一結果雖然有利于庫工黨整合區域資源,獲得當地民眾支持,但缺乏競爭對手亦使得庫工黨很難就自身的策略,尤其是不合理的策略進行反思和調整,庫爾德工人黨已經排除了其他庫爾德民族主義政黨,將暴力甚至恐怖主義視為可以接受的斗爭和不可避免的后果。暴力手段的便捷性及短時效益使庫工黨難以舍棄這一斗爭手段。通過制造暴力事件又可以最大限度地吸引公眾對該黨的關注,迎合庫爾德人對政府的負面情緒,快速打擊其他競爭對手,招募更多青年加入該黨。因此,選擇武裝斗爭的暴力路線不僅僅是指導庫工黨的庫爾德民族主義及左翼思想影響的結果,而且也有著實實在在的現實考量。同時,中東庫爾德人分散于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敘利亞四個國家的結合地帶,且所處地區多為山地,交通不便,庫爾德問題在地緣政治上的復雜性也使得庫工黨得以獲得鄰國庫爾德人的同情和支持,從而將其跨境襲擊的游擊戰持續下去。
四、結語
庫工黨持續制造的暴力事件使土耳其政府受到來自國內外各界的關注,而其根源則需追溯到土耳其共和國的世俗化和現代化策略的缺陷,同時,官方和民間對庫爾德人的壓迫和潛在歧視加劇了族群矛盾,阻礙了土耳其民族國家的建設。土耳其的現代化提高了新興精英分子的民族權利意識,尤其是民主化改革和1961年憲法,更是為左派庫爾德精英爭取庫爾德政治文化權利提供了機遇,庫爾德組織積極表達族裔訴求。土耳其政府對庫爾德人的強制同化和軍方的嚴厲鎮壓使庫爾德問題以更激烈的庫工黨反叛形式出現。持續十多年的暴力活動使土耳其當局不得不重新直面建國初期遺留下來的難題——庫爾德問題,而解決庫工黨問題的關鍵在于土耳其政府必須正視庫工黨暴力行為背后更為深層次的矛盾,承認庫爾德人的少數族裔特性,加強民主政治體制改革,進而促進凱末爾主義的與時俱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