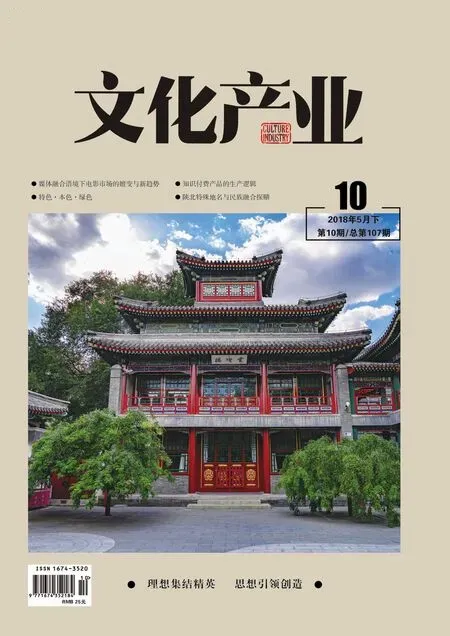話劇《暗戀桃花源》節選喜劇淺析
◎張瑋瑜
(華南師范大學 廣東 廣州 510006)
《暗戀桃花源》是一部經典的悲喜劇,其中《桃花源》部分講述了一段滑稽可笑又富含深意的“武陵三角戀”,老陶無法忍受妻子春花與袁老板偷情,選擇了逃避,來到桃花源中,受生活在那里的白袍男女感化,回到家中卻發現春花與袁老板的生活并不幸福。當他想重回桃花源時,卻再也找不到來路。《桃花源》的精彩演繹與刻意的場景“打破”和“轉換”,引起觀眾不斷“發笑”,在笑聲的背后,蘊含著深刻的現實矛盾與人生思考。
一、人物形象
《桃花源》塑造了一批性格鮮明,體現“丑”的特點的人物形象。車爾尼雪夫斯基曾說:“丑在滑稽中我們是感到不快的;我們所感到愉快的是,我們能夠這樣洞察一切,從而理解,丑就是丑。既然嘲笑了丑,我們就超過它了。”[1]喜劇中的“丑”,不僅指外貌的丑陋、身體的缺陷和卑劣的品質,其外延泛化為一切具有負面意義、否定性價值、會對人類的自由產生阻礙的事物。而《桃花源》中,老陶無疑是一個典型的“丑”的集合。
老陶中等身材,其貌不揚,形容邋遢,不善言辭,對外作為漁夫而捕不上大魚;對內作為丈夫而不能進行床事。戲劇一開場,老陶無能,他三番四次想打開酒瓶的瓶塞卻始終失敗,這與后來春花輕易拔開瓶塞形成鮮明對比;明知妻子與袁老板偷情卻只能認命似的逃離開,一味退讓可見他的軟弱。在物質、地位和性(本能)這三種價值需求中,老陶都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失敗者,他的身上融合了各種“丑”的特征。正是老陶的以丑為美,將丑偽裝成美,在倒錯中顯示真實,在無意識中呈現出外現的“丑”,引發了觀眾的笑。
在《桃花源》中,所有人都有缺點。春花庸俗潑辣,與袁老板偷情,無視婚姻愛情的忠貞。袁老板為人輕佻,往情人家里送棉被,手段狠辣,提出要老陶去充滿危險的上游捕魚,后來又迷上賭博以致家財盡散。還有順子,言行無知,一本正經地介紹“蒙太奇是一個法國人”,讓人捧腹不已。
《桃花源》中人物的丑陋,讓觀眾發笑之余,還會進行理性的審美與反思。段寶林認為:“丑只是喜劇反映的對象而已。對象不等于內容,藝術內容中更重要的是對描寫對象的審美感情和審美態度。”[2]我們嘲笑老陶、春花、袁老板,不僅是被他們的表演所逗樂,更是我們在這些人物的身上反思缺陷,對否定因素的批判和對內心的自省。
“喜劇是人類反思自身、超越現實的重要方式,美學喜劇性的核心是喜劇意識。”[3]喜劇讓觀眾在欣賞喜劇的過程中進行價值判斷與審美,最終實現在現實社會中的更美好的改變。觀眾嘲笑劇中的人物,既是在表達對否定性人物的鄙視與指責,也是在反思審美主體意識到的期望與現實的矛盾。
二、表現手法
喜劇通過滑稽可笑的藝術形式,展示丑惡、落后與美好、進步事物之間的矛盾,對被否定的事物進行諷刺,表達蘊含的深刻思想。“喜劇將那無意義的撕碎給人看”[4],從而引起人們的厭惡與自省。
夸張。夸張是指將正常的行為動作放大,在“失真”的環境中通過不和諧的言行暴露“丑”。如《桃花源》一開場,老陶咬不動大餅,憤怒地把兩張餅扔在地上,一邊連踩帶跺,一邊大嚷“踩死你”。歇斯底里的叫喊和夸張的演繹將人物性格中消極的一面放大,讓觀眾更直觀地發現“丑”。
誤會。誤會是指喜劇刻意安排的理解上的交錯,從而制造出矛盾沖突。老陶回家后,想帶春花和袁老板一起去桃花源生活,然而春花和袁老板卻以為老陶是回來索命的,認為桃花源其實是噬人的陰曹地府;在明確老陶真的還活著后,又以為老陶精神失常了。三人的誤會與行動組成一段鬧劇,深刻地反映出現實對“桃花源”——理想生活的懷疑。
重復。重復是指喜劇中的臺詞、動作或情景反復出現,由此起到強調和呼應的作用。如袁老板重復講述偉大的抱負,“讓我們這些延綿不絕的子孫,手牽著手,肩并著肩,左手拿著葡萄,右手捧著美酒,口里含著鳳梨”。由于《暗戀桃花源》的敘事時空交錯,重復的表達能將不同場景連貫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增強觀眾對人物“丑”的感受。
諷刺。諷刺是喜劇很重要的一個要素,以批判和否定丑惡為旨歸。往大的來說,《桃花源》整部喜劇都在進行諷刺 ;往小的來說,作為一種表現方式,諷刺主要通過言語和動作揭露并抨擊丑惡。如春花和袁老板借“魚”小暗指老陶的生殖缺陷,帶著一些惡趣味,又直指要害。
“真正喜劇性的(笑謔的)東西分析起來之所以困難,原因在于否定的因素與肯定的因素在喜劇中不可分地融為一體,它們之間難以劃出明顯的界限。”[5]喜劇的否定性因素不像悲劇那樣赤裸裸地將罪惡、死亡、毀滅擺在眼前,而是隱藏在喜劇的笑聲當中。觀眾要在笑聲中發現“丑”,理解喜劇的內涵,很大程度上依靠喜劇要素的有效表現。因此,喜劇是“丑”在臺前表演,然后美嘲笑“丑”,將“丑”壓倒,讓觀眾在其中實現審美超越。
三、內涵分析
《桃花源》體現了諷刺批判精神和自由狂歡精神。一方面,該劇通過諷刺“丑”,批判社會問題和人性弱點,觀眾在笑聲中以旁觀者身份反思現實婚姻生活正確的幸福觀和反省人性格軟弱妥協的弱點;另一方面,喜劇擺脫外在束縛,高揚人的主觀精神,對現實黑暗的批判與否定以及對自由生活的向往與憧憬,是肯定與否定、贊美與批評、建設與毀滅、死亡與新生的融合,肯定人的價值,讓觀眾從喜劇中追求自由。
在《桃花源》尾聲,老陶終于對現實生活感到失望,當他心灰意冷想回桃花源時,卻發現再也找不到歸途。“世界對情感的人來說是一出悲劇,對理智的人來說是一出喜劇。”[6]喜劇帶給人的沖擊不及悲劇的強烈,卻更加突出人的主體地位。觀眾對喜劇發笑,也保持著理智的審美距離,觀眾無論在劇中如何大笑,劇終時都會有一種別樣的清醒。因為我們知道自己不是劇中的人物,卻又清楚地意識到話劇所展示的矛盾來源于現實。老陶希冀平靜美好的家庭,春花想要更好的婚姻生活,袁老板有一個偉大的抱負,所有人都在追求,但都失敗了。
“喜劇永遠是可笑的——這正是喜劇特征之所在。與此同時,喜劇與可笑又不同,它具有社會意義,與建立正面的美學理想相聯系。”[7]桃花源是虛幻的,但喜劇反映的社會中家庭、愛情、自由的矛盾植根于社會現實。人的性格的弱點導致了老陶與春花婚姻的悲劇;春花放棄老陶而選擇與袁老板生活,但生活卻變得更加痛苦,可見現實中家庭生活的矛盾有其必然性;老陶在上游的發現讓他窺探到桃花源的純潔,但想折返時卻徒勞無功,體現理想的美好與不可企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