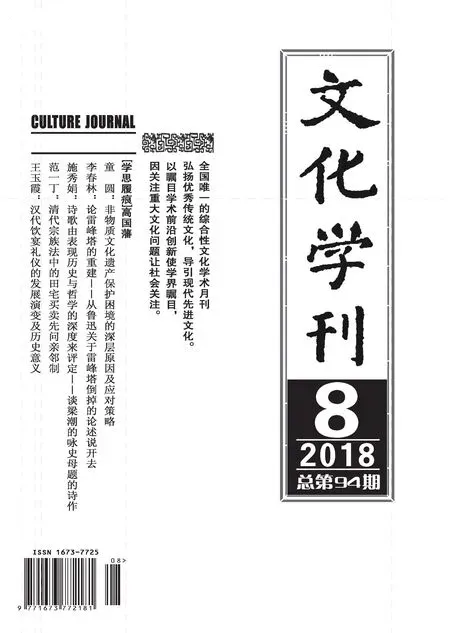清代宗族法中的田宅買賣先問親鄰制
2018-03-07 10:56:23范一丁
文化學刊
2018年8期
范一丁
(貴州黔勻律師事務所,貴州 都勻 558000)
宗族作為一種社會組織形式,其內部由兩個共同體組成,一個是以小家庭為單位的經濟共同體,另一個是以宗族為單位的血緣共同體。宗族由同族姓所有成員組成,且以男系成員為主,而取得族籍是具有共同體成員資格的標志。[1]在清代,以族長權為核心,以家譜、族田、祠堂為控制手段的宗族制度,出現了回光返照之勢。同宗共祠的男性血親,按照一定的規范組成的宗族[2],“落落差錯縣邑間”[3]。乾隆初年,江西巡撫陳宏謀說:“直省惟閩中、江西、湖南皆聚族而居,族皆有祠。”[4]據統計,乾隆二十九年(1764)江西省有宗祠的宗族竟達8 994族。[5]清代宗族法也在經歷宋、元、明各代的發展后,內容更加完備,調整范圍涉及宗族內部社會生活各個方面,其法的規范性進一步加強。清代宗族法是國家制定法的重要補充,同時,宗族法也是最基本的民事習慣法,它涉及宗族內的身份、婚姻、繼承、買賣、租賃等各方面。從清朝的社會實際來看,宗族法承擔了對宗族內部各種社會關系,包括財產關系、婚姻關系、繼承關系、家庭關系及絕大多數刑事法律關系的法律調整任務,在很多方面起到了國家法律難以起到的作用。[6]馮爾康認為,清代紳衿和富有的地主、商人成為宗族的掌握者,是清代宗族制民眾化之后的特點,因此導致宗族成為以官僚、紳矜、富有的地主和商人為主體的社會組織。[7]從清代宗族法對契約法的影響來看,受宗族內部財產關系與其他宗族、社會習慣法及國家法之間相互作用的影響,契約法形成的相關特殊規則,更具有趨近于市場化的傾向。……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