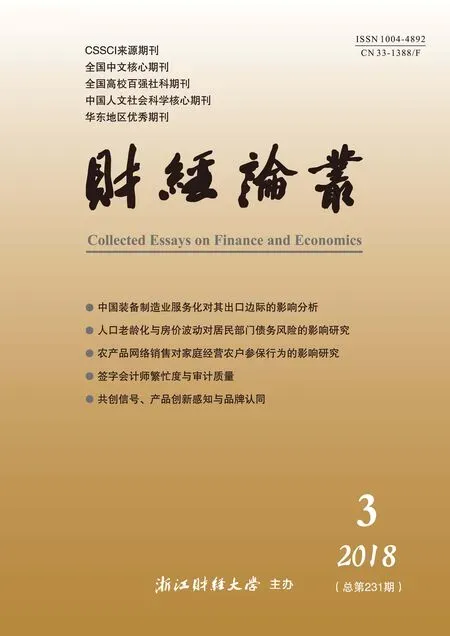人口老齡化與房價波動對居民部門債務風險的影響研究
童 偉,張居營
(中央財經大學財經研究院,北京 100081)
一、引 言
近些年來,我國居民部門的債務規模處于不斷攀升過程,表現在:杠桿率水平持續上升,由1997年的3%提高到2014年的36.4%,尤其是金融危機之后增速加快;消費信貸余額逐步增加,截至到2015年末余額為18.95萬億元,比1997年增加了18.93萬億元,年均增長速度為49.14%,也在2008年呈現增速加快的趨勢。但是,與政府部門、非金融企業部門等相比,我國居民部門杠桿率處于較低水平,據社科院估算,截至2014年末,我國居民杠桿率為36.4%,政府、非金融機構、金融部門杠桿率分別為57.8%、123.1%、18.4%,部門總計債務占GDP比重,即全社會杠桿率為235.7%。從各部門的縱向對比來看,居民部門債務杠桿率較低且遠低于政府部門及非金融企業部門杠桿率,僅占我國總債務水平的15%左右。從全球橫向對比的角度來看,中國居民部門的債務杠桿率同樣處于比較低的絕對水平,遠低于美歐日等發達國家。2014年美國居民債務占GDP的比重高達77%,其他發達國家杠桿率也多高于50%。
我國居民部門由于杠桿率較低,就存在著一定的加杠桿空間,可通過居民舉債消費以實現擴內需以及與企業、地方政府部門的債務對沖,從現實的情況看,我國政府也在嘗試通過去庫存、城鎮化等路徑進行國民經濟的去杠桿化。然則從長期看,人口老齡化又是我國經濟持續增長所不得不面臨的一大問題,它不僅會改變我國增長動力、產業結構等,人口結構的變化將會改變整個居民部門的消費、儲蓄傾向,對于我國居民部門的資產負債表情況產生巨大影響,甚至帶來潛在風險。同時,居民部門的凈資產又是宏觀經濟的一道重要“護城河”,特別是在經濟危機時期表現的尤為明顯。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就源于家庭資產負債表的惡化,導致家庭儲蓄、收入等無法抵消過重的房產信貸,爆發金融危機。因此,在現階段重視非金融企業、地方政府資產債務問題,也要從長期角度關注居民部門資產負債問題,尋找去杠桿下居民部門債務對沖的有效空間。
二、基本事實和文獻研究
(一)基本事實
在我國老齡化趨勢逐步明顯的情況下,人口年齡結構的新變化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如何?這種影響又會對居民部門債務帶來什么樣的沖擊呢?通過下邊的基本事實與文獻研究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
1.我國居民部門的資產債務結構。從負債結構來看,居民部門的全部金融債務都是貸款,沒有債券,且以住房貸款為主的中長期消費性貸款在居民貸款的占一半以上。據中國人民銀行的《金融機構本外幣信貸收支表》中住戶貸款的統計,2004年來,我國居民部門貸款額呈顯著增長態勢,住戶部門的總貸款中消費性貸款始終占65%以上,且消費性貸款中占比最大的以住房貸款為主的中長期貸款占總貸款的一半以上,2013、2014年來該比重雖微微下滑到51.97%、52.36%(因汽車貸款和信用卡貸款等新型消費貸款產品的增長),但2015、2016年由于房地產市場的再度繁榮,其中長期貸款占比又攀升到51.97%、52.36%,導致消費性貸款占總的住戶貸款比重也上升到70%以上,這從側面說明了房地產市場對居民部門貸款的影響。同時,房地產已經成為居民家庭重要財產,居民部門對房地產的需求帶動了部門負債的擴張。這點從居民部門的資產結構也能看出來,2004年至2014年,房地產在總資產、非金融資產中的占比均保持在50%以上和90%以上的水平,可見房地產始終是居民最重要的資產項目。居民部門房地產資產配置占比較高導致資產配置上存在一定的資產錯配風險。一旦房價下跌,居民資產大幅縮水,甚至無法沖抵住房貸款,居民的住房貸款償還壓力加大,違約率增加,居民部門債務風險凸顯。
2.我國人口老齡化與房地產的現狀。我國于上世紀80年代左右實行嚴格的計劃生育,導致人口生育率快速下降,經過長期影響人口年齡結構的拐點逐漸形成,人口老齡化趨勢也愈來愈明顯。1982~2014年,我國老年撫養比由8.0%至上升13.7%,特別是2000年以來上升趨勢明顯,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的峰值在2010年達到74.5%的高點,到2013年這一占比已經降至72.8%(圖1)。與此同時,我國房地產市場也在1998年的住房改革之后開始了新一輪的發展征程,尤其是進入21世紀之后,在土地國有化與財政支持下地方政府大規模基建與城市規劃,加之人口紅利帶來大量的住房需求,房地產價格突飛猛進,2000年~2014年全國商品房平均銷售價格由2112元/平方米上漲至6324元/平方米,增幅達到了1.99倍(圖2)。但是當上世紀50、60年代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的那批人已基本邁入老年,80年代左右的嬰兒潮到2013年大多結婚生子,這一批人員的住房需求基本滿足之后,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導致房地產的潛在需求也發生了變化。中國社科院發布的2016年《社會藍皮書》中調查顯示,2015年受訪家庭居民住房自有率為95.4%,其中城鎮居民家庭住房自有率為91.2%,19.7%的家庭擁有兩套以上的住房。此外,從房地產投資數據可以看到,雖然近些年我國較為寬松的貨幣供應給房地產市場帶來了更多的投機因素,導致房價仍然較為堅挺,但是從房價增速、房地產投資增速的數據來看,增速已有大幅度下降(見圖2)。在2010年房地產投資增速達到頂點33%,此后增速不斷下滑,并且這一拐點與勞動年齡人口占比的拐點重合,而房價增速的拐點也在這幾年間,在某種程度上表明了人口周期與房地產周期的一致性。

圖1 我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

圖2 我國房地產市場的變化情況
(二)文獻研究
目前關于人口老齡化與居民部門債務或家庭債務的研究并不多,更多的研究是從人口老齡化與房地產價格、房地產價格與居民債務等兩兩之間關系的視角分析的。
1.人口老齡化與房價關系的文獻研究。著名的美國經濟學家Mankiw和Weil(1989)[1]就從住房需求角度研究了人口年齡結構對住房價格的影響。他們運用生命周期理論從資產需求方進行分析,認為老年人口的收入和儲蓄都少于中青年,因而老齡化的加劇會造成對住房等資產需求的降低,從而房價下跌[1]。兩位學者在研究中還對美國1998~2007年的房價進行預測,認為房價在這一時期會下降47%,而事實確是美國房價不降反升,且上漲了30%。Levin et.al(2009)在此基礎上對收入、利率等相關的變量控制之后發現,人口老齡化確實會造成房價下行壓力[2]。除此之外,也有學者從平滑消費-儲蓄角度對人口年齡結構與住房價格進行分析,他們認為個體的消費-儲蓄行為會隨年齡產生變化,老年人口的消費大與儲蓄,會選擇出售資產,此時房屋等資產會由于超額供給而價格下跌,甚至出現方式崩潰(Modigliani,1966)[3]。國內方面,王勤和蔣旻(2011)認為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導致未來適齡購買人口的減少,促使國內住房價格在2018年左右出現拐點逐步回落,可能會長期處于低迷[4]。鄒瑾(2014)采用面板協整檢驗證明了人口年齡結構是房價波動的長期因素,老齡化曾經對房價上漲起到推動作用,但從中長期來看,其趨勢可能發生逆轉,即老齡化可能對房價產生負面影響[5]。郭娜等(2015)也認為人口年齡結構是影響住房價格變動的重要因素,認為人口數量的增長會推動房價上漲,而老齡化的加劇則減弱這種正向影響而使房價下跌[6]。
上述研究均說明了人口年齡結構會導致房地產價格的下跌,但是仍存在一定爭議,部分學者則認為經濟自身機制的調節作用會緩沖老齡化對房價的沖擊作用,比如經濟增長、城鎮化等因素,Farkas(2011)研究表明,人口老齡化會對房價造成負面沖擊,而經濟增長對房價有正向作用,因而在短期內老齡化對房價的沖擊作用無法顯現[7]。陳彥斌等(2013)對中國城鎮住房需求進行估算,發現由于城鎮化和家庭規模小型化的影響,老齡化對住房需求的負面沖擊作用要到2045年左右顯現出來[8]。總的來看,大量研究基本證明了人口年齡結構是影響房地產價格的重要因素,而對于具體的影響方向雖然仍存在爭議,但這種爭議大多體現在短期中老齡化對房價的影響,而中長期考慮各種控制變量之后,人口老齡化的加劇或者說老年撫養比的加大對住房價格的負向沖擊作用會逐漸顯現出來。
2.房價與居民部門債務風險關系的文獻研究。房價與居民部門債務關系的闡述最早來自于Fisher(1933)的“債務通縮理論”,其中債務危機產生的一個環節就是外界對經濟體的負面沖擊導致信貸市場收縮,債務人通過資產清算來減少債務存量,這種清算會導致資產價格下跌,又進一步加大債務人的債務壓力,引發又一輪的資產變賣、價格下跌,陷入“債務通縮螺旋”,這里的資產價格就包括房地產價格,債務人則是企業和家庭為主的私人部門[9]。Mishkin(1977,1978)通過研究驗證了1930年的大蕭條與1973年的經濟衰退中,資產價格下跌與家庭的資產負債表連鎖變化導致了經濟危機的產生[10]。Borio&McGuire(2004)、Girouard et al.(2006)認為債務會提高家庭對資產價格尤其是房產價格的敏感性。同等幅度的房價下跌,杠桿越高的家庭,凈資產的減少幅度會越大,家庭的抗風險能力也越低[11][12]。Aoki et al. (2004)、Iacovieilo(2005)從金融加速器的角度構建不同模型分析住房價格沖擊下住房資產的抵押物效應,認為住房價格波動將改變家庭的抵押物頭寸,從而改變抵押貸款規模以及貸款成本,加大住房價格沖擊對家庭債務的影響[13][14]。Moore&Palumbo(2010)等從家庭金融脆弱性的角度,認為高杠桿率或債務規模較高的家庭對利率、住房價格、失業率等更為敏感,更易受利率和資產價格沖擊的不利變化影響而變得脆弱[15]。由于我國居民部門債務水平相對較低,且房地產市場發展較晚,國內對于房價與居民部門債務或家庭債務的研究較少,郭新華(2011)研究家庭債務、房價與家庭消費等因素的動態關聯關系,通過格蘭杰因果檢驗、VECM模型等認為,家庭債務和住房價格互為因果關系,兩者共同對家庭消費產生影響,但并沒有具體展開分析家庭債務和住房價格的關系[16]。唐文進、張坤(2013)通過VECM模型分析認為,房價主要通過抵押效應對家庭債務產生影響,房價上漲會導致房屋抵押價值上升,從而使住房者更容易獲得消費信貸,這種關系并不是直接通過個人住房按揭貸款的消費方式來發生作用的[17]。
在當前我國人口老齡化趨勢已經確立的條件下,有必要通過房地產市場的變化來討論我國居民部門債務的潛在風險,特別是居民部門“加杠桿”的戰略背景下。本文就以上述理論和實踐研究基礎,通過構建計量模型,利用相關宏觀經濟數據,檢驗人口老齡化、房價與居民部門債務的關系,為決策部門制定合理的經濟政策提供參考。
三、理論模型
本文首先采用世代交疊模型(OLG)的框架并借鑒傳統的“人口-資產泡沫模型”(Takats 2010)[18]來論證人口老齡化、房價變動與居民部門杠桿率的關系。OLG模型將將人的一生分為兩個時期:年輕期和年老期,年輕期個體通過勞動獲得收入,進行消費和儲蓄,并假設年輕個體具有居住和投資房地產的需求,在資金不足的條件下要通過銀行借貸*需要說明的是,傳統的世代交疊(OLG)模型,年輕人是儲蓄者,即資金的供給者,無法在初期就貸款買房。但OLG模型是總量分析,現實情況往往需要結構分析才能抓住問題的關鍵。一方面,銀行對外借貸的資金可以是之前的儲蓄積累或外資流入,另一方面,房地產價格上漲會導致其他資產的資金轉向房地產投資,因此,該假設符合現實經濟情況。來滿足需求,并假設每個個體向銀行貸款的額度有限;老年個體則主要利用年輕時的儲蓄及房地產投資盈余進行消費,且償還債務,其理論模型為:
(一)基準模型
根據OLG模型,代表性消費者一生的效用主要從中青年時期的消費以及其進入老年后的消費中得到滿足,因此效用函數為:
(1)

(2)
其中,rt分別表示t期利率。
在此,引入銀行信貸和房地產資產,假定在一定的利率水平rt下,年輕消費者會根據自己對房地產價格走勢的判斷,從銀行借貸購買房地產用于居住和投資,因此,式(2)可轉變為:
(3)
其中,pt、ht分別表示t期的房價以及年輕個體購買的房產數量,lt表示t期年輕個體向銀行貸款的最大額度,它可以決定個體購買房地產的數量,在理性人的假設條件下,個體為了追求資產最大化,一般會選擇最大貸款額。
(4)

(5)
該批年輕個體到t+1期則會變成老年個體,通過出售房地產來償還銀行借貸本息,剩余部分用于消費,即:
(6)
由式(6)可知,老年個體的消費與該個體年輕時的借貸及其購買房地產數量、房價漲幅有關。本文在這里還假設t期的人口增長速度為vt,經濟增速為gt,并根據經濟學常識認為經濟增速與人口增速、信貸增長率dt正相關,與人口撫養率λt負相關,即gt=gt(vt,λt,dt),由于各時期年輕個體是同質的,經濟增速與不同時期年輕人的收入增速相同,那么可以得到:
nt+1=nt(1+vt)yt+1=yt[1+gt(vt,λt,dt)]
(7)
(二)模型求解
基于消費者效用最大化以及預算約束,由式(1)、(3)整理可得:
(8)
將上式代入式(5),得到:
(9)
式(9)說明t期房價與該時期人口數量、人口結構、信貸規模、經濟水平相關,我們還可以看到房價越高,信貸規模就越大,將該推導邏輯擴展到t+1期,得到:
(10)
將式(7)代入式(10),可得:
(11)
式(11)除以式(9),就可以得到:
(12)
由式(12)可知,從t期到t+1期的房地產價格上漲速度pt+1/pt與人口增長速度vt、經濟增速為gt,信貸增長率dt正相關,與人口結構變化反向變化,若t+1期老年人口比例較大,導致人口撫養率增大,λt+1>λt,(1+λt)/(1+λt+1)就越小,且小于1,pt+1/pt就越小,說明人口老齡化使得房地產價格上漲速度減緩,甚至小于1,導致房價下跌。
(13)
由式(13)可知,若t期人口撫養率越大,會導致t+1期經濟增速gt變小,從而導致t+1期居民部門的杠桿率γt+1變大,這說明了人口老齡化可以通過減緩經濟增速,從而影響居民收入使得居民部門杠桿率增大。
命題:從當期來看,t期房地產價格越高,居民部門信貸規模也越高,短期內房價漲跌與居民部門的杠桿率增減難以顯現出來;當擴展到t+1期,人口老齡化導致人口撫養率的增加,會使得房地產價格上漲速度減緩,甚至導致房價下跌,同時人口老齡化引起國民經濟增速下滑,一方面也會導致房價增速減緩,另一方面會導致居民杠桿率加大,因此,從長期來看,人口老齡化對居民杠桿率提升的潛在影響較大。
四、實證分析
(一)變量選擇和數據說明
由于本文研究居民部門債務風險,且前文分析中居民債務風險也包含了居民房地產資產縮水給總債務帶來的風險,故本文采用居民房產負債率(房地產債務/房地產資產)而非居民部門債務規模來衡量居民部門債務風險。且考慮到數據的可獲性,居民房產負債率中的房地產債務以個人購房貸款余額(單位:億元)來代替,而房地產資產則以商品銷售額中住宅、別墅、高檔公寓銷售額等個人購買商品房代替;房價用商品房平均銷售價格(單位:元/每平方米)衡量,為消除構建模型時消除異方差的影響以及實現綱量一致,對數據進行了對數化處理;人口老齡化水平則采用老年撫養比(%)作為衡量指標。
本文選取1997~2015年為樣本期。樣本期中的商品房銷售價格、老年撫養比(%)及住宅、別墅、高檔公寓銷售額均由歷年《中國統計年鑒》的相關統計數據整理而得;個人購房貸款余額數據由歷年《金融統計數據報告》、wind資訊整理而得;本文采用eviews6.0軟件,將年度數據轉化為季度數據。
(二)模型建立
本文首先采用協整分析考察我國人口老齡化與房價、房價與居民債務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并建立三者間的長期均衡方程如下:
DEBT=β1+β2LNPRIC+β3OLD+εt
(14)
其中,β1為常數,β2,β3分別為房價水平、老齡化水平對居民部門債務的影響系數,εt為殘差項。
為研究人口老齡化與房價、房價與居民債務之間的短期波動,構建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模型)如下:
(15)

(三)單位根檢驗
本文所選取的數據均是經過季度化的時間序列數據,為避免“偽回歸”造成的結果無效,運用ADF法對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ADF結果見表2。

表2 ADF單位根檢驗結果
注:表中的Δ2表示二階差分;檢驗形式三項分別表示常數項、趨勢項和滯后階數項。
從表2可看出,DEBT、LNPRIC、OLD這三個變量的ADF統計量均大于各顯著水平臨界值,表明居民債務、房價、老齡化水平的原序列數據都是不平穩的。而經過二階差分后,三個時間序列都為平穩序列。因此,居民債務、房價、老齡化水平二階單整,可進行協整分析。
(四)協整檢驗
根據式(1)構建的計量模型,采用E-G兩步法檢驗DEBT、LNPRIC、OLD三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首先運用最小二乘法對三變量進行回歸,結果如下:
DEBT= 3.437-1.305×LNPRIC+0.769×OLD
(16)
(1.69) (-2.81) (4.55)
對(16)式保留參數序列ECM,并對殘差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顯示,殘差序列的ADF統計量為-2.806,小于1%臨界值(-2.600),因而殘差序列ECM在1%顯著性水平下平穩,因而,居民債務、房價、老齡化水平三變量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式(16))。從長期來看,老年撫養比和房價對居民房產負債率的影響方向相反,且房價對居民房產負債率的影響大于老年撫養比對居民房產負債率的影響。具體來看,老年撫養比上升一單位會引起居民房產負債率0.769單位的上升,說明隨著老齡化的加劇居民部門債務風險會加大。而房價下滑一個百分點會導致房產負債率1.305單位的提高,說明房價下跌會提高負債率,增加負債風險。
實證結果表明房價與居民房產負債率負相關,這表明,由于我國居民部門在房地產資產的配置上占比較高,導致了一旦房價下跌,居民資產就會大幅縮水,住房貸款償還壓力加大,違約率增加,從而加大了居民部門債務風險,即房價的下跌會增大居民部門債務風險。而老年撫養比與居民房產負債率呈正相關關系,說明老口老齡化加劇會通過減少對住房等資產的需求引致房價下跌,最終加大居民部門債務風險。
(五)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
由協整檢驗可知居民債務、房價、老齡化水平三變量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但無法得知居民債務偏離其長期均衡趨勢時的調整速度,因此建立VEC模型考察變量間的短期偏離修正機制,最終檢驗結果如下:

以上VEC模型反映了居民部門債務、房價及老齡化水平間的短期波動關系,該波動不僅受到誤差項(短期偏離均衡)的影響,還受住房負債率、房價、老年撫養比自身變動的影響。
具體來看,在居民房產負債率的VEC模型中,誤差修正項系數為-0.046039,負值符合反向修正機制,反映了當居民債務短期波動偏離長期均衡時,三變量間的動態關系將以-0.04的調整力度將非均衡狀態拉到均衡狀態。滯后1期、2期、4期的老年撫養比對居民房產負債率的影響為正,與長期影響趨勢保持一致,但系數小于長期均衡時的影響系數,體現了人口老齡化的加劇會加大居民部門債務風險,但短期內的影響并沒有長期顯著,其原因可能是老齡化過程本身也是一個較為緩慢的趨勢,對居民負債的影響存在滯后性。而滯后1到4期的房價對居民房產負債的影響為正,彈性系數分別為1.108004、0.449734、0.321264、0.731510,均與長期(-1.305)相反且絕對值也低于長期的絕對值,說明房價降低對居民部門負債風險的加劇效應并不會在短期內顯現出來,也沒有長期效應顯著。在房價和老年撫養比的誤差修正模型中,誤差修正項的系數分別為0.026375、0.010713,均為正,不符合負的反饋機制,因而無法將短期波動拉回到長期均衡狀態。
進一步地,基于VEC模型的脈沖響應分析,脈沖響應設定為15年,本文主要研究人口老齡化、房地產價格對居民部門債務的動態響應,因此只給出兩個圖示,如圖3、圖4所示:
由圖3可看出,在受到老齡化水平正向沖擊后,沖擊效應為正,從第二年期逐年上升并在第9年達到最高值之后逐漸下降但沖擊效應依然為正。 這與我們前面VEC模型結果一致,即人口老齡化水平對居民負債影響為正,但短期內的影響并沒有長期顯著。

圖3 居民部門債務受到老齡化的脈沖響應

圖4 居民部門債務受到房價的脈沖響應
由圖4可看出,居民部門債務受到1單位正向標準差的房價沖擊后,沖擊效應在前5年基本為正,但這種正向沖擊效應并不顯著,說明房價的下跌在短期內對居民部門沖擊并不明顯。從第6年期,沖擊效應表現為負,體現了房價對居民部門債務的負向沖擊作用在較長時期才能顯現出來,由于之前的VEC模型并不能展示較長滯后期的變化,因而這種負向沖擊并未在模型結果顯示,但脈沖響應可以明確看出房價對居民部門債務的反向沖擊效應,即房價的下跌會加重居民部門的債務風險。
五、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選取1997~2015年中國居民部門債務、房價、人口老齡化的相關統計數據,采用協整檢驗、構建誤差修正模型等方法考察了人口老齡化、房價、居民部門債務三者間的長、短期關系,得到以下結論:(1)從長期來看,居民部門債務、房價、人口老齡化三者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老齡化的加劇會加大居民部門債務風險,房價下跌會提高負債率,增加居民負債風險。從影響效應來看,房價對居民債務影響大于人口老齡化對居民部門債務影響。(2)從短期來看,當居民債務短期波動偏離長期均衡時,三變量間的動態關系將以-0.04的調整力度將給均衡狀態拉到均衡狀態,短期內人口老齡化對居民房產負債率的影響為正,但不如長期影響顯著。而短期的房價對居民房產負債的影響也為正,體現了房價下跌對居民部門負債風險的加劇效應并不會在短期內顯現出來,但居民債務仍存在潛在風險。(3)居民部門債務的潛在風險受人口周期、房地產周期的影響,人口老齡化會通過改變房地產需求向居民債務沖擊,即人口老齡化加劇會通過降低房產需求從而使房價下跌的形式加大居民部門債務風險。
基于以上結論,提出以下建議:(1)為防止人口老齡化加劇對房地產市場可能帶來的沖擊,政府應注意對房地產市場的實時調控,根據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調整戰略并做好前瞻性監測與規劃并及時公布,以便公眾進行合理預期。以此同時,政府應做好老齡化所導致的房價波動應對機制,以沉著應對日益加劇的老齡化進程。(2)與政府部門、企業部門相比,居民部門雖存在一定的加杠桿空間,但從上分析可看出在人口老齡化加劇的背景下居民部門存在潛在債務風險,因而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必須遵循適度有序原則,審慎評估、謹慎推行居民部門加杠桿政策,并對可能出現的問題做好監測監控準備,盡量降低加杠桿對金融、經濟穩定帶來的影響。(3)針對居民部門資產配置中房地產占比過高的現狀,一方面要完善信用體系、法律體系、社會保障體系,積極推動資本市場建設、加強金融創新,使居民可資產進行有效的分散化多元化配置,另一方面,居民自身也應加強風險意識,樹立分散化多元化投資觀念,合理配置資產。
[1] Mankiw N. G.,Weil D. N. The Baby Boom,the Baby Bust,and the Housing Market[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1989,19(2): 235-258.
[2] Levin E., Montagnoli A., Wright R. E. Demographic Change and the Housing Market: Evidence from a Comparison of Scotland and England[J]. Urban Studies, 2009, 46(1):27-43.
[3] Modigliani, F. The Life Cycle Hypothesis of Saving, the Demand for Wealth and the Supply of Capital [ J]. Social Research,1966,33 (2 ) : 160-217.
[4] 王勤, 蔣旻. 人口年齡結構與住宅價格調控[J]. 上海金融,2011,(10):15-22.
[5] 鄒瑾. 人口老齡化與房價波動——來自中國的經驗證據[J]. 財經科學,2014,(6):115-124.
[6] 郭娜, 吳敬. 老齡化、城鎮化與我國房地產價格研究——基于面板平滑轉換模型的分析[J]. 當代經濟科學, 2015, (2):11-17.
[7] M. Farkas. Housing Demand and Demographic Trends: Evidence from Hungary [Z].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2011.
[8] 陳彥斌, 陳小亮. 人口老齡化對中國城鎮住房需求的影響[J]. 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 2013, 33(5):45-58.
[9] Fisher I. The Debt-Deflation Theory of Great Depressions[J]. Econometrica, 1933, 1(4):337-357.
[10] Mishkin F. S. The Household Balance Sheet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J].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78, 38(4):918-937.
[11] Borio C. E., Mcguire P. Twin Peaks in Equity and Housing Prices [J]. BIS Quarterly Review, 2004, (3):79-93.
[12] Girouard N., Kennedy M., Noord P. V. D., et al. Recent House Price Developments: The Role of Fundamentals[J]. Canadian Journa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2006, 80(3):465-471.
[13] Aoki K, Proudman J., Vlieghe G., et al. House Prices, Consumption, and Monetary Policy: A Financial Accelerator Approach[J].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2002, 13(4): 414-435.
[14] Iacoviello M. House Prices, Borrowing Constraints and Monetary Policy in the Business Cycle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5, 95(3): 739-764.
[15] Moore K. B., Palumbo M. G.. The Finances of American Households in the Past Three Recessions: Evidence from the 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 [J].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2010, (6): 7-24.
[16] 郭新華,何雅菲. 中國家庭債務、房價波動與居民消費的動態相關性分析[J]. 經濟經緯,2011, (1):9-13.
[17] 唐文進,張坤. 基于VEC模型的家庭債務、房價與消費的動態關系研究[J]. 統計與決策,2013, (15):108-110.
[18] Takats E. Ageing and Asset Prices[J].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2010, 68(318):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