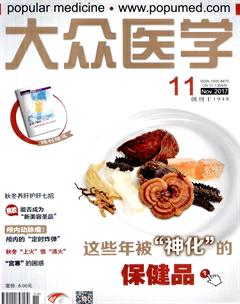從“腎”論治慢性乙肝 “七分”黃疸獨樹一幟
王靈臺
我出生于浙江鄞州的儒商之家,自幼對中華文化之博大精深頗有感悟,成年后喜愛京劇、書法、篆刻等,自幼便立下“不為良相,愿為良醫”之志,于1959年考入上海醫科大學(現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醫療系,1963年畢業后在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工作2年,后調至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曙光醫院工作至今。我雖初學西醫,半路皈依岐黃,但一貫主張“能為西醫之已為,善為西醫之所為,敢為西醫之不為”,提倡“中醫之未明處,西醫助之;西醫之未能處,中醫補之”,從事中西醫結合治療慢性肝病達五十余載。
從“腎”治“肝”,另辟蹊徑
在跟隨上海市名老中醫夏德馨教授臨診時,我從臨床實踐中深刻體會到,對慢性乙型肝炎的治療,若拘泥于清熱解毒等苦寒之法,難以取效,應當另辟蹊徑,尋覓新法。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除有濕熱癥狀外,尚有腎虛,間或有命門之火不足的表現。況且慢性乙型肝炎病情纏綿、病程較長,患者感染乙肝病毒曠日持久,必然暗耗腎精,即所謂“久病傷腎”之說。此外,本病多濕重熱微,濕為陰邪,易傷陽氣,輕則脾陽不運,重則脾陽不振,暫則脾病而已,久則腎陽亦虛,正所謂“濕久,脾陽消乏,腎陽亦憊”。因此,我認為慢性乙型肝炎的病機主要體現在腎精腎氣虧損,或命門之火不足,濕熱未盡,在全國率先提出以“補腎法為主治療慢性乙型肝炎”的創新理論,獲得同行廣泛認可。
根據益腎溫腎為主,清化濕熱為輔的治則來選方用藥,我擬定了補腎方治療慢性乙型肝炎,并申報院內制劑——巴菟補腎益肝沖劑,選用甘溫緩和的益腎溫腎類中藥,如巴戟天、仙靈脾、肉蓯蓉、菟絲子等,溫補命門而不熱,補益腎精而不峻,在補腎同時又可充實肝體,改善肝脾功能,使“命門火旺,蒸糟粕而化精微”,從而達到治療目的。經過長期的臨床驗證和實驗研究,證實補腎為主、清化為輔是治療慢性乙型肝炎的有效方法,為中醫藥治療慢性乙型肝炎開辟了一條新途徑。
“七分”黃疸,獨樹一幟
黃疸是臨床常見病癥,以目黃、身黃、小便黃為主癥。中醫學關于黃疸的論述由來已久,早在《黃帝內經》時期就對其進行了詳細的論述,歷代醫家對黃疸的病因病機、證治方藥的認識也不斷深入。我翻閱大量醫典醫案,總結名家經驗后認為,黃疸的病因不外“濕、熱、毒、瘀、虛”五端,且多兼癥。“陽黃”與“陰黃”不能函括黃疸病證的全部內容,需要更加細化的分類辨治。
2004年4月,我首次提出“介黃”之說,認為陽黃與陰黃不能包括黃疸病證的全部內容,臨床所見“似陽似陰”“非陽非陰”的黃疸患者,從辨證角度難以截然分類。究其根源,可能包含陽黃陰黃之病因病機,且按陽黃或陰黃論治亦難奏效,此乃陽黃與陰黃之間特殊的病理階段,我將其命名為“介黃”,其本質是從陽黃到陰黃演變過程中的一個特殊的病理階段,即具有陽黃與陰黃二者的病因病機和證候的多種特征,但又不能全部或完全歸于陽黃或陰黃。經過數十年的臨床總結和提煉,我提出了黃疸七分類的辨證論治方案,即陽黃、陰黃、介黃、惡(急)黃、稽黃、塞黃、虛黃7種分類。
黃疸的治療應法取仲景,同時結合歷代名家經驗和論著,多法并用。外感傷寒之黃多熱,內傷雜病之黃多濕;得之外感者,不可用補法;得之內傷者,不可用攻法。治則治法當取“盛則瀉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切忌大汗大下、溫補燥熱、破氣閉氣,陰黃誤用陽治或濫用苦寒之藥。半陰半陽之證,必先退陰復陽,陰退乃從陽治。黃疸日久者需循扶正祛邪之則,諸癥不離脾胃。同時要遵尋關幼波老先生的經驗,即“治黃必治血,血行黃易卻,治黃需解毒,毒解黃易除,治黃要治痰,痰化黃易散”。黃疸均需從肝論治,注意肝臟的生理特性,以保護、促進肝臟功能為主,扶正祛邪當為治“黃”大法。此外,尤應注重藥物的炮制及煎煮方法對臨床療效的影響。
外治論肝,舒肝消脹
慢性肝病的常見癥狀多為肋脅疼痛、腹痛腹脹,多因情志抑郁,或暴怒傷肝,而使肝失調達、疏泄不利;氣郁日久,血流不暢,逐漸積滯而成瘀血,氣血運行不暢,導致肋脅疼痛、腹痛腹脹。我在臨床發現,理氣、活血之法對病程短的急慢性肝病脅痛、腹脹者均有明顯治療效果。而病程超過半年以上的慢性肝病脅痛、腹脹者,則不宜應用理氣活血之法,不僅止痛消脹效果欠佳,還可引起其他不良反應。因此,我認為慢性肝病患者脅痛、腹痛的基本病機是:“虛”以氣虛為主,“實”為氣滯血瘀,氣虛不能行血,脈絡瘀阻。治則當以益氣通絡、活血化瘀、行氣止痛為治,不應再拘泥于理氣、活血通絡法。
在臨床治療中,得到“外治之理即內治之理,外治之藥,亦即內治之藥”的啟示,我將傳統經絡學說和現代透皮吸收制劑的優勢結合起來,將現代透皮給藥與穴位功能結合起來,研制成功了治療慢性肝病脅肋疼痛的中藥穴位敷貼透皮劑“肝舒貼”以及治療肝硬化腹水的中藥穴位敷貼透皮劑“消脹貼”,使中藥之性達疾病之所而發揮最佳治療作用。目前,肝舒貼和消脹貼已進行二次開發,廣泛應用于慢性肝病伴脅痛、腹脹患者,具有顯著療效。
民族醫藥,協調發展
2015年11月,我當選為中國民族醫藥學會肝病分會會長。近2年來,在中國民族醫藥學會領導下,我與肝病分會同仁開展了民族醫藥論治慢性肝病的有益探索。
作為肝病分會會長,我重點開展了編撰民族醫藥防治慢性肝病知識手冊,發掘防治肝病的民族特色藥物和診療技術,系統挖掘近10年來具有確切療效的防治肝病的民族特色醫藥和技術方法,共同解決民族醫藥整理和發掘中碰到的難題和瓶頸,促進中醫藥、民族醫藥防治慢性肝病的理論知識和學術經驗的協同發展。
我從事中西醫結合防治慢性肝病臨床和基礎研究工作五十余載,取得了一些成績。回顧既往工作經歷,撰以詩文而自勉。
懸壺半生暮回憶,俯仰無愧憑戒欺,
一心皈依岐黃門,自恃守中亦知西。
矢志之途尚依稀,路遙何懼重攀躋,
真如佛云有來世,續修正果再為醫。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