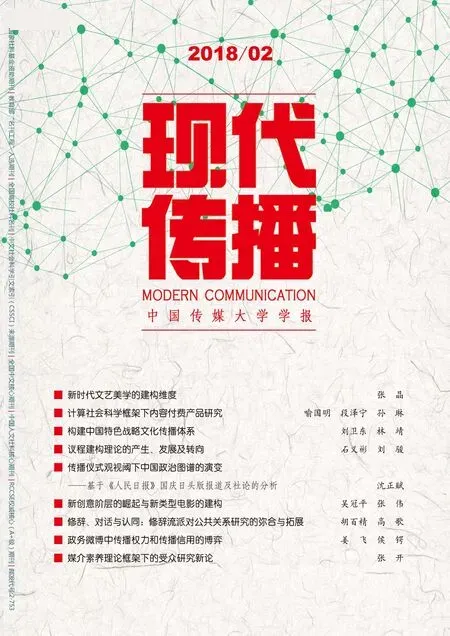新創(chuàng)意階層的崛起與新類型電影的建構(gòu)
■ 吳冠平 張 偉
美國教授理查德·佛羅里達寫過一本題目很“燃”的書——《創(chuàng)意階層的崛起》。該書對一個新的社會階層——創(chuàng)意階層的出現(xiàn),如何改變我們的工作、休閑娛樂和群體交往,如何創(chuàng)造城市的新未來,進行了富有洞見的描述。在他看來:“資本主義也擴充了對人才的定義,開始招攬那些曾經(jīng)被排斥的具有古怪思想的人和喜歡標新立異的人,通過這種方式,實現(xiàn)另一項令人吃驚的突變:讓放蕩不羈的、波西米亞風(fēng)格的怪才去主導(dǎo)創(chuàng)意和經(jīng)濟的增長……創(chuàng)意人士不再被視為對傳統(tǒng)的破壞者,而是成為新的社會主流。”①美國教授的觀察無法一一對應(yīng)中國的現(xiàn)實,但他的描述讓我們可以從一個新的維度,理解當(dāng)下中國電影新一代的創(chuàng)作者和觀眾。
本文中,電影主要還是被當(dāng)作一種文化,并且文化形成的面貌是一個過程的結(jié)果。即群體在這個過程中理解自身的世界,并且在持續(xù)不斷地造就群體成員之間理解自身和他人行為的意義網(wǎng)絡(luò)。當(dāng)下中國電影正在形成這樣的意義網(wǎng)絡(luò),它是由新成員、新規(guī)則和新關(guān)系造就的新時代的電影文化。
一
中國新創(chuàng)意階層的逐步形成與中國城市化的進程,以及城市化帶來的新的生產(chǎn)方式和技術(shù)革新密不可分。那些新的生產(chǎn)方式和新的技術(shù)改變了人口的知識體系,創(chuàng)造出新的職業(yè),新的服務(wù)和消費方式。
1994年中國的城市化率只有28.62%,到了2004年,上升到41.76%,2011年達到了51.27%,2017年的城市化率已經(jīng)高達57.35%,超過了亞洲城市化率的平均水平②。北上廣深等大城市的城市化率都在80%以上。1994年,中國大學(xué)的錄取率是36%,到2014年達到74.3%。1994年,中國大學(xué)畢業(yè)生人數(shù)大約為63.7萬人,到2016年達到704.2萬人。1994年,每十萬人口高校平均在校生數(shù)為433人,到2016年為2530人。③城市化的進程和人口教育程度的提高,也改變了人口的就業(yè)結(jié)構(gòu)。“城鎮(zhèn)就業(yè)比重正在上升,非農(nóng)產(chǎn)業(yè)就業(yè)比重也在上升。正規(guī)部門正在從部分行業(yè)中逐漸退出,非正規(guī)就業(yè)比重相應(yīng)上升。在正規(guī)部門中傳統(tǒng)正規(guī)部門就業(yè)人數(shù)顯著下降,新興正規(guī)部門就業(yè)人數(shù)迅速上升。”④據(jù)國家統(tǒng)計局數(shù)字,2004年城鎮(zhèn)就業(yè)人口2.73億,鄉(xiāng)村就業(yè)人口4.70億;到2016年,城鎮(zhèn)就業(yè)人口4.14億,鄉(xiāng)村就業(yè)人口3.62億。⑤2016年,在國有單位就業(yè)的大約6169.8萬人,而在私營和個體單位就業(yè)的大約有3.09億。⑥并且,從業(yè)人員“增幅超過200%的行業(yè)有建筑業(yè)、租賃和商務(wù)服務(wù)業(yè);增幅超過100%的行業(yè)包括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wù)和軟件業(yè)、批發(fā)和零售業(yè)、住宿和餐飲業(yè)、房地產(chǎn)業(yè)和居民服務(wù)業(yè);增速超過 50%的行業(yè)包括制造業(yè)、金融業(yè)、科學(xué)研究、技術(shù)服務(wù)和地質(zhì)勘查業(yè)、衛(wèi)生、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業(yè)。而采礦業(yè)、教育、文化、體育和娛樂業(yè)等行業(yè)門類從業(yè)人員數(shù)量增速不到 30%……房地產(chǎn)相關(guān)產(chǎn)業(yè)、IT、批發(fā)零售、住宿餐飲、租賃與商務(wù)服務(wù)等服務(wù)產(chǎn)業(yè)高速發(fā)展”⑦。2016年,第三產(chǎn)業(yè)(也包括被稱為第四產(chǎn)業(yè)的信息產(chǎn)業(yè)或知識產(chǎn)業(yè))的就業(yè)人口占整體就業(yè)人口的 43.5%。
理查德·佛羅里達教授在談到支撐創(chuàng)意階層崛起的創(chuàng)意社會結(jié)構(gòu)時,給出了三個必要的構(gòu)成條件:“(1)技術(shù)創(chuàng)新與創(chuàng)業(yè)活動的新體系;(2)新穎高效的生產(chǎn)和服務(wù)模式;(3)推動各種創(chuàng)意活動的寬松的社會、文化與地域環(huán)境。”⑧
佛羅里達教授的判斷很大程度上得自于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世界進入新經(jīng)濟時代,一體化、信息化和知識化為全球經(jīng)濟活動帶來的新變化。事實上,中國為應(yīng)對世界經(jīng)濟潮流發(fā)生的變化,特別是在加入WTO之后,分階段有步驟地實行了國有經(jīng)濟體制的改革,調(diào)整第一、二、三產(chǎn)業(yè)在國民經(jīng)濟中的比重,加快城鎮(zhèn)化建設(shè)。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加快發(fā)展文化產(chǎn)業(yè),推動文化產(chǎn)業(yè)成為國民經(jīng)濟支柱性產(chǎn)業(yè)的國家戰(zhàn)略;進而2015年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大眾創(chuàng)業(yè),萬眾創(chuàng)新”,并把“互聯(lián)網(wǎng)+”作為推動創(chuàng)新的引擎。這些無疑為中國新創(chuàng)意階層的崛起創(chuàng)造了適應(yīng)的社會文化氛圍和新創(chuàng)業(yè)活動所需的條件。
據(jù) 2017 年8月中國互聯(lián)網(wǎng)絡(luò)信息中心(CNNIC)發(fā)布的《第40次中國互聯(lián)網(wǎng)絡(luò)發(fā)展?fàn)顩r統(tǒng)計報告》顯示,截至 2017 年 6 月,中國網(wǎng)民規(guī)模達7.51 億,互聯(lián)網(wǎng)普及率為 54.3%。網(wǎng)民以10~39歲群體為主,占整體72.1% 。其中,20~29歲年齡段網(wǎng)民占比最高,達 29.7%,10~19 歲、30~39歲群體占比分別為 19.4%、23%。網(wǎng)民以中等學(xué)歷群體為主,初中、高中/中專/技校學(xué)歷的網(wǎng)民占比分別為37.9%、25.5%。網(wǎng)民中學(xué)生群體占比最高,為 24.8%;其次為個體戶/自由職業(yè)者,比例為20.9%;企業(yè)/公司的管理人員和一般職員占比合計達到15.1%。網(wǎng)民中月收入在 2001~3000元及3001~5000元的群體占比較高,分別為15.8%和22.9%。
而2016年的電影觀眾分年齡段調(diào)查結(jié)果顯示,19~30歲是觀眾最主要構(gòu)成,占比達到75.70%。其中,19~22歲觀眾占了22.30%,23~25歲的觀眾占23.70%,26~30歲的觀眾占29.70%,31~40歲觀眾占12.40%。觀眾中本科學(xué)歷占比最高達到46.30%,大專學(xué)歷占比26.60%,高中及以下學(xué)歷占22.60%,碩士及以上學(xué)歷占比4.5%。觀眾中月收入在3000元及以下的占比36.30%;3001~5000元的群體占比32.8%;5001~8000元的群體占比19.4%⑨。對比網(wǎng)民和電影觀眾主要數(shù)據(jù)會發(fā)現(xiàn):網(wǎng)民與電影觀眾在年齡、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上,有很大重合度。
曾任優(yōu)酷土豆集團高級副總裁的朱輝龍先生提供了這樣一組數(shù)據(jù),在中國,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用戶占到互聯(lián)網(wǎng)用戶的80%,這個比例估計是全世界最高的,接近5億是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用戶。而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爆發(fā)是從2011年開始的,安卓智能手機降到1000元以內(nèi),這使智能手機在二三線城市有了爆發(fā)式增長。很多二三四線城市的年輕人無時不在網(wǎng)絡(luò)上。2013年中國電影票房一線城市占40%,二線城市漲了46%,三四線城市漲了91%。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直接拉高了二三線城市的票房。⑩這里可以再補充一些數(shù)據(jù)。2009年7月,中國進入3G手機的時代,2012年3G手機的用戶達到1億人。只用了4年,2013年中國進入了4G手機時代。截至 2017 年 6 月,中國手機網(wǎng)民規(guī)模達 7.24 億,網(wǎng)民中使用手機上網(wǎng)人群占比為96.3%。年輕的知識階層成為網(wǎng)絡(luò)和新媒體最忠實的伙伴。事實上,中國互聯(lián)網(wǎng)最早的用戶正是活躍在清華大學(xué)、北京大學(xué)等高校校園BBS中的大學(xué)生群體。網(wǎng)絡(luò)和新媒體不僅為創(chuàng)意階層提供了更靈活、更包容、更開放的創(chuàng)意空間,也讓城市中年輕的知識階層領(lǐng)受到更便利、更多元化的創(chuàng)意服務(wù)。
從圖1我們可以看到,2005年中國網(wǎng)絡(luò)用戶突破1億。從2005年到2012年是中國網(wǎng)絡(luò)用戶增長最快的階段,七年增長了近四倍。對照圖2,中國觀眾的觀影人次2012到2016是增長最快的五年。兩相比照,我們是否可以得出一個初步的判斷:當(dāng)網(wǎng)絡(luò)的人氣和活躍度達到相對飽和的時候,網(wǎng)絡(luò)用戶在特定網(wǎng)絡(luò)內(nèi)容的影視轉(zhuǎn)換中會成為拉動票房的觀影人群,且數(shù)量龐大。

圖1 1995—2015中國網(wǎng)絡(luò)用戶數(shù)量統(tǒng)計表

圖2 2005—2016年中國電影年度觀影人次統(tǒng)計表
近十年來,一個顯見的事實是,跨界創(chuàng)作已然不新鮮。作家、歌手、主持人、演員、影評人的跨界電影自不必說,有其與影視天然的親緣性。而有一批創(chuàng)作者則是從非藝術(shù)領(lǐng)域轉(zhuǎn)換跑道進入影視創(chuàng)作界。《盜墓筆記》的編劇南派三叔(本名徐磊)。他最早是外貿(mào)公司職員,做過廣告美工、軟件編程、國際貿(mào)易等諸多行業(yè)。2006年開始在網(wǎng)上進行文學(xué)創(chuàng)作,寫出了《盜墓筆記》系列。《鬼吹燈》的編劇天下霸唱只有初中畢業(yè)文憑,一開始在天津洗盤子,后來跑到深圳一家合資企業(yè)打雜工,一邊打工一邊念了個專升本的文憑,去電視臺做了美工。再后來自己做服裝生意、美容院,各種各樣生意,還和一幫朋友回天津開了家金融公司。2006年在起點中文網(wǎng)發(fā)表《鬼吹燈》,之后人氣攀升成為重要的網(wǎng)絡(luò)寫手和編劇。編劇辛夷塢2004年大學(xué)畢業(yè)后進入南寧電力公司從事文秘工作。2007年4月連載現(xiàn)代言情小說《致我們終將腐朽的青春》獲得廣泛關(guān)注,2007年7月更名為《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出版。2008年,辛夷塢辭去文秘工作開始專職寫作。這些“外來者”給影視圈的創(chuàng)作帶來了奇特的、充滿差異性、魅力與不適感交疊的“異域風(fēng)情”作品。界墻的拆除,以及對于跨界一代命名的尷尬,在另一個維度上表明了新創(chuàng)意階層在中國影視產(chǎn)業(yè)中漸成氣候,并在價值觀上表現(xiàn)出傳統(tǒng)電影意義網(wǎng)絡(luò)中不曾有過的多樣性。
2012年10月,盛大文學(xué)以“文學(xué)改編影視的第二次浪潮”為名,在北京召開論壇。根據(jù)盛大文學(xué)公布的數(shù)據(jù),盛大文學(xué)2011年共售出版權(quán)作品651部,其中旗下七家文學(xué)網(wǎng)站影視改編售出74部(含晉江文學(xué)城)。而2012年1至9月份,盛大文學(xué)旗下七家文學(xué)網(wǎng)站就售出75部小說的影視版權(quán)。截至2014 年底,已有114部網(wǎng)絡(luò)小說被購買影視版權(quán)。近五年來許多人氣賣座電影,如《失戀33天》(2011)、《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2013)、《匆匆那年》(2014)、《左耳》(2014)、《尋龍訣》(2015)、《何以笙簫默》(2015)、《盜墓筆記》(2016)、《微微一笑很傾城》(2016)、《從你的全世界路過》(2016)、《擺渡人》(2016),都出身于2006到2011年間的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作品。
華誼兄弟董事長王中軍在2015 中國(深圳)IT領(lǐng)袖峰會上曾說過這樣的話:“互聯(lián)網(wǎng)到底在電影上起到什么作用?BAT進入電影領(lǐng)域,帶來大量的資金、客戶和大量年輕人進入這個行業(yè)。但是,我們還沒有在電影圈兒內(nèi)看到類似 BAT一樣的大公司,包括互聯(lián)網(wǎng)公司怎么樣幫助這個行業(yè)創(chuàng)新……我們的電影行業(yè)不那么強大,中國 IT 行業(yè)創(chuàng)新精神很強,還有中國企業(yè)家的年輕化,以及中國企業(yè)家的通融程度。”顯然,技術(shù)創(chuàng)新帶來的創(chuàng)業(yè)活動的新體系正在改造電影產(chǎn)業(yè)的傳統(tǒng)與格局。
在資本層面,互聯(lián)網(wǎng)公司在2014年大舉進軍電影領(lǐng)域,三大巨頭“BAT(百度、阿里巴巴、騰訊)”紛紛出手。百度旗下的愛奇藝與華策影視共同出資,成立“華策愛奇藝影視公司”;阿里巴巴收購文化中國,更名為“阿里影業(yè)”,進軍制片業(yè);騰訊網(wǎng)成立了騰訊影業(yè)和企鵝影業(yè)兩家公司。其他視頻網(wǎng)站如樂視、優(yōu)酷土豆等亦均已參與多部電影的制作。
《中外企業(yè)文化》雜志上的一篇文章是這樣描述資本大鱷馬云的電影生意經(jīng):“馬云玩電影,除了在常規(guī)地帶縱橫捭闔外,更多的卡位布點均是傳統(tǒng)電影產(chǎn)業(yè)的薄弱環(huán)節(jié),如首開電影眾籌之先河的余額寶,推出O2O在線選座售票的淘寶電影,搭建特效渲染的視覺云,開發(fā)仍是處女地的電影衍生品等。而所有這些,都是基于嘗鮮動機的互聯(lián)網(wǎng)+思維,由此也形成了阿里巴巴電影王國特有的生態(tài)模式:在上游,阿里文學(xué)、知名導(dǎo)演與制作人聯(lián)袂進行IP內(nèi)容的推送,余額寶予以及時的資金跟進和襯托;在中游,阿里影業(yè)和光線傳媒順勢承接,借助視覺平臺Render cloud 實現(xiàn)低成本的拍攝制造;在下游,淘寶電影與粵科軟件組成的銷售前端完成線上線下院線的拓展以及衍生品的開發(fā)銷售;在外圍,阿里所擁有電商數(shù)據(jù),新浪微博等社交平臺數(shù)據(jù)直接強勢輔助和推動內(nèi)容以及營銷產(chǎn)品的反向定制。”上述信息在筆者撰文時已有變化,但我們依然可以從這些信息中看到資本利用互聯(lián)網(wǎng)與新媒體空間創(chuàng)造的新穎高效的生產(chǎn)和服務(wù)模式。
“網(wǎng)生代”的概念被電影理論批評界創(chuàng)造出來,用來描述新創(chuàng)意階層的某些特征。清華大學(xué)尹鴻教授對“網(wǎng)生代”的解釋是,網(wǎng)生的電影產(chǎn)品、網(wǎng)生的電影觀眾、網(wǎng)生的電影導(dǎo)演和網(wǎng)生的電影公司共同構(gòu)成了“網(wǎng)生代”。和以前電影的代際劃分不一樣,它不是時間化的,而是空間化的。“網(wǎng)生代”對電影產(chǎn)業(yè)的改變主要體現(xiàn)在五個方面:電影產(chǎn)品的網(wǎng)民化、電影生產(chǎn)的網(wǎng)絡(luò)化、電影營銷的社交化、電影文化的部落化,以及電影市場的多屏化。在尹鴻教授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到,新的創(chuàng)意階層在電影產(chǎn)業(yè)的不同領(lǐng)域,形成的新的具有經(jīng)濟驅(qū)動力的創(chuàng)意鏈條。
事實上,當(dāng)城市成為新型行業(yè)、知識產(chǎn)業(yè)(寫作、金融、IT、設(shè)計、演出……)的中心時,各種新的社會關(guān)系交織在一起,形成一個不同于傳統(tǒng)社會結(jié)構(gòu)的群體。新的年輕知識階層間的交流與碰撞是在一個更為活躍領(lǐng)域內(nèi)的,多樣、包容又獨立、開放的,被新經(jīng)濟驅(qū)動的情感分享與資源互動的體系。這正是新的創(chuàng)意階層所賴以存在的體系(韓寒、郭敬明小說改編的熱點影片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出版、時尚、金融領(lǐng)域的創(chuàng)意群體共同打造了這樣的跨界神話。他們的影片以及他們的導(dǎo)演身份并非是神話的重點,也未必可以給中國電影業(yè)提供可復(fù)制的案例,但是他們神話誕生的過程確是當(dāng)下中國電影逐漸穩(wěn)定的創(chuàng)意生產(chǎn)的模式)。當(dāng)下中國電影便身處這樣的體系之中。面對好萊塢電影的市場壓力(這個壓力在2017年結(jié)束之后會更加沉重),如何保持本土電影的觀眾吸引力,不僅是商業(yè)問題,也是意識形態(tài)問題,需要我們在對新的電影文化的理解中找到與政治的新型關(guān)系。
二
承前所述,以城市為中心的新的創(chuàng)意階層所形成的社會關(guān)系改變了中國電影的傳統(tǒng)生產(chǎn)模式。民營的電影制片、發(fā)行和營銷單位形成了各自新的創(chuàng)意和生產(chǎn)流程,電影創(chuàng)作者的“自由職業(yè)”屬性變得更加明確。新的生產(chǎn)模式和“自由職業(yè)”者們包容差異與自我表達的工作狀態(tài),又在逐漸服從和適應(yīng)著新的社會關(guān)系所支撐的新創(chuàng)意階層的內(nèi)在認同。最為顯著的就是,這種相對自由、松散,卻沒有傳統(tǒng)體系經(jīng)濟保障的狀態(tài),使得新創(chuàng)意階層對于產(chǎn)品商業(yè)回報的訴求比以往更加強烈。新創(chuàng)意不僅僅要體現(xiàn)創(chuàng)作者和創(chuàng)作團隊的個性差異,同時也更加主動地尋求最大公約數(shù)的受眾認同。畢竟,社會認同首先產(chǎn)生于共同的社會經(jīng)濟經(jīng)歷。普遍而言,對于電影類型的觀察,需要我們注意到這些類型共享的社會功能和它們形成的慣例。今天處于成長期的中國本土類型共享著新創(chuàng)意階層的經(jīng)濟訴求的同時,也在為類型創(chuàng)作結(jié)構(gòu)新的編碼,尋找著如何給予與最大公約數(shù)受眾之間“契約”的實際事件。
角色、場景和事件是構(gòu)成類型電影敘事成規(guī)和視覺慣例的重要元素。以此來觀察中國觀影人次增長最快的近六年(2011~2016年)的本土商業(yè)電影,我們會發(fā)現(xiàn)一些有趣的規(guī)律。在角色上,同校(班)同學(xué)(大學(xué)、高中)、職場同袍、歡場男女構(gòu)成了主要人物關(guān)系;場景方面則是校園、秘境(墓穴、荒村、鬼宅)、職場(辦公室、會議室)、休閑空間(酒吧、夜店、商場、餐館)、公路和城市(鎮(zhèn))街道;事件集中于愛情故事、友情故事、探寶(密)故事以及路上故事。這些角色、場景和故事構(gòu)成的電影并不為今天的主流評論甚至是大眾輿論所看好。低級、膚淺、平庸甚至爛俗常常是這些電影的標簽。從電影專業(yè)角度看,這些電影中的大部分也的確沒有辜負這些負面標簽給予的品格定位,也沒有形成如經(jīng)典類型般的觀眾期待效應(yīng)。盡管青春校園、都市言情、鬼怪驚悚、秘境探寶/奪寶形成了一定的敘事套路和視覺常規(guī),具備了作為類型的雛形,但這里面存在一個使這些類型處在不穩(wěn)定性狀態(tài)的因素:類型編碼有效的內(nèi)在認同,即與最大公約數(shù)受眾間“契約”的真實性。
羅伯特·麥基在他的名著《故事》一書中,用了一個例子說明故事的價值觀的時代真實感:“在整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婚外情一直都被視為一種痛苦的背叛。許多尖刻的影片——《相逢何必曾相識》(美國/1960)、《相見恨晚》——都是從社會對通奸的仇視中來汲取能量的。然而到了八十年代,社會態(tài)度發(fā)生了變化,人們越來越強烈地感到,浪漫的愛情是那樣寶貴,而人生又是那樣短暫,如果兩個已婚的人想要一份婚外情,就由著他們好了。”換句話說,與當(dāng)下最大公約數(shù)觀眾所訂立的“契約”應(yīng)該體現(xiàn)當(dāng)下價值觀的某種真實性。
對于中國本土類型電影來說,正在尋找新的類型編碼,而不僅僅是襲用好萊塢,更不是遵從中國電影傳統(tǒng)意義體系內(nèi)的敘事規(guī)則。以青春校園故事為例,中國電影的傳統(tǒng)題材編碼中,青春校園故事里的學(xué)生/個體與學(xué)校/權(quán)威之間的關(guān)系,是改造與被改造的啟蒙關(guān)系。學(xué)生與老師之間的階層差異構(gòu)成了對抗,最終老師和學(xué)生的變化,無論是向上、向善都服從于主導(dǎo)意識形態(tài)的教育觀。而好萊塢青春校園類型,我稱之為力比多戰(zhàn)爭。處在荷爾蒙旺盛期的青少年如何與一種壓抑性的規(guī)訓(xùn)體制做抗?fàn)帯W(xué)生/犯人、老師/警察構(gòu)成了兩組有趣的同構(gòu)關(guān)系。當(dāng)下的中國青春校園類型,雖不乏《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左耳》這樣有質(zhì)量的作品。青春傷痛過后對青春不朽的信念堅持,哀婉而美麗,帶有儒家出世哲學(xué)的意味。但在類型編碼上卻不同于好萊塢也與傳統(tǒng)中國校園電影有區(qū)別。2017年暑期檔公映的《閃光少女》,為校園青春故事提供了新的類型編碼。影片弱化了好萊塢電影和中國傳統(tǒng)校園題材電影中,老師與學(xué)生之間建立在體制和階層規(guī)訓(xùn)上的對抗,更沒有出格的荷爾蒙事件,而是把民樂和西洋樂之間的精神差異轉(zhuǎn)化為青春情感的價值堅守,兩相安好,各得其所。相比而言,我國臺灣地區(qū)的校園青春類型更接近好萊塢類型,但其小清新情緒又有臺灣地區(qū)青年人的感覺特征。《那一年,我們追過的女孩》《我的少女時代》都形成了本土化的類型樣式。相對于大陸(內(nèi)地)更多數(shù)的校園青春類型來說,除了表現(xiàn)出校園(老師)乏味和男女之間的縱情多彩外,似乎并沒有找到最大公約數(shù)的“契約”內(nèi)核。有些作品甚至把一些午夜B級片情色、暴力與奢靡的趣味也當(dāng)作了主流類型的配置。
這在都市愛情類型中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一些評論把近幾年出現(xiàn)的都市愛情類型簡約地當(dāng)作是好萊塢“小妞電影”的本土版,整體上“陰盛陽衰”。這類電影中的女主角常常是主動、勇敢、擔(dān)當(dāng),對愛情無怨無悔,而男主角卻常常是怯懦、含蓄、功利,對愛情瞻前顧后。暗戀、曖昧、錯過后偶然相逢的橋段被反復(fù)使用。某種程度上,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的日韓純愛電影和性別反轉(zhuǎn)愛情電影對這一類型影響頗深,如《情書》《四月物語》《八月照相館》《野蠻女友》。從時間上看,這些日韓電影在新創(chuàng)意階層的知識積累期和青春期具有啟蒙意義,因此形成了關(guān)于性別關(guān)系的一種新的審美趣味。相比好萊塢經(jīng)典都市愛情片,當(dāng)下中國都市愛情片的男性主導(dǎo)性不強,其實這恰恰是本土都市愛情類型最誠實的狀態(tài),它符合東方男性大智若愚,雅人深致的內(nèi)在要求,也符合東方女性對于男性沉穩(wěn)內(nèi)斂、淑人君子的性別想象。《北京遇上西雅圖》《失戀33天》能夠獲得最廣泛的認可,便是找到了這種性別文化心理的新的編碼方式。當(dāng)然,這兩部電影也在主題上都找到了一個對新知識階層受眾有粘度的內(nèi)核:成全與陪伴比占有和婚姻對愛情更有價值。
對于類型電影而言,它的基本功能在于利用最大公約數(shù)的受眾所能感受到的世俗日常生活的所見、所聽和所感,建立一個不同于現(xiàn)實世俗生活的具有帶入感的想象的生活,并在這個想象的世界中找到與受眾共享的價值觀“契約”。生活還是那個生活,精神卻已鳳凰涅槃了。徐崢的兩部公路喜劇片《人在囧途之泰囧》和《港囧》,在這方面做得比較到位。在筆者看來,影片把旅途中的各種不堪夸張地予以展現(xiàn),符合公路喜劇所應(yīng)有的元素和節(jié)奏,同時又沒有異想天開地逃避現(xiàn)實,而是把人物的處境非常結(jié)實地固定在今天我們所面臨的現(xiàn)實中。應(yīng)該說,徐朗(《人在囧途之泰囧》)和徐來(《港囧》)所面臨的困境正是今天崛起的年輕的創(chuàng)意階層所面臨的問題。職場傾軋、家庭分崩,以及夢想幻滅的時刻,是他們正在經(jīng)歷的新型社會關(guān)系與角色體驗的共同感受。影片沒有把這些感受變更成個人化的反思或憤懣,而是以自嘲的方式喜劇化地呈現(xiàn)出來。影片結(jié)尾,家庭依然是保持內(nèi)心和諧的心靈世界。麥基老先生說得好:“世上絕無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故事。一個誠實的故事只可能在一個地點和時間內(nèi)適得其所。”
新的創(chuàng)意階層正在用新的編碼方式建構(gòu)當(dāng)下中國本土類型電影的新樣式。他們調(diào)用自己的生活經(jīng)驗和對現(xiàn)實的切身感受,整合城市中新的職業(yè)分工所形成的社會關(guān)系,進行著一場既誘惑人心,又充滿風(fēng)險的試驗。囿于中國電影管理的現(xiàn)實國情,和他們本身相對局限的人生閱歷,以及與創(chuàng)意階層相伴而來的強大的商業(yè)企圖心,使得他們的試驗并不完美。但不可否認的是,創(chuàng)意階層靈光乍現(xiàn)和不斷試錯的挑戰(zhàn)性,是新時代中國電影所需要的創(chuàng)新意識。
三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中國自2002年開始的產(chǎn)業(yè)化改革,對中國電影業(yè)最根本的改造,是把電影由過去精英文化的屬性改造為大眾流行文化的品格。特別是近五六年,隨著新創(chuàng)意階層的崛起,網(wǎng)絡(luò)及新媒體受眾占比的不斷提高,中國電影的流行文化趣味愈發(fā)自覺。盡管在中國,電影依然無法回避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審查管理,無法如新媒體般自由呈現(xiàn)不同層面的以青年文化為主的多樣景觀(2017年對于網(wǎng)絡(luò)和新媒體傳播的管理條例的出臺,情況將有所變化),但也在新的類型編碼中挪用、收編了可以被最大公約數(shù)受眾認同的流行元素。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通俗小說已經(jīng)取代經(jīng)典名著成為電影改編主要的文學(xué)資源。網(wǎng)絡(luò)游戲的改編(《魔獸》)和元素調(diào)用(《微微一笑很傾城》)也不再是新鮮話題。網(wǎng)絡(luò)流行用語和“雞湯文”也頻繁出現(xiàn)在電影片名和臺詞中(如“囧”“屌絲”“Loser”“土豪”“女漢子”“你不來,我不老”“喜歡就會放肆,但愛就是克制”……)。一些世界著名的旅游景點也成為許多電影的取景地。這些場景的選擇有的是劇情需要,但多數(shù)只是給影片貼上時尚流行的標簽。正如英國杜倫大學(xué)教授大衛(wèi)·錢尼所言:“當(dāng)大眾文化形式——電影院、廣播電臺和電視臺、錄制的音樂、大眾出版物,尤其是大規(guī)模的營銷,等等——開始主導(dǎo)城市流行文化的多樣性之時,各種民族文化(nationalcultures)就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變得更具有同質(zhì)性。”這里所提到的營銷,恰是中國新創(chuàng)意階層對于電影作為大眾流行文化產(chǎn)品的內(nèi)在價值觀,即創(chuàng)意是一種具有更大影響力的“商品”,而不同于其他普通商品的傳播理念。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新創(chuàng)意階層努力在新媒體帶動的新經(jīng)濟模式中制造和擴展電影作為流行文化的用戶體驗效果。前文提到的馬云“玩”電影的策略,以及樂視老總張昭對于未來電影的暢想便是例子。
所有這些與傳統(tǒng)中國電影創(chuàng)意機制不同的變化,也促使我們反思在新舊媒體融合沖突的時代,如何建立一個主導(dǎo)意識形態(tài)和流行文化之間的新型關(guān)系。正如許多批評者所看到的那樣,當(dāng)下中國電影存在著諸多問題。這些問題的產(chǎn)生,一方面是轉(zhuǎn)型期中國類型電影創(chuàng)作和營銷的主體是城市一代的新的創(chuàng)意階層。他們的年輕態(tài)以及對于經(jīng)濟影響力的迷戀,使得這些作品囿于特定的圈子思維和價值觀,而無法建立更加普適的“契約”關(guān)系。另一方面,虛擬態(tài)和年輕態(tài)的流行文化又形成了新的霸權(quán),缺少必要的包容性。誠如前文所言,創(chuàng)意活動需要寬松的社會、文化與地域環(huán)境。當(dāng)下中國電影產(chǎn)業(yè)對經(jīng)濟增長有強烈需求,這與新創(chuàng)意階層的商業(yè)向往一拍即合,從而有了更多的創(chuàng)作機會。但對于那些更成熟的,對于現(xiàn)實和歷史有更深入思考的電影創(chuàng)作者來說,由于缺乏有效的溝通渠道,使得他們的創(chuàng)意在內(nèi)容和商業(yè)推廣上充滿了危險和不確定性。世界上許多電影導(dǎo)演,他們的創(chuàng)作周期很長,常常會在創(chuàng)作的最成熟期貢獻出充滿創(chuàng)意和文化價值的經(jīng)典作品。而今天中國的現(xiàn)實是,五六十歲的創(chuàng)作者基本上沒有了創(chuàng)作空間,更不用說更年長者。真正的文化創(chuàng)意者“他們既非傳統(tǒng)價值的擁躉者,也不隨波逐流地認同現(xiàn)代價值觀。這些人通常較為積極地參與與所關(guān)注的問題有關(guān)的社會活動……他們當(dāng)中的許多人對于精神生活很重視,他們拒絕接受主流宗教信仰……”因此,真正的創(chuàng)意活動需要調(diào)動不同閱歷的文化創(chuàng)意者的參與,惟其如此,才能使當(dāng)下中國電影有更加多樣成熟有質(zhì)量的類型電影。
對于新創(chuàng)意階層依賴網(wǎng)絡(luò)和新媒體制造的流行文化質(zhì)感,一方面我們應(yīng)該注意到這種文化確實使傳統(tǒng)媒體所創(chuàng)造的社群感發(fā)生了變化,參與現(xiàn)實問題討論的主動性更強,對官方和“磚家”的意見抱懷疑態(tài)度,對靠虛擬社群力量解決問題的意識更加強烈;另一方面,他們對問題的敏感和反應(yīng),他們討論問題的思路和步驟,以及他們有社群粘性的表達方式,讓“普通人”講“普通話”,都是電影故事獲得當(dāng)下性角色和場景的靈感源泉。
因此,最大限度地釋放新創(chuàng)意階層可能帶給中國電影新類型成長的活力,需要我們審慎地思考新型的政治與流行文化間的關(guān)系。美國電影學(xué)者托馬斯·沙茲對成功的類型有這樣解說,任何類型成功至少要依賴于兩個因素:它反復(fù)處理沖突的主題訴求,以及它在適應(yīng)觀眾和電影制作者對待這些沖突變化態(tài)度上的靈活性。作為一個“誠實的故事”,主題的重要性和對待沖突的靈活態(tài)度,來自于金科玉律般的歷史片庫,還是復(fù)雜豐富的現(xiàn)實境遇?處在產(chǎn)業(yè)轉(zhuǎn)折期的當(dāng)下中國電影選擇了后者。誰也不會否認,近十年中國電影業(yè)的巨大變化,為多樣的類型提供了過往無法想象的生存空間,也給本土類型電影的商業(yè)嘗試反饋了本土觀眾可能的痛點和興奮點。這或許是在那些被看作當(dāng)下中國電影的負面存在中,我愿意期許的新的積極因子的生長。
注釋:
② 見國家統(tǒng)計局發(fā)布的《中國城市化率歷年統(tǒng)計數(shù)據(jù)(1949-2013)》。
③⑤⑥ 見國家統(tǒng)計局網(wǎng)站: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
④ 楊韻新:《中國經(jīng)濟轉(zhuǎn)軌中的就業(yè)與失業(yè)狀況、形成機制及對策研究》,清華大學(xué)碩士學(xué)位論文,2002年,第18頁。
⑦ 張威:《中國行業(yè)收入差距現(xiàn)狀及影響機制研究》,中央財經(jīng)大學(xué)博士學(xué)位論文,2015年,第55頁。
⑨ 中國電影家協(xié)會、中國文聯(lián)電影藝術(shù)中心:《2017中國電影產(chǎn)業(yè)研究報告》,中國電影出版社2017 年版,第224-225頁。
⑩ 尹鴻、朱輝龍、王旭東:《“網(wǎng)生代”電影與互聯(lián)網(wǎng)》,《當(dāng)代電影》,2014年第11期。
(作者吳冠平系北京電影學(xué)院電影學(xué)系主任、教授,中國電影文化研究院執(zhí)行院長;張偉系北京電影學(xué)院中國電影文化研究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