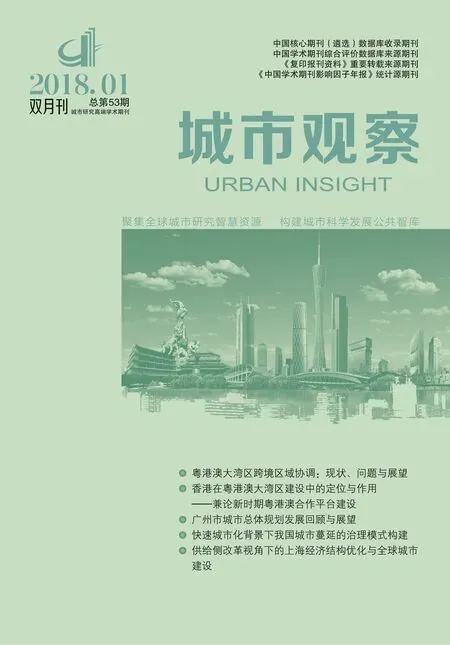公共行政視角下蘭斯塔德區域規劃及啟示
◎ 范建紅 劉雅熙
一、前言
區域規劃是國家政府進行區域管理和調控區域發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是新型城鎮化發展的重要空間尺度。在面對日益突出的人口、資源、環境問題和增強區域國際競爭力等方面,創新城市群區域規劃已成為不可回避且亟待研究的命題。城市群區域規劃根植于特殊的制度環境且受到政策設計的敏感影響,一方面,行政主體是激活城市群區域的主要執行組織,另一方面,政策設計的主導方向對城市群區域規劃將造成直接影響。更需要厘清的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機制往往是在地方政府的行政機器下形成的,行政體系才是真正的增長機器[1]。荷蘭蘭斯塔德(Randstad)是區域協調規劃的典范,該區域以多中心網絡化的空間組織和大面積的綠心格局而得名。分析蘭斯塔德區域規劃的發展歷程,剖析其所面臨的行政障礙,并從公共行政角度剖析其解決措施及效果,以期對我國城市群區域規劃發展具有一定的啟示與借鑒。
二、區域概況
蘭斯塔德是荷蘭乃至歐洲的一個重要都市區域,它包括荷蘭最大的四座城市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和烏特勒支市,以及這4個城市分屬的南荷蘭省、北荷蘭省、烏特勒支省和弗萊福蘭省中的一部分地區[2-4],一起形成了稱之為“蘭斯塔德”的都市區(圖1)。由于地處歐洲大陸多條大河的交界地區,有利的地理位置和日趨完善的運河基礎設施,使蘭斯塔德成為歐洲重要的貿易和經濟中心。
歷史上蘭斯塔德是一個沼澤地區,土地不易利用,只有少量居民從事捕魚和狩獵。從11世紀開始,蘭斯塔德進行了堤坎建造和土地開墾,居民隨之大增,伴隨經濟的發展,在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等城市間出現了定期航班,促使了商業和貿易的進一步繁榮[5]。1665年,蘭斯塔德地區各城市間的運河體系基本完工。隨著歐洲工業化時代的到來,作為歐洲大陸門戶和商貿樞紐的蘭斯塔德經濟實力和地位得到鞏固和提升,其中位于萊茵河口的鹿特丹成為世界排名第一的港口城市,1975年其港口貨物吞吐量達到2.73億噸。阿姆斯特丹通過圍海造地變成了內陸海城市,雖然其港口城市地位下降,但是其金融中心的地位得到進一步提升。從19世紀下半葉開始,新的基礎設施包括水路、公路和鐵路等相繼完善,使得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成為新的連接北海和德國魯爾地區的樞紐。交通工具的現代化,大量農村人口遷移到城市,到2005年大約有670萬人居住在此,成為繼倫敦、魯爾萊茵河、巴黎、米蘭后西歐人口最密集的城市地區。
蘭斯塔德區域的突出特點,是由功能上互補的多個專業化中心構成的互補型空間結構[6,7]。其“多中心”馬蹄形環狀布局,同時將一個大城市點所具有的多種職能,分散到大、中、小城市,形成既分散、又聯系,并有明確職能分工的有機結構[8-10]。歷史上,它曾是荷蘭共和國的中心,現在依然是荷蘭的政治和經濟中心。該地區的發展一直呈現著多點集聚態勢,一方面見證了以城市為核心的區域競爭力提升,另一方面又引發了不可避免的城市之間圍繞產業發展、招商引資、人才、基礎設施等的白熱化競爭[11]。由于蘭斯塔德地區不是法律上的實體,導致地區的發展沒有統一的政府機構來直接解決他們所共同面臨的區域缺口。鑒于蘭斯塔德開拓的復雜性及其對于荷蘭整個國家的重要性,公共行政機制對于該區域的發展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圖1 蘭斯塔德區域空間布局圖
三、分離與制衡:區域規劃背后的行政邏輯
(一)縱向協調的零和博弈
荷蘭的公共行政被描述為“分權的單一制國家”,即公共權力在中央、省、市等三個層級政府間進行分配,每一層級政府都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權,三個層級的政府不會采取與其他兩個層級的政府相矛盾的行動[12],但各自都不可避免更加熱衷于各自的權力擴張和功能的強化,增大了非合作的決策概率[13]。三層制雖存在固有的縱向協調規則,即國家政府通常決定空間規劃政策,省政府在各自轄區內實踐規劃政策,市鎮政府則進一步具體落實規則政策。但荷蘭權力下放的程度卻總能打破這一規則,中央、省、市政府在財政支出比較時,往往會以市政府的權利為主導。相比省政府,各市的責任更重大且更廣泛,市政府負責范圍廣泛的政策領域包括公路、公共交通、住房、環境、社會事務、經濟發展、教育、醫療等。直到2008年新的《空間規劃法》出臺,一直被挫敗的層級制縱向協調規則得到了主動糾正,中央再次固化了嚴格的層級體系,空間規劃中的權力平衡被打破。中央強制性要求所有的省份都設置一個“省級空間規劃委員會”(荷蘭語:Provinciale Planologische Commissie,簡稱PPC,由《空間規劃法》的第9.1條建立),并以主動磋商與被動強制的雙重手段,使得不同層級政府間的協商成為空間制度并內化為縱向規劃的典型特征[14]。但各方利益的博弈,地方政府仍難以輕易放棄空間開發的主動權。
(二)橫向合作的縫隙制衡
橫向協調規劃的復雜性在于空間規劃不可避免地會觸及許多其他部門的利益,同時又涉及不同空間范圍的權限設定,合作的基礎極其薄弱,只能在各部門各自能接受的最大范圍內尋求縫隙,展開區域制衡設想。在市鎮層面,蘭斯塔德區劃內各市之間的合作相對頻繁,據統計,平均每個市有涉及27個合作安排[16]。合作可以通過公私法下的協議進行,大約40%的私法協議以合同形式存在,一旦訂立,法律上可強制執行。市政府已經越來越意識到,這樣的安排將有助于他們分析各種合作的最終成本效益[17]。在省級層面,雖然省空間規劃委員會并不直接對許多政策地區負責,但它是所有協調規劃問題的最終匯集點,因此省空間規劃委員會常用于解決橫向協調的難題。而國家政府層面的橫向協調是難度最大的,因為總是存在著一些強勢、富有且雄心勃勃的大部門,如經濟事務部想要更多的商業用地、交通部想讓住宅鄰近商業區建設、農業部門不希望耕地變成自然景觀等等,使得國家政府層面的橫向協調規劃面臨困境。
四、資金與市場:行政協調的現實障礙
(一)資金的融通互斥
融通互斥是指規劃資金不論是融資還是流通都存在互相抵觸的情境。據統計,市政府70%的資金來自中央政府補貼,但融資一定是市政府的工作內容之一,且區域內的空間開發是受財政利益所驅動。綠心的開發則充斥著政府進退兩難的局面,被稱為“為綠而紅”,其實質表現為,規劃部門希望改善鄉村地區的質量,但也不希望用公共資金來資助這項工作,于是少量的城市開發被加入這一地區的規劃[18]。同時,當區域內的資金和責任必須協調時,各區域尺度之間則存在顯著的利益沖突。如阿姆斯特丹城市區域(ROA)和北荷蘭省之間的公共交通系統運行沖突,本可互相依賴,但最終因為雙方夙愿的差異而導致缺乏合作,使得在整個北翼很難建立一個協調的公共交通網絡,交通的碎片化和不通達問題較為嚴重[19]。
(二)市場的規則沖擊
荷蘭政府職能的不斷轉變給了市場經濟無限的可能,政府主動的向開發商下放空間開發的權利,這一政策帶來了許多不可預見性的問題。如為了財政盈余,政府和開發商往往沖突嚴重,這是各國規劃都會遇到的尷尬。其中一個典型案例來自阿姆斯特丹市政府與ABP公司,兩者于1998年簽署協議,該協議包含以下條款:“雙方承諾,直到所有建筑都已出售完畢,否則不會在其境內進行辦公樓和酒店的開發,這與現有項目會產生競爭”。這種避免競爭的方式,使得主觀影響了市鎮政府的土地利用規劃政策和對市場規則產生沖擊。由于市場與政府這兩大團體各有不同的利益追求,兩者的關系平衡仍是需要關注的問題。
五、擴省并市與區域建構:行政干預的兩條脈絡
(一)縱向激進變革:擴省并市
蘭斯塔德的區域合作通常集中于城市地區以及市級層面之間,權力的下放使得地區間的合作與市級本身的權益處于矛盾狀態。20世紀60年代以來,中央各級政府對這一治理問題提出了若干改革措施,主要包括增加區域一級,增設省份和創造大城市的建議。70年代初期,提出增設區域一級建立44個地區。在1975年至1983年期間,提出了增設省份的建議,并從最初的26個最終修改增設為17個。在20世紀90年代,由于增設省級的建議一直被擱置,改革重點轉向增加大城市的作用,提出除現有省份外再造7個大城市[20]。這一改革主要集中在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目標是創建一個大阿姆斯特丹和一個大鹿特丹,以便將周邊市鎮分別并入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市。1995年,隨著國家空間戰略對蘭斯塔德提出了新的發展要求,要求將蘭斯塔德提高到全球競爭體系中,建議將蘭斯塔德地區合并成一個新的區域,類似于大倫敦空間形式,這種獨立行政框架的建立意味著巨大的經濟社會活動集中。
這些空間調控策略不僅是荷蘭政府對區域發展邊界進行的強制重構,也與荷蘭國家追求區域平等主義和可持續發展的傳統格格不入。相較于建立一個蘭斯塔德省,荷蘭人民更希望建立與之抗衡的區域,維持多中心網絡化的空間格局,同樣強行整合必然會觸動地方自治與文化認同,反對勢力會壓倒推動改革的動力。雖然建立區域縱向治理框架是一個良好的開端和有力的保障,但改革該結構需要大量的精力和時間,在短期內不能解決許多實際問題,因此縱向層面上激進的改變結構并不是有效的解決方案[21]。
(二)橫向溫和調整:區域建構
當1983年增加省份數量的建議失敗,使得區域橫向合作的機會得到加強。相比于縱向協調試圖硬性改變權利網絡,橫向合作的嘗試則是相對溫和的一種選擇。一是不觸犯更多的權利組織;二是可以多方合作,跨界范圍靈活;三是以預設目標合作,約束性能弱化。
蘭斯塔德區域規劃中的水平合作模式,最多能達到七個層級:國家政府、蘭斯塔德、翼、省、城市區域、市政區、市轄區(如表1)。在傳統體制內,基本認可了這種合作會使預設目標變得更加具有特定任務性。2002年的“雙重地方政府法”加強了市議會控制其執行委員會的權力和增加了合作的民主合法性,并且多半市政府認可這種橫向合作模式,認為促進合作安排和改進民主控制是有效的手段。自2003年以來,城市地區基于聯合安排法案(“WGR加強”區域,荷蘭目前有8個“WGR①加強”區域),這些城市區域包括一個大城市和其周圍的城市,形成城市系統的一部分。2010年,“WGR加強②”區域的強制屬性被廢除,市際間的合作不再被要求強制執行,但可以自愿持續,并形成了蘭斯塔德地區、WGR加強區域③、北翼地區和南翼地區。
橫向合作使蘭斯塔德區域規劃發展中面臨的治理問題得到了一定的解決,但由于組織構建上的一些障礙,使得蘭德斯塔德在這個階段的區域決策作用相對有限[28]。其次引發的次生效應中呈負面屬性的影響還無法控制,例如行政擁擠問題,從表2中可以看到,形成的機構很少被廢除,使得城市集群區域不能很好地處理空間關系。蘭斯塔德橫向的區域建構,其產生的效果與預設目標的達成之間基本呈正相關,能夠辨別實質效力情況,這樣也能更好地估計協調效果與進行進一步改進,這是橫向合作相比縱向改革一個更明顯的優勢。
六、結論與啟示
當今國家與區域之間的競爭,在相當程度上是取決于制度的競爭。荷蘭政府早已關注到如何提升蘭斯塔德的國際競爭力,促成內涵式可持續的發展模式。這種良性溢出趨向的內涵式可持續發展模式導向加上規劃實踐的雄心,讓荷蘭區域規劃獲得了一份雙重保險,正如法羅迪和范德沃克所強調的,“規劃和秩序”是荷蘭空間規劃的顯著特點[29,30]。相較而言,中國在區域規劃的主導方向上還缺乏一定的著力點和前瞻性,近年來,隨著市場化與私有化引發城市社會空間改變加劇,固有尺度正在分化,不同空間的聯系變得更加密切與復雜,更加容易引發對規劃空間的變向爭奪。因此,提出以下行政改革的建議與啟示。
(一)行政理念:從區域兼并到區域管治
行政區劃調整對于解決區域問題的作用多次證明是非常有限的,蘭斯塔德地區的核心城市周邊的行政兼并,不論是兼并核心城市之內的還是外部的區域,都是暫時回避地方政府之間沖突的深層體制性問題,為鞏固集權體制的一個變向途徑,對于行政體制的進步并沒有太大意義。區域整體發展中的矛盾,已經不可能再寄希望于通過簡單的行政區劃調整來解決了。轉型的城市區域,由于城市空間或社會空間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尤其是“全媒體”時代的到來,公共與私人領域的融合打破了傳統科層式的等級空間,多元文化使得空間異質性增強。因此,在制定公共政策時更需要考慮整體的公眾利益并且增進不同群體之間的交流與理解,利用管治的理念處理不同尺度的區域問題是解決問題的思想前提。各層級找準在體制內外的角色,創造良好的制度—社會—生態環境,才是社會公平與社會和諧的前提。

表1 蘭斯塔德公共行政橫向合作平臺
(二)合作基礎:從多層級區域協調到全國空間和基礎設施建構
從蘭斯塔德經驗中可以看出,縱向行政合作的基礎是薄弱的,這與我國的情況較為相似。但是荷蘭政府在橫向合作的基礎構架上做出了積極轉型,掙脫多層級區域協調的種種壁壘,建立全國空間和基礎設施框架。從空間整體性集中管理出發,例如農業片區、河流沿線、堤岸防護以及道路管線等基礎空間規劃。也正是因為對農業片區的保護,才形成了城鎮形態突出的蘭斯塔德地區。同樣為了保護河流沿線水質與生態景觀,才有了荷蘭特色高質的鄉村景觀。荷蘭的區域規劃協作基礎不僅僅局限于經濟的增長,而是注重于培養空間增長點的方式,通過自然聯系塑造的空間網絡,使得以“生命線”為媒介的區域協作變得更持久和可靠。到目前為止,中國各城市之間并沒有攻破各自建立的行政區經濟壁壘,且生態整體性規劃框架尚未建立。中國式區域規劃如何找到合適的切入點,使得區域間的矛盾能得到有效解決,將是未來區域發展與規劃的重點。
(三)行政管控:從行政壁壘到溝通協調
荷蘭的規劃體系以溝通、協商、共贏為最大特點,為了打破行政區壁壘的出現,專門在中間層級設置了縱向三級政府溝通平臺——省空間規劃委員會,以及國家部委橫向層面協調機構——國家空間規劃委員會,同時還在層級內設置了橫向的省協會(IPO)和市政協會(VNG)。處在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出現的問題和情況錯綜復雜,決非某一組織所能獨立解決的。這就要求從實際出發,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按照“少而精”的原則,建立少量的協調組織進行協調,明確運行主體的責任和義務以及相關部門或配合行動部門的責任和義務。因此,建議設立區域聯席會議制度和部級聯席會議制度。區域聯席會議制度主要針對發展中不同尺度的空間鏈體,部級聯席會議制度則是針對部門間的協作,這樣既不會讓還沒有形成固定尺度的區域進行組織整合,又不會增添新的管理對象,以增加行政的彈性,有利于集中解決實質問題。
注釋:
①WGR(荷蘭語:Wet Gemeenschappelijkeregelingen):聯合規定法,用以促進鄰近市鎮之間的合作。
②WGR加強:聯合規定法的進一步加強。
③WGR加強區域:海牙城市區域(Haaglanden),阿姆斯特丹區域(Regionaal Orgaan Amsterdam),烏特勒支管理區(Beatuur Regio Utrecht),鹿特丹城市區域(Stadsregio Rotterdam )。
[1]吳縛龍,馬潤潮,張京祥.轉型與重構:中國城市發展多維透視[M].東南大學出版社,2007.
[2]劉利,王法成.“綠心環形城市”的源流、發展與演變[C].生態文明視角下的城鄉規劃:2008中國城市規劃年會論文集.大連:中國城市規劃學會,2008:12.
[3]柳天恩,翟紅敏,曹洋.荷蘭蘭斯塔德功能區聯動發展模式及其啟示[J].新疆財經,2015,(4):49-53.
[4]吳之凌.城市生態功能區規劃與實施的國際經驗及啟示——以大倫敦地區和蘭斯塔德地區為例[J].國際城市規劃,2015,30(1):95-100.
[5]華晨.蘭斯塔德的城市發展和規劃[J].城市規劃匯刊,1996,(6):16-25.
[6]謝盈盈.荷蘭蘭斯塔德“綠心”——巨型公共綠地空間案例經驗[J].北京規劃建設,2010,(3):64-69.
[7]馬永歡,黃寶榮,陳靜,張迎新.荷蘭蘭斯塔德地區空間規劃對我國國土規劃的啟示[J].世界地理研究,2015,24(1):46-51.
[8]胡燕,孫羿,陳振光.中國城市與區域管治研究十年回顧與前瞻[J].人文地理,2013,28(2):74-78.
[9]盧明華.荷蘭蘭斯塔德地區城市網絡的形成與發展[J].國際城市規劃,2010,25(6):53-57.
[10]袁琳.荷蘭蘭斯塔德“綠心戰略”60年發展中的爭論與共識——兼論對當代中國的啟示[J].國際城市規劃,2015,30(6):50-56.
[11]Falidi A,Valk A.De Groeikernen als Hoekstenen van de Nederlandse Planningdoctrine[M].Assen:Van Gorcum,1990.
[12]何鶴鳴,張京祥.產權交易的政策干預:城市存量用地再開發的新制度經濟學解析[J].經濟地理,2017,37(2):7-14.
[13]張書海,馮長春,劉長青.荷蘭空間規劃體系及其新動向[J].國際城市規劃,2014,29(5):89-94.
[14]Hall P. Cities of Tomorrow: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M]. Oxford:Blackwell,1996.
[15]Pellenbarg P, Van Steen P. “Housing in the Netherlands: spatial variations in availability, price, quality and satisfaction” [J].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2005,96(5):593-603.
[16]Faludi A. The Performance of Spatial Planning[J]. Planning Practice & Research, 2000, 15(4): 299-318.
[17]尼德漢姆.荷蘭土地使用規劃:原則與實踐[M].東南大學出版社,2014.9.
[18]Commissie G, Op schaal gewogen. Regionaal bestuur in Nederland in de 21ste eeuw, Association of Provinces[M]. The Hague,2002.
[19]Boogers H. Middenbestuur in discussie; analyse van en reflectie op de naoorlogse discussie over middenbestuur in Nederland[M]. Paper University of Tilburg, Tilburgse School voor Politiek en Bestuur,Tilburg,2006.
[20]Cerfontaine G. Governance in de Randstad, Rede Universiteit van Utrecht[M]. Utrecht,2005.
[21]Manfred Kühn. Greenbelt and Green Heart: Separating and Integrating Landscapes in European City Regions[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3, 64(1-2):19-27.
[22]Lambregts B. Polycentrim: Boon or Barrier to Metropolitan Competitiveness? The Case of the Randstad Holland[J]. Built Environment, 2006,(32):114-123.
[23]Hendriks F, Juliet M. Making Local Democracy Work: Neighborhood-oriented Reform in Lo Angeles and the Dutch Randstad [M]. Tilburg,2003.
[24]Robert C K, Sako M. The Polycentric Urban Region: Towards a Research Agenda[J]. Urban Studies,2001, (38):623-633.
[25]Anas A, Arnott P & Small A. Urban Spatial Structure[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8, (6):411-424.
[26]Davoudi S. Polycentricity in European Spatial Planning: From an Analytical Tool to a Normative Agenda[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03,(11):979-999.
[27]阿金J.凡德伯格,巴特L.賓客,林劍云.面向2040年的蘭斯塔德地區——荷蘭政府遠景規劃[J].國際城市規劃,2009,24(2):20-26.
[28]Thorsten S.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Urban Developments in the Dutch Lowlands[M/OL].[2009-08-11] http://summerschool.ifou.org/2009delft/downloads.php.
[29]Faludi A,Van Der Valk A. Rule and Order-Dutch Planning Doctrin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M].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4.
[30]Lambregts B, Zonneveld W. From Randstad to Deltametropolis: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s the Scattered Metropolis[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04,(12):299-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