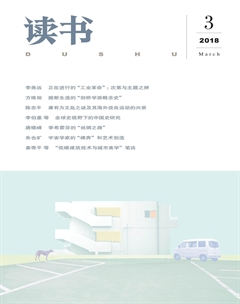正在進行的“工業革命”:次第與主題之辨
李堯遠
二0一一年九月,美國著名的未來學家杰里米·里夫金撰寫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新經濟革命如何改變世界》出版,二0一二年四月,英國著名經濟學雜志《經濟學人》發表了《第三次工業革命:制造業與創新》的專題報道,兩者都言明:“人類已進入第三次工業革命時代。”而自二0一五年起,德國的工業4.0專家烏爾里希·森德勒主編的《工業4.0:即將來襲的第四次工業革命》(二0一五年一月),日本學者藤原洋的《精益制造030:第四次工業革命》(二0一五年十月),世界經濟論壇(也叫“達沃斯論壇”)創始人兼執行主席、德國學者克勞斯·施瓦布的《第四次工業革命:轉型的力量》(二0一六年六月),《日經商務周刊》編撰的《第四次工業革命》(二0一六年九月)等著作也相繼問世,它們卻在宣示著“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在發生。另一方面,不論是在新聞媒體上,還是在學術刊物上,近些年的諸多文獻都以“第三次工業革命”或“第四次工業革命”為背景或內容進行報道或者研究。甚至在二0一三年,《新工業革命》一書的作者英國人彼得·馬什還提出了“第五次工業革命”的觀點。這種大相徑庭的表述說明工業革命的次第和主題出現了紊亂:當前正在科技和工業領域發生的深刻變革能否被稱為“工業革命”?如果是“工業革命”,究竟是“第三次”還是“第四次”抑或“第五次”?各自的主題又是什么?
一、界定工業革命的標準
什么樣的變化才能被稱為“工業革命”,需要設定一定的評判標準,標準的缺失與錯亂,是人們“自言自語”或各執一詞的原因。在學術范疇里,人們通常把“工業革命”與“第一次工業革命”等同起來。雖然不同的學者對工業革命有著不同的解釋,甚至至今沒有達成共識,但工業革命的研究者舒小昀認為,對工業革命的解讀越來越趨向于綜合性的定義,即,將對工業革命進行闡釋的各類學派觀點的核心要素綜合起來,構成一個工業革命評價或定義的集合體系,以此作為界定工業革命的標準。以不同學派對工業革命的內涵研究為依據,可以勾勒出界定工業革命的基本條件:
社會變革學派: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全面的巨大變革;
工業組織學派:能夠影響整個經濟和社會的生產組織形式的變化;
宏觀經濟學派:投資率的大幅提高、經濟結構的變化和由政治、社會結構的優化而帶來的可持續的增長;
技術學派:新技術的出現及其持續性創新是工業革命的核心;
能源學派:工業革命根本上改變了人們獲取能源的方式,從而滿足了以能量需求為核心的人的物質需求,新能源的利用或能源獲取及使用方式的變化是工業革命的核心指標;
消費學派:日益擴大的供求缺口即消費需求的產生推動了工業革命的發生。
綜上所述,判斷一場變革是不是工業革命,大概需要如下四個條件:一是能夠深刻影響生產生活尤其是生產組織形式變化的非傳統核心技術體系革新,二是生產效率的提升和經濟社會的快速持續發展,三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的系統性變革,四是新能源的出現或能源利用方式的變化。只有上述四個條件同時具備才能被稱為工業革命,其中一個或兩個領域的變化不能以“工業革命”相稱,這正是科技革命的次數多于工業革命次數的原因。
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都符合上述標準,而且關于這兩次工業革命的時間、主題,人們基本已經達成共識:第一次工業革命被稱為“蒸汽革命”,時間是從十八世紀六十年代到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蒸汽機動力技術的深刻變革不僅使工業工廠代替了手工勞動,也促進了英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使自耕農階級的消失和工業資產階級的壯大,深刻地影響了英國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為英國成為資本主義強國奠定了基礎。第二次工業革命被稱為“電氣革命”,時問是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紀初,電力技術的革命帶動了化工、能源、機器制造、交通運輸等行業的全面發展,新技術的廣泛應用不僅極大促進了生產力的進步,而且加快了資本主義的社會化趨勢,催生了壟斷組織,壟斷資本家為了攫取更多的超額利潤開始更加肆無忌憚地干預國家的經濟和政治,甚至走出國門,制造國際壟斷組織,推動美、英、法等資本主義國家進入帝國主義階段。
二、當前工業革命次第和主題的爭議
關于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爭論。工業革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人們置身其中時常常不能感知,多數是一種事后的評價和界定,摩根認為:“工業革命的影響是相對的,只有在進行回顧的時候才顯示它的意義。”在第二次工業革命發生以后,也有人根據經驗去研判和預測某些領域的技術變革可能給社會帶來的巨大變化,關于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預言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的八十年代。第一種觀點認為,計算機技術或信息技術的創新和應用帶來的系統性變革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核心內涵。一九八六年,美國新澤西理工學院的經濟學教授羅伊·赫爾夫戈特看到以中央計算機為核心的柔性制造系統控制下的機器人勞動對于提升生產效率和降低成本的巨大作用,并預測這種技術同時也將對以等級和分工為依據的組織管理帶來沖擊,由此做出美國正在發生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判斷。一九八八年,印度經濟學家羅哈特·奈比·柯漢指出,計算機和通信技術的相互融合及其在金融、商業、管理、工業、科學研究、天氣預報等領域的廣泛應用必將帶來第三次工業革命。一九八八年,日本日立公司的科技研發經理武田認為由晶體管、計算機、火箭等技術發明為核心的工業革命是“2.5次工業革命”,而日本東京大學的后藤教授研究的磁性量子參數器將能夠徹底優化“信息處理裝置的存儲單元和邏輯單元”,從而將世界帶進第三次工業革命時代。可見,武田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支撐技術仍然是信息技術。
二000年,阿格內斯·巴爾頓總結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一九九九年六月召集的由世界知識界領袖參加的“全球化與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圓桌會議的主要觀點,其中來自耶魯大學的保羅·肯尼迪教授指出由計算機和互聯網技術主導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將擴大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差距。為討論方便,我們將這種觀點定義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信息技術學派”。第二種觀點認為,可再生能源技術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技術支點。二0一0年,能源工程學家貝拉·利普塔克強調在其《后化石能源時代》一書中設計的過程控制技術把太陽能發電推向世界,它將推動全球在二十至五十年后實現清潔能源對化石能源的替代,從而實現工業領域的革命。第二位支持可再生能源技術是工業革命的推進劑的學者便是杰里米·里夫金,他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一書中指出:“互聯網信息技術與可再生能源的出現讓我們迎來了第三次工業革命。”我們把這種觀點定義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新能源學派”。第三種觀點認為,新材料和智能制造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主題。持這種觀點的是《經濟學人》雜志,它在《第三次工業革命:制造業與創新》中指出,3D打印技術、納米等新材料、產業集群、新一代機器人、高度的數字化等元素的創新與融合將成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導火索。我們把這種觀點定義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智能制造學派”。第四種觀點認為,納米技術“點燃了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曙光”。斯路陽在總結一九九三年第二次國際納米技術研討會成果的基礎上,得出納米技術發展“可引起電子學、計算機技術、生物學和醫學的質的飛躍,產生一次新的工業革命”的結論。我們把這種觀點定義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納米技術學派”。endprint
關于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研究有兩次高潮,一次是在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四年左右,一九八三年十月,歐洲經濟共同體為了改變在信息技術領域的研究落后于美國和日本的狀況,十個國家的工業部長在希臘雅典制訂了“歐洲信息技術研究發展戰略計劃”,人們以為第四次工業革命即將來臨;另一次是在二。一三年,德國政府在漢諾威工業博覽會上提出“工業4.0”戰略后,又引起了產業界、新聞界和學術界關于“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熱烈討論。而這些關于“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內容或主題的提法都不盡相同。第一種觀點認為第四次工業革命是以電子、信息、新材料等技術的使用為動力而產生的一系列變革。這種看法是一九八三年左右學術界和新聞界關于第四次工業革命討論的主題:一九八三年,《芝加哥論壇報》科學撰稿人羅納德·科圖拉克引用時任環球石油公司(UOP)副總裁瑪麗·古德的看法,認為以計算機、遺傳工程、新材料和新能源的發明和使用為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已初露端倪。一九八三年,著名經濟學家華·惠·羅斯托把電子、通信、機器人、新材料等技術發明與應用稱為“尚處于起步階段的第四次工業革命”。一九八四年,在歐共體工業部長的“雅典會議”之后,英、法、意大利、聯邦德國等國家的主要報刊都對“第四次工業革命”進行了討論,普遍認為新的電子和信息技術將會對職業結構、生產效率、社會形態帶來深刻影響。我們把這種觀點定義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信息技術學派”。第二種觀點認為以信息技術為基礎的智能制造將成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驅動力。施瓦布認為人工智能、可植入技術、納米技術、3D打印、萬物互聯等二十三項技術的全面革新將成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主要內容。《日經商務周刊》通過對西門子、通用電氣、博世、日立、羅蘭貝格等世界知名公司領導的采訪,匯集了他們對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看法,這些公司領導基本上將第四次工業革命與德國的“工業4.0”等同起來,認為“關聯工業”(相連接的工業)、“智能工業”(會思考的工業)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著力點。森德勒整理了電子、自動化、機械工程、汽車制造等諸多領域專家的觀點,認為“生產高度數字化、網絡化和機器自組織”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主體意涵。我們把這種觀點定義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智能制造學派”。第三種觀點認為綠色能源革命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重心。二00九年一月,許明等人提出新能源、新材料、新環境科技和新生物技術將成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核心。藤原洋認為自己在二0一0年就率先提出了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概念,以信息技術不斷革新為基礎的太陽能經濟、新智能電網等應成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核心要素。清華大學的胡鞍鋼認為要中斷十八世紀中葉以來的“黑色發展軌跡”,讓人類步入綠色發展時代,綠色能源革命或環境革命將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主線。我們把這種觀點定義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新能源學派”。
關于第五次工業革命的爭論。藤原洋在展望工業的未來發展趨勢時,認為機器人革命將是第五次工業革命的主要篇章。彼得·馬什認為技術的交叉融合、智能化支持的個性定制與生產、高度專業化、環境保護壓力與責任、特立獨行的制造商、新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等組成了第五次工業革命的關鍵要素。
三、當前工業革命的次第與主題辨析
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四年,關于“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討論之所以認為工業領域將要發生的變革是“第四次”是因為當時學術界對于工業革命的次第劃分本身就在爭論當中,古德、羅斯托、馬什等都認為在目前我們已經達成共識的第一次的“蒸汽革命”和第二次的“電力革命”之間還有一次“工業革命”,即鐵路和輪船的發明和使用在十九世紀三十到四十年代先后為英國、美國和德國帶來了繁榮,是“第二次工業革命”,這就是一九八三年左右那次關于工業革命的討論會被定義為“第四次”的原因。但是,后來學者們認為鐵路、輪船的使用不過是“蒸汽革命”的繼續,所以,應當被歸入“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范疇,也就是說,基于后來對第一次工業革命和第二次工業革命達成的共識,一九八三年那次討論中認為將要發生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實際上應該是“第三次”,其內容是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一系列技術革新帶來的系統性變化。因此,馬什所認為的“第五次工業革命”應該叫作“第四次工業革命”,依此類推,馬什關于工業革命的觀點便又和施瓦布等人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智能制造學派”回到了同一起跑線上。
當前,對“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定義占主流的仍然是赫爾夫戈特、柯漢、武田、巴爾頓、肯尼迪等人的“信息技術學派”的觀點,即電子信息技術的發明使用及其給整個世界帶來的巨大影響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主題和內容,根據上面的分析,該觀點的支持者還可以包括羅斯特、古德和馬什,還有后來提出“第四次工業革命”觀點的施瓦布、森德勒等人。我們依據衡量工業革命的四個方面的標準來判斷“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信息技術學派”的觀點。第一,以某一核心技術為支點的非傳統的技術體系的革新。信息技術是本次變革的核心技術,且它與第一次的蒸汽機技術和第二次的電力技術在本質上存在區別,同時,以信息技術為支點,它帶動了原子能技術、空間技術、生物技術、能源技術、海洋技術、材料技術等一系列技術的發展。第二,生產效率大幅提升和經濟社會發展。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第四代大規模集成電路在計算機上的運用揭開了計算機在生產生活領域運用的新篇章,從一九七0到二00一年,世界經濟經歷了長達三十二年的持續增長,平均增長率為3.7%。周勤等人的研究發現:“信息技術的應用發展以網絡形成與擴展為載體,不僅能夠改進交易效率,促進分工水平提升和報酬遞增,而且又可以以生產性產業的身份直接促進經濟增長,另外,信息技術的進步能夠使市場大小和分工程度相互依賴,從而產生報酬遞增的良性機制并促進經濟持續增長。”第三,導致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系統性變革。信息技術尤其是互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和廣泛使用,加快了信息傳遞的速度和效率,使傳統的“官僚制”模式受到挑戰,產生了組織扁平化的趨勢;它使各類資源信息的聚集與共享成為可能,催生了電子商務、分享經濟;它建造了虛擬的網絡世界和新型媒體,加速了文化、思想的傳播和碰撞,軟化了傳統的權威力量,推進了社會的多元化進程,信息技術立體地影響和改變著整個社會。以上可以證明,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技術體系的進步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標志,在這一點上,“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信息技術學派”“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智能制造學派”“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新能源學派”的觀點是一致的,也可以說人們在“第三次工業革命是信息技術革命”這一點上共識是非常廣泛的。endprint
里夫金和施瓦布等人定義的“新工業革命”實質上只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新浪潮”而非“新革命”。首先,辨析“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新能源學派”的觀點。里夫金認為,可再生能源的轉變、分散式生產、氫存儲技術、能源互聯網實現分配和零排放的交通方式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五大支柱,他對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次第與主題定義是認同的,但他否認“第三次工業革命信息技術學派的觀點”,認為第三次工業革命是“互聯網技術和可再生能源的融合”,所以,上海交通大學的陳憲教授認為里夫金是“重新定義了第三次工業革命”。從里夫金對第三次工業革命五大支柱的厘定中可以看到,太陽能發電、垃圾發電、風能發電等可再生能源技術已經日趨成熟,它們或許會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也會引起政治、文化等領域的部分變化,但這種影響與信息技術帶來的影響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而且關鍵的是這些僅僅存在于能源領域的技術無法引起整個社會技術體系的革新,因此,它無法被稱為新的“工業革命”,但恰恰相反,如果沒有互聯網技術,里夫金所說的能源供應方式的革命便不會發生,所以支撐里夫金關于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不可或缺的技術依然是以互聯網為表現形式的信息技術,里夫金所說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不過是信息技術在新能源領域的運用,依然是信息革命的繼續,他所提出的“革命”的最大緣由與二十世紀后期以來日益緊張的化石能源的供給、全球污染和氣候變暖有關。同理,“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新能源學派”的觀點也應當看作信息技術運用領域的拓展,而不是“革命”。其次,辨析“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智能制造學派”的觀點。以施瓦布為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智能制造學派”其核心名詞是“智能制造”,而智能制造也是信息技術在生產領域運用的新形式,其并沒有產生“不同于傳統的核心技術”,所以,它也不能被稱為“工業革命”,不過,它在很多生產領域已經變為現實,從目前的發展趨勢來看,它比里夫金認為的“互聯網與新能源的結合”來得要快要早。如此,“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智能制造學派”、藤原洋和馬什的“第五次工業革命”與“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智能制造學派”的觀點也就殊途同歸了:都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延續。最后,結合界定工業革命的標準,可以看到納米技術雖然是一項不同于傳統的新技術,但它并沒有引發不同生產領域的技術體系的變化,也沒有對政治、經濟和社會造成系統性影響,目前來看也不具備被稱為“工業革命”的條件。
工業革命界定標準的不統一性、對已有共識的排斥以及認知起點的差異造成了工業革命次第和主題定義的分歧,通過以上分析可知,爭議最大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新能源學派”“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智能制造學派”“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新能源學派”“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智能制造學派”等四個學派所定義的“新革命”不過是信息技術運用的“新領域”。我們可以把互聯網的誕生看作以信息技術為核心和標志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第一次浪潮”,把以信息技術為支撐的智能制造看作“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第二次浪潮”,把互聯網與可再生能源的結合看作“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第三次浪潮”,而且“第二次浪潮”和“第三次浪潮”融合的趨勢已經出現。至于信息技術是會給我們帶來更多的創新性浪潮,還是未來會有顛覆信息技術的新技術帶來真正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我們還須拭目以待。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