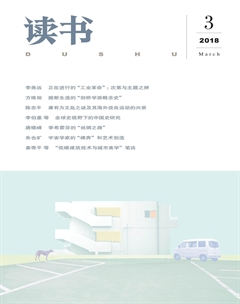人、整體史與“中國原理”
覃延佳
一九六九年的一個初春之夜,一名瘦弱的少年在稀疏的星星陪伴下摸黑疾行于粵北的山道上。此刻,他的心情異常復雜:既因好消息的傳來而興奮不已,又對黑壓壓的南嶺山脈傳來的死寂感到絲絲恐懼。在此之前的“復課鬧革命”時期,他因為被列為修正主義苗子而被剝奪了入學權利,隨父母到了大山中的“五七干校”勞動。當晚九時多,從縣城采購物資回到干校的人帶來一個口信,學校通知他明天可以回到校園了。獲知這一消息,只有十三歲的他決定獨自一人,走二十里的山路回到縣城,以便次日一早能夠準時走進中學校門。而今,當年那個瘦弱的少年,已是明清社會經濟史及歷史人類學領域的知名學者,他就是劉志偉教授。
基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九十年代所做的具有歷史人類學研究取向的努力而產出的大量成果,劉志偉和科大衛、蕭鳳霞、陳春聲、鄭振滿等研究伙伴逐漸被學界稱為“華南學派”。盡管如此,華南研究群體卻甚少對自身研究“范式”做“總結”,尤其是上升到“認識論”、普遍主義的追求方面,更是絕少提及。其緣由大致有二:其一,華南研究的群體更看重研究實踐所揭示的問題,亦即后文孫歌所言的“流動的過程”,而非理論預設或總結;其二,他們認為自身的研究與認知,總是隨著學術環境與具體實踐的變化而處于不斷變動之中,尚未抑或永遠沒有蓋棺定論之時。因此,當談到關于其研究過程中的認識論與歷史觀等大問題時,劉志偉坦言:“這樣的議題,如果要我寫文章,大概永遠寫不出來的……”正源于此,華南研究群體的很多學術見解經常被誤讀甚至曲解,由此促發包括劉志偉在內的眾多學者意識到,需要在恰當的時機對華南研究的一些基本認識進行說明。
在賀照田等人的推動下,一場被稱為“人間思想”運動之一的對談,讓我們看到了《在歷史中尋找中國:關于區域史研究認識論的對話》一書在內地的付梓(該書曾于二0一四年十一月在香港大家良友書局有限公司出版)。該書通過劉志偉和孫歌兩位不同研究領域的歷史學者之間的對談而成稿。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最有名的對談之一,恐怕非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布爾迪厄與年鑒學派新生代代表人物夏蒂埃在一九八八年的對話莫屬(《社會學家與歷史學家:布爾迪厄與夏蒂埃對話錄》)。作為學術產出方式之一的對談雖在國內甚為罕見,但在日本卻頗為盛行,而熟悉日本學界動態的孫歌明白“對談要求雙方有合作的誠意與能力,有健康的論辯意識,有把問題開放之后再重新認識的胸襟”。
既然把問題聚焦在“尋找中國”上,兩人的對話就是圍繞區域史研究中所可能呈現的“中國原理”展開。孫歌將整個對談設置為三個部分:歷史研究中的基本問題、華南研究和制度史研究的基本經驗、華南研究的原理性思考。根據這樣的設置,他們的對談在編輯成稿時分成“從國家的歷史到人的歷史”“形而下之理與普遍性想象”“從人的行為出發的制度史研究”“‘中心與‘邊緣”“局部與整體”“區域研究中的‘國家”“尋找中國原理”七個方面的內容。
對談伊始,兩人就歷史研究中的基本問題展開敘說,劉志偉在孫歌的追問下,提出歷史研究的起點應是“人”。為說明“以人的行為作為歷史解釋的邏輯出發點”這一命題,他引用施堅雅區域理論作為例子,指出施氏區域理論中的“網狀交疊層級體系”與“人之互動的空間形構”兩大概念之所以具有范式意義,是因為施堅雅是“以理性的經濟人之交換與交往行為作為論證的邏輯出發點”的,其理論有效擺脫了王朝體系與國家意識影響下的區域劃分理路,形成更具解釋性的范式。
以此為基點,兩人將話題轉向歷史研究中的普遍意義探尋問題。劉志偉的態度很明確,他是反對歷史研究追尋明確、僵化的普遍主義的。在他看來,作為歷史主體的人,“是經歷了漫長的歷史塑造出來的人,他是社會的人,具有文化的屬性,同時也只能在歷史制造的時空結構、意識形態、社會關系、文化形態和國家制度下行動,他是一個能動者,他在既有的結構下行動并創造新的結構”。面對這樣一個能動者,劉志偉所追求的“就是建立對這個結構過程的認識”。
有了這個認識論上的理解,劉志偉在總結其所開展的制度史研究時,強調具體時空中的人面對各種制度而呈現的多元行動策略,并圍繞明清賦役制度問題指出王朝國家與其“民”之間的從屬關系變化是理解明清國家運行的重要方面之一,進而強調歷史時空中的行動者在“實踐機制”方面呈現的脈絡。
在理清了相應的歷史主體認識論取向之后,兩人的對談進入到本書最為核心的部分,亦即孫歌所說的“開放你們的華南研究,讓它提供更多原理性的要素”。她首先向劉志偉提出其對中心和邊緣的問題之看法。劉志偉認為,中心一邊緣的認知結構是研究的一種表述策略,其實質并非“一種物理上的空間格局,而是由人的活動形成的一種權力關系與交往空間”。倘若以人為出發點來構建這套表述話語,我們可以構建出非常多元的中心一邊緣體系。但他更希望做的是擯棄中心一邊緣的歷史敘述結構,而僅將其視為一種歷史研究的解釋工具。
以此為對談指向,兩人的談話便具體到華南研究所揭示的整體與局部的關系問題。劉志偉對這一問題的理解異常明確,他認為“整體史是我們的一個最基本的信念”,并將整體史視為“學術研究中的一種方法論取向和價值追求”。在他看來,從歷史時空中的人出發,局部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整體,是一個由人的交往關系織造出來的整體。由此,他進一步指出,傳統中國并不存在如西歐那般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對立。國家與社會在中國歷史上是一體的,國家的在場是基層社會體系的重要方面之一。就此而論,華南研究的意義并非在于揭示作為區域的華南的特殊性抑或“典型性”,更不是以華南研究作為范式來解釋中國歷史,而是在整體史的概念下揭示一定時空中的人群行動及其相互交往關系的結構過程。
基于以上一般性問題的認知,在對談進入第六部分后,孫歌一直試圖將問題指向華南研究的普遍意義,從而更系統、更準確地找出“形而下之理”所呈現的“中國原理”。不過事與愿違,從他們的對話中,我們不難發現,劉志偉是有點抗拒談具有普遍主義意味的“中國原理”的。在他看來,如何認識中國是一條循環往復的道路,承認某種歷史研究具有普遍意義,等同于這個理論接近于無用。他始終認為,只有將人作為一切歷史問題研究的起點,這里所討論的“中國原理”作為一種流動的概念才更具解釋力。于是他坦言,他感興趣的地方在于:“如果在不同的區域,中國是一個不一樣的中國,為什么它還是中國?”這個被他視為“有點永恒味道”的問題,是其近十余年來較為關切的重要論題。endprint
不過,為了使對談更具指向性和建設性,劉志偉還是試圖換一種方式來討論華南研究的路徑與貢獻。他首先指出華德英的意識模型理論可以為我們提供認識中國歷史與社會一統性的“認識論路徑”。對他而言,意識模型理論所揭示的人群互視與自我建構路徑,正是我們理解中國為何如此多樣卻還是一個大一統中國的關鍵。華德英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他們找到了觀察傳統中國發展軌跡的最核心要素,那就是“禮儀”概念及其實踐。劉志偉認為,自宋代以來,國家的基本脈絡是以違禮的方式把“禮”擴展到基層社會。不同時期、不同區域人群主體基于“禮儀”構建出來的一套秩序結構及其演變,是中國在文化甚為多樣的情況下依舊成為大一統國家的核心所在。倘若我們將之視為一種“中國原理”,則“禮儀”概念的實踐所構筑的秩序與結構之演變過程,可使我們更好理解明清時代里的“人”之能動策略及其所構筑的意義體系。
在此意義上,華南研究群體對于宋代以來國家運行中禮儀的演變及其作用展開的探討,具有開創性意義。近十幾年來,他們已經陸續指出,禮儀的作用不僅在于為宋代以來的國家之運行提供一套儀禮規范,更在于其實踐過程中所呈現的中國社會動態運行機制。他們已經關注到,禮儀作為一種話語資源與文化象征,在歷史上不同時期透過宗族、宗教、文字、師傳等關鍵性要素成為中國不同區域人群表達自身社會與文化的重要路徑。在此過程中,作為歷史主體的人如何透過儒家文化、道教傳統、佛教文化、法師傳統等文化資源來形塑自身社會,從而為我們呈現一種“結構過程”,成為我們認識中國社會的一種重要取徑。
就文本觀察,整個對談是成功的。兩位學者通過高密度的發問與對答,呈現了以人作為歷史研究的邏輯起點之重要性,同時由此更加系統地說明了中國并非一個不言而喻的言說對象,必須置于具體的人的歷史中,它才具有核心價值與意義。該書末尾附上了二。一三年出版的一篇劉志偉的訪談。這篇訪談記錄詳細道明劉志偉所經歷的研究歷程及其核心觀點,不失為本書的一大補充。
總體而言,兩人對談的成功與前期兩者“閱讀彼此”的自覺分不開。當然,由于研究領域不同,我們也能看出兩者在一些學術觀點的表達策略上存在不同看法。對談作為一種知識回溯與生產方式,需要參與雙方有足夠的誠意和對彼此的認知才能達成,這在中國學界仍需要不斷實踐。需要指出,由于對談是一種半結構式的訪談與對話,存在諸多變數,因而本書在架構及對談過程中的重要概念和觀點表述上仍存在界定不是特別清晰的問題。讀者若想更加全面地認識對談中涉及的核心問題,就必須將對談雙方的論著拿來對比閱讀。
作為“現象”的華南研究之所以延續三十多年不間斷,與劉志偉、科大衛、鄭振滿、陳春聲、蕭鳳霞等主要成員對于學術研究認知的共同旨趣與開闊心胸分不開。科大衛在他的《告別華南研究》中說:“學者交流最好的情況是既有共同的興趣,又沒有競爭心態。我們這群人在學業上的交往,從沒有出現感情上的沖突。”
劉志偉也在本書附錄的訪談中坦言,華南研究群體既有共通性,同時也堅持自己的興趣與個性,但是他們不會追求個人的學術地位。在亂象紛紜的中國學界,華南研究群體展現了何為真正的“學術共同體”。而今,四十八年前那個匆匆趕夜路的少年,依舊用不再矯健的步伐探尋他所理解的“中國”。對于“跑”了三十多年田野的劉志偉和他的伙伴們而言,這條路永無止境。
(《在歷史中尋找中國:關于區域史研究認識論的對話》,劉志偉、孫歌著,東方出版中心二0一六年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