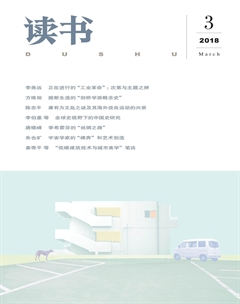為什么還要談論文學史?
張麗華
說起文學史,我們可能馬上會想到泰勒的《英國文學史》、勃蘭兌斯的《十九世紀文學主潮》等經典著作。這類勃興于十九世紀歐洲的文學史,通過將文學的發展與種族、環境、時代的語境狀況相勾連,對于塑造民族認同或是勾勒時代心理,起了重要作用。作為十九世紀廣受關注的一種知識門類,文學史的興起,與歐洲浪漫主義思潮,尤其是赫爾德、施萊格爾兄弟等人的著述密不可分。
晚清以降,文學史這一全新的著述形式,部分以日本為中介,開始進入中國。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堪稱這一領域的開山之作。一九0四年初清廷頒布的《奏定大學堂章程》規定在文學科大學專設“中國文學門”,并提醒其中的“歷代文章流別”一課,可仿日本《中國文學史》之意,“自行編纂講授”;很快,大學堂講習林傳甲即根據《章程》亦步亦趨地編出了他的這部《中國文學史》。林傳甲此書的制作方式,如同一則寓言,此后,中國學者的文學史寫作,便幾乎與大學制度結下不解之緣:無論是黃人具有世界文學視野的《中國文學史》(一九0五),還是魯迅堪稱經典的《中國小說史略》(一九二三),或者王瑤具有學科奠基意味的《中國新文學史稿》(一九五三),皆與他們在大學里的教書事業息息相關。
與眾多歐西事物的“遷地弗良”不同,文學史這一著述形式進入中國之后,很快便落地生根,而今已變得枝繁葉茂。歐洲十九世紀興盛一時的文學史,在十九世紀末即遭遇了來自審美主義的質疑;二十世紀中葉,在美國學院占據主流的“新批評”更是公然拒絕文學史;盡管后來隨著文學社會學、接受美學、新歷史主義等研究路徑的展開,文學史一度有復興之勢,但對這一學科進行理論反思的聲音,一直不絕如縷。近些年來,在日益強調“微觀”“異質”“多元”的后現代學術情境之下,試圖將文學的過去敘述成一個起承轉合的故事的文學史,其方法與前提皆飽受質疑;而在歐美大學的文學課程中,文學史也早已退出了教學的中心。然而,時至今日,名目繁多的各類文學史,如“古代文學史”“現代文學史”“當代文學史”“歐洲文學史”等等,卻依然是中國大學(尤其是中文系)文學課程中的重頭戲。大學里的課程設置自然催生出一大批文學史的教材、專著,在出版業的推波助瀾之下,文學史儼然已發展出一條擁有源源不斷的作者、產品和讀者的完整產業鏈,成為知識界難以忽視,同時也難以“消化”的龐大家族。
陳平原的近著《作為學科的文學史——文學教育的方法、途徑及境界(增訂本)》,即是基于這一問題意識、針對目前中國學界依然存在的文學史迷思,對發生在二十世紀中國的文學史與大學教育之問的“糾葛”,所做的回顧與反思之作。在作者看來,文學史在二十世紀中國的確立和演進,始終與大學教育密不可分,因此,“不只將其作為文學觀念和知識體系來描述,更作為一種教育體制來把握,方能理解這一百年中國人的‘文學史建設”(《作為學科的文學史》,507頁,下文引用此書時只注頁碼)。相對于對文學史的書寫形態和理論預設進行內在的學理探討,本書更著重于勾勒和辨析文學史在中國得以確立和發展的制度基礎,即百年中國大學教育的現代化進程。作者視野所及,從清末的京師大學堂到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北大國文系,從三十年代的民國老大學到五六十年代的臺大、港中大,從晚清教會大學的文學教授到八十年代的“北大中文四老”,幾乎是一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教育史的巡禮。該書的核心問題是:隨著中國向西式教育體系的轉化,以及一九一九年之后新文化人從文學革命轉向“整理國故”,系統化的“文學史”取代了注重“辭章之學”的傳統文學教育,這一話語體系的急遽變遷究竟是如何發生的?它對現代中國的文學研究和文學教育造成了何種影響?得失如何?以及在具體的教授與學人身上,面對此種洶涌而來的現代化大潮,又有何種應對措施?
九十年代以來,受學術史研究思潮以及福柯知識考古學的影響,對文學史書寫背后的權力、政治意識形態的探討,中文學術界已有不少專論陸續問世,如戴燕的《文學史的權力》(二00二)、陳國球的《文學史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二00四)等;此外,陳廣宏的新著《中國文學史之成立》(二0一七),則對晚清以降若干重要文學史著作的體式和來源,進行了詳盡的考辨。作為九十年代學術史研究的引領者,陳平原對文學史的關注與反思由來已久。與前述作者主要分析具體的文學史書寫文本,進而反思文學史作為一種著述形式和知識體系的利弊得失不同,陳平原對“文學史”的考察,除了學術史的視野之外,始終伴隨著教育史的維度。將教育體制引入對文學史的討論,不是理論推衍的產物,而是源于作者對二十世紀中國學術史現象的經驗觀察。收入本書的十二篇論文中,最早的一篇是作者在王瑤先生晚年主持的“近代以來學者對中國文學研究的貢獻”課題下的作品——《作為文學史家的魯迅》(一九九三),在此文中,作者通過追問魯迅晚年為何最終未能編出一部《中國文學史》,提出了如下論斷:“文學史著述基本上是一種學院派思路。這是伴隨著西式教育興起而出現的文化需求,也為新的教育體制所支持”(354頁),因此,魯迅晚年文學史著述的中斷,與其學界邊緣的位置有關。這一關于文學史著述與新式教育體制之依存關系的歷史觀察,很快上升為一種方法上的自覺;此后,在學術史和教育史的夾縫中思考“文學史”的生存處境及發展前景,成為陳平原關注這一課題的重要視角,這在他的《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一九九八)、《文學史的形成與建構》(一九九九)、《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二00五)、《假如沒有文學史……》(二0一一)等著作的相關討論中,皆有所體現;而《作為學科的文學史》(二0一一年初版,二0一六年增訂)一書,則堪稱這一方法的總結和集大成者——增訂本新增了副標題“文學教育的方法、途徑及境界”,使得這一宗旨和方法更為顯豁。
將教育史的維度引入對“文學史”之學科建構的探討,在陳平原這里,既是一種因歷史觀察而來的方法自覺,同時也包含著強烈的現實關懷。文學教育是陳平原所寄身同時又密切關注和反思的現代學院體制的重要功能之一。與文學史一樣,現代中國的大學制度,同樣是晚清以降西學東漸的產物;對這一制度的得失及其改革方向的討論,至今仍然是知識界密切關注的現實議題。對百年中國大學的歷史、現狀及出路的探究和思考,是陳平原近年來用力甚勤的領域,這不僅是他面向公眾發言的重要議題,也是他所著力經營的學術課題之一。近年來陸續出版的陳平原“大學五書”——《老北大的故事》《大學何為》《大學有精神》《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大學新語》,即是他在這一領域孜孜耕耘的成果。從這一角度來看,《作為學科的文學史》不僅可視為陳平原九十年代以來學術史研究的延續和總結,他在此書中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教育史的巡禮,對以“文學史”為中心的文學教育方式的反思,以及對何謂“理想的文學教育”的探詢,同時也構成了他面向現實發言的歷史資源和學理基礎,可以與他近年持續發出的關于中國大學改革問題的論述和建言,互相參看。endprint
《作為學科的文學史(增訂本)》所收十二篇論文,雖然撰寫時間跨度達二十余年,但被作者精心地編為三個有機板塊:第一至第四章討論文學史的學科建構與大學機構、制度的關系,從清末的京師大學堂一直說到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北大、臺大、港中大;第五至第八章著眼具體的文學史家——黃人、林紓、魯迅以及“北大中文系四老”;第九至第十二章則分別探討小說、散文、戲劇及“中國現代文學”四個專業領域的成就及拓展的可能性。與二0一一年的初版本相比,增訂本刪去了《學術講演與白話文學》一文,增加了作者近年新撰的三篇論文(分別編入第四、六、八章),論題因此更為集中和完整。
考察晚清以降以知識積累為主的“文學史”何以取代傳統的“詞章之學”成為文學教育的重心,是本書所要處理的核心主題。在作者看來,這一話語體系的轉折,“并不取決于個別文人學者的審美趣味,而是整個中國現代化進程決定的”(2頁)。本書各章的論述對象和論述視角各有不同,但對這一“現代化進程”的描述與拷問,則一以貫之。第一章《新教育與新文學》開宗明義,從林傳甲《中國文學史》對京師大學堂《章程》的適應談起,考察了文學史與大學新學制結伴而行的“緣起”;隨后在討論具體學人與專業領域時,則不時回到這一主題,如黃人在他所編撰的《普通百科新大辭典》《中國文學史》中展現出的“博學”與系統化的西學知識,與他擔任東吳大學教習這一“大學教授的事業”密不可分(第五章),而魯迅的文學史著述如《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也離不開他當時所處的學院環境(第七章);此外,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之所以成為后世戲劇研究的主流,仍然與學院體制有關:與吳梅強調戲曲唱腔、齊如山等人關心劇場和演劇實踐相比,王國維注重歷史考證與文學批評的研究路徑,更容易為后世戲劇史研究的主體——中文系教授(而非戲劇學院的學者)所青睞(第十一章)。作為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重要一翼,晚清以降從西方引進的大學教育體系,成為文學史在二十世紀中國的文學教育中占據中心地位的制度保障。
從學科、學人再到專業領域,在多層次地展示出現代教育體制如何建構“文學史”話語這一主線之外,作者對這一似乎不可抗拒的現代化進程,同時又提出了反思與質疑:“文學史”在現代學院體制中的大行其道,是否壓抑了文學教育的其他可能性?在陳平原看來,文學史對科學性與系統性的過分強調,會相對忽略文學感覺與寫作技巧,而這直接造成了文學教育中“文學性”的缺失。有鑒于此,在勾勒百年中國文學教育的歷史風貌時,陳平原不僅著眼于聚光燈下的弄潮兒,同時也注重鉤沉日益被淡忘的舊式學者、邊緣教授。第二章《知識、技能與情懷》探討的是新文化運動時期北大國文系的文學教育,面對這個幾乎群星璀璨的時代,除了討論劉師培、黃侃、魯迅、周作人這些在文學史研究上留下名篇名作的名教授,作者還通過課程講義以及學生們對文學課堂的追憶等材料尋幽探微,鉤沉和還原出“黃節說詩”“吳梅談曲”以及“劉毓盤講詞”的生動場景,這三位教授并不以文學史研究見長,但他們的文學課堂注重文學感覺與詩詞技藝的訓練,同樣吸引了不少北大學子,為二十世紀以文學史為主軸的文學教育提供了另一種選擇。第三章《“文學”如何“教育”》則干脆直接以文學課堂為中心,將視線從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北大國文系拓展開去,選取了近現代教育史上九個精彩片段,從文學學科建立以前的書院講學,一直到五十年代北大師生的文學史集體寫作,通過大量的回憶資料,追懷和重構出包括康有為、章太炎、魯迅、朱自清、胡小石、汪辟疆、沈從文、顧隨、錢穆、臺靜農等不同時期、不同派別的教授們多姿多彩的文學課堂風貌。這里,既有傳統的書院大儒,也有建立經典文學史論述的文學史大家,還有講究趣味、流連詩酒的文人雅士,以及以小說家、詞人等身份登上講臺的文學教授。對這些各有千秋的文學課堂的發掘與重構,用作者自己的話說,“既是歷史研究,也是現實訴求”(《增訂本序》,4頁),目的是為了將當下的文學教育從“文學史”的迷思中喚醒,賦予文學教育以應有的“溫情”“詩意”與“想象力”。
在描述和拷問“作為學科的文學史”在二十世紀中國得以形成和建構的現代化進程之外,本書讀起來最令筆者感到興味盎然的是,在這一宏大視野之下,作者對身處這一進程之中的個體的處境、命運及其應對之道,有著極富溫情與想象力的體察與描摹。第六章《古文傳授的現代命運》是作者收入本書的最新一篇論文,它饒有興味地講述了林紓這位新舊交替時代的文人與作為現代大學堂的北京大學之問“離合悲歡”的故事。在以往關于“文學革命”或新文化運動的回憶和論述中,林紓往往作為反面人物出現,他與蔡元培及新文化人的論戰、交鋒,顯得十分突兀且可笑而可鄙。本文則一反常規,將林紓作為故事的主人公,并將時間上溯至清末京師大學堂時期,通過對林紓“何時入職大學堂”“被解聘的恥辱”等具體細節和緣由的考證,為其日后“至死必伸其說”以及與新文化人愈演愈烈的沖突,提供了體貼入微的闡釋。經過抽絲剝繭式的考證和論述,作者令人信服地向我們展示,林紓與北京大學之問的恩怨與沖突,除了具體的人事關系及自身的性格因素之外,還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即本書作為核心議題來處理的“文學教育的重心,由技能訓練的‘詞章之學,轉為知識積累的‘文學史”這一不可抗拒的現代化進程——在新的教學體系中,林紓的“古文辭”開始派不上用場,他的去職以及隨后與新文化人的沖突,皆已在此埋下伏筆。這一章的寫法堪稱個案研究與進程描述的完美結合:表面上敘述的是林紓的個人命運及其與北京大學之間跌宕起伏的故事,背后則指向現代中國文化、思想與教育的艱難轉型。在此,我們也充分領略到陳平原史學研究的特質:他對歷史進程的描述,并不停留在抽象的概念層面,而是力圖由眾多的文本、細節、個案賦予歷史以鮮活的血肉和生動的形象。
對細節與個體的關注,既是史學方法,同時也是人文情懷。盡管《作為學科的文學史(增訂本)》是一部著眼于知識考掘的學科史專著,探討的是現代大學教育對“文學史”的制度形構,但作為個體的“人”的主體性,并沒有被淹沒在“制度”之中。作者在《增訂本序》中指出:“過去談學科建設,對學問背后的政治關注不夠;現在則反過來,受福柯影響,滿眼看過去,‘知識全都變成了‘權力,這同樣是一種遮蔽。”(2-3頁)正是基于這種對“理論”的警惕與反省,本書通過貼近歷史原生態的細節考訂與高超的敘事技藝,描摹了眾多栩栩如生的人物群像,充分釋放出個體在歷史進程之中的能動性以及歷史本身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值得注意的是,與趨新的、主流的學者相比,在本書中作者對提供了“另一種選擇”的舊式文人、邊緣教授,甚至投入了更多的關注。在筆者看來,這既是一種敘述策略,即避免將中國文化與教育的現代轉型,描述成一幅清晰的整體化圖景;同時,這一選擇本身,也構成了著者自身對走向“文學史”這一似乎不可抗拒的歷史大潮的質詢與抵抗。
作為專業學者,陳平原自身的學術研究早已走出文學史的范疇,近年來,他在圖像、聲音、大學以及都市研究等領域不斷施展拳腳,為“中國現代文學”學科開辟了不少新方法與新路徑;然而,作為一位文學教育者,反省并打破當下知識界與大學課程中依然彌漫不去的“文學史”迷思,乃其責任。為了尋找當下文學教育的出路,作者將眼光投向了歷史。讀完《作為學科的文學史(增訂本)》一書,筆者充分體會到作者投向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溫情”目光:既有反思與批判,也有“了解之同情”,還有為了應對當下的現實處境所進行的追懷與重構。對于文學究竟應該如何教育,本書沒有給出直接的答案,但以史為鑒,我們可以追隨著作者所勾勒和發掘的眾多大時代中的人物與故事,不斷展開思考。
(《作為學科的文學史——文學教育的方法、途徑及境界[增訂本]》,陳平原著,北京大學出版社二0一六年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