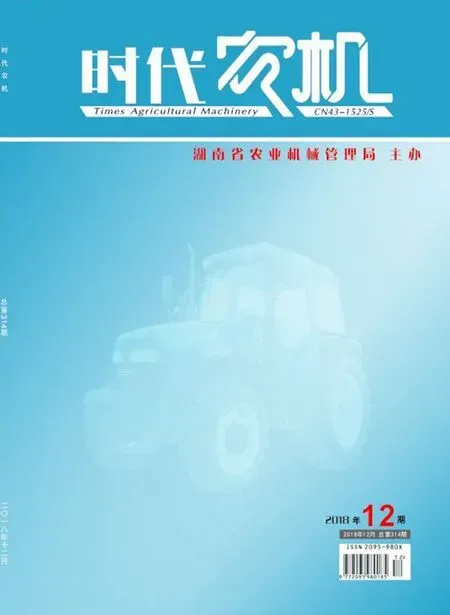淺析明清時期分成租制向定額租制演化的原因及影響
劉英英
(鄭州市科技工業學校,河南 鄭州 450000)
1 概述分成租制和定額租制
地主和佃農的關系是封建社會重要的經濟關系,雙方的關系通過租佃制度表現出來。明清時期地主和佃農的關系主要表現為分成租制向定額租制的演化。分成租和定額租都是中國封建地租剝削的一種形態。
在分成租制下,租佃農民按照農田收獲量的一定比例向地主繳納地租,在中國封建社會,分成租制很普遍,秦漢“見稅什五”,即租種土地的農民把農田產品的一半交給田主作為地租。此后,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分成租制在租佃制度中占主要地位。分成租制以主佃對半均分最為普遍,但也有主六佃四,主七佃三或者主四佃七,主三佃七,甚至比率更懸殊的。如何分成,往往與誰提供生產資料有關系。此外,與土地肥瘠、地權集中程度、人口密度也有關系。一般來說,佃農自備耕蓄、農具的,多為主佃對半均分;地主供給肥料、種子,佃戶自備耕畜、農具的,佃戶要繳納農田產品的六七成;地主供給肥料、種子、耕畜、農具,佃戶只出勞力的,主八佃二。
2 分成租制向定額租制演化的原因
2.1 農業生產力的發展
分成租制向定額租制的轉變是農業生產力發展的結果。高產穩產的田地增多,佃農能夠支付全部生產資料以及經營成本,為實行定額租制準備了條件。明清時期農業生產力的發展表現在很多方面,如農業技術的改進,新的生產工具的發明創造,水利灌溉事業的興修推廣等。李文治先生在《明清時代封建土地關系的松解》中以安徽休寧縣吳蓀園祀產為例考察同一塊耕地單位面積產量增長的問題,以1680-1693 年的13 年為前期,1694-1705 年的11 年為后期,通過前后兩期的對比,發現田地的地租量有所增加,在前后24 年間,分成地租制并沒有改變,但地租量增加,這是單位面積產量增加的結果。產量增長,使主佃雙方的收入都有所增加。寧可先生主編的《中國經濟發展史》也認為定額租制的發展與農業生產力的水平和佃農的自由經濟完備程度密切相關,只有農業生產力提高到一定水平,土地畝產量已經比較穩定,地主才有可能將分租制改變為定額租制。中國的生態條件不好,農業生產的風險高,過去由于生產力不發達,再加上佃農經濟條件差,承擔風險的能力也很低,分租制下是主佃雙發共同承擔風險。生產力的發展使佃農戰勝自然災害的能力增強,農業生產力的發展提高了佃農承擔風險的能力,為分租制向定額租制的轉變創造可能。
2.2 地主為了增加租額
單位面積產量提高,地主企圖把增產部分全部攫為己有,限于舊有的慣例,又不能改變分成租的比例。在人多地少的情況下,租佃方式與地租額完全是由地主決定的,佃農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于是地主通過改分成租為定額租的方式來提高地租額。在向定額租過渡之后,地租剝削率都有所增長。在定額租制下,租額的制定本來應該是“計數歲之中以為常,豐年不增,兇年亦不減”,但在很多情況下,租額并不是“計數歲之中以為常”,而是“大約計豐年所收各得其半以為常”,即定額租的租額是豐年產量的一半,但是豐收之年不常有,甚至很少,地租剝削率實際上遠遠超過分成租制下的50%,如果遭遇歉收之年,地主會按照定額收租,把因歉收而造成的損失全部轉嫁到佃農身上。地主甚至可以獲得因歉收而谷價上漲的額外收益。通過把分成租制改為定額租制的方式,地主達到了增加租額的目的。
2.3 經濟作物的推廣
明清時期經濟作物得到了推廣,而經濟作物的價值要高于糧食作物,如棉花是“利倍于谷”,其他經濟作物如甘蔗、煙、蠶桑也是如此。但是各地地租仍然是繳納糧食。在分租制下,地主會直接干涉佃農種植什么作物,而佃農又無力反對,但是定額租制下,地主一般不會再過問佃農種植什么,只要他們能按時按量的繳納地租就行,因此佃農有一定的經營自由,可以種植價值較高的經濟作物來增加自己的收入。隨著價值較高的經濟作物的推廣,佃農也產生了實行定額租制的愿望。
3 分成租制向定額租制演化的影響
3.1 提高佃農生產積極性
在分成租制下,佃農因增加投入而獲得的增產部分都要與地主平分,而在定額租制下,租額固定不變。相對于前者,佃農獨立經營的優越性比較能夠發揮,他們更關心改進生產技術、改良作物品種、使用肥料等,更愿意多投入勞動,因為由此獲得的增產部分全歸佃農所有,這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佃農的生產積極性,對生產力的發展是有利的。
3.2 沖擊小農經濟
在分租制下,地租量與農田經營好壞相關,地主為了獲得更多地租,會干預佃農的生產活動,包括作物種植品種等等。種什么作物,怎樣經營、管理乃至收割莊稼等方面,地主都直接干涉。每當作物成熟時,地主都要臨田監督收割,如果佃農不通知地主而自行收割莊稼,就會被視為“非法”,可能會被奪佃,甚至被毆打致死。在這種情況下,佃農難以發揮獨立經營的優越性,不利于生產積極性的發揮。而實行定額租制以后,地主所關心的是每年所規定的租額能否交清,至于種植什么作物,如何經營等等,地主一般不過問。
3.3 削弱佃農和地主的人身依附關系
除了對佃農的農業生產進行控制以外,在分成租制下,地主對佃農還進行超經濟強制,比如地主家有婚喪喜慶等事,佃農要到地主家服役;在莊稼收割以后,佃農還要把屬于地主的那一部分收成送到家,主佃之間保留有勞役地租的殘余。實行定額租制以后,上述情況發生了改變,這時佃農一般都有自己的生產工具,生產獨立性有所加強,隨著經濟上的獨立,農民獲得了更多的人身自由,佃農除交租外,一般不為地主服役,不用再為地主送租上門。這時的租佃關系開始由封建依附關系向單純的納租義務過度。定額租制削弱了佃農和地主的人身依附關系。
3.4 加重佃農負擔
定額租租額往往高于分成租的足額,而且農業生產的的風險完全是由佃農承擔的,豐收年份,佃農的負擔就輕一些,災年,佃農的負擔就會加重。而地租一般不會隨豐歉年份的變化而變化,一遇歉收年景,佃農往往要以農田以外的收入,甚至出賣耕牛來繳納地租,而且定額租制下,地主增加地租的情況還經常發生,更加重了佃農的負擔。
3.5 促進在城地主的增加
定額租制的發展促進了在城地主的增加。定額租制實行,地主不必管農田中的實際情況,也不必像分成租那樣監分監收,只要坐收租額就好,地主也不必親自收取地租,可委托代人收租的專業代理商去辦理。因此許多地主就遷入城中居住,成為不在地地主。
4 結 語
在分成租制下,主佃雙方是合伙經營,雙方共同投入生產要素,共負盈虧,根據雙方投入的多少而分配收成;而在定額租制下,佃農付給地主地租而購買土地在某一段時間的使用權。土地的所有權與經營權逐漸分離,隨著押租制和永佃權的發展,土地經營權進入市場,走向貨幣化和商品化,這也是貨幣地租出現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