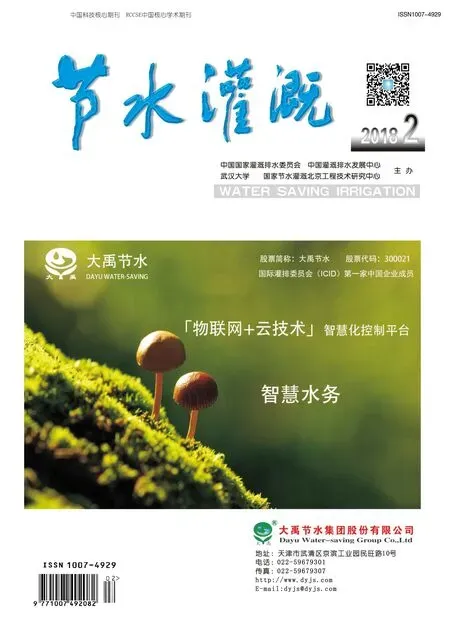秸稈覆蓋對夏玉米土壤溫度和硝態氮的影響
申勝龍,李援農,銀敏華,張 敏,趙 祥
(1.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水利與建筑工程學院,陜西 楊凌 712100;2.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旱區農業水土工程教育部重點實驗室,陜西 楊凌 712100)
中國是世界第一秸稈大國[1],秸稈的有效利用對改善耕作層土壤結構、提高土壤中有機質含量和保護環境、增加農民收入具有重要作用。自1936年開展試驗研究并推廣應用[2]以來,秸稈覆蓋技術以其調節土壤水分狀況[3],平抑土壤溫度[4],改善土壤團聚結構[5],為作物提供良好生長環境[3-6]的優點在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區得到廣泛采用。
然而,目前對秸稈覆蓋的定量研究尚存在一定爭議,主要表現在作物生育期土壤溫度動態變化對水分保蓄的影響[7,8],覆蓋前期“低溫效應”對作物生長發育的影響[9]以及覆蓋對最終產量的貢獻率大小[10,11],但在作物生長必需的水、肥、氣、熱及微生物活動因素中,熱能及養分鮮有報道,且當下的定量研究主要針對平作條件下一元覆蓋,而對壟溝二元覆蓋下秸稈覆蓋量的研究相對較少。不同學者將壟溝二元覆蓋條件下作物產量,土壤水分等與其他種植方式對比得出的結論存在較大差異[12-15],這種差異的來源可能是由于不同地區氣候條件、覆蓋時期或降雨量的差異導致,但通過大量調查研究發現,差異的來源還與在進行二元覆蓋時確定的秸稈覆蓋量不同有關。因此,對二元覆蓋下不同秸稈量導致的溫度變化及養分積累的差異進行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通過田間試驗,以平作不覆蓋為對照,設置壟溝二元覆蓋下4種秸稈量差異來探求該種植模式下秸稈量對夏玉米土壤溫度動態變化,土壤硝態氮分布的影響,以期為壟溝種植模式下秸稈和養分的有效利用提供理論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試驗地概況
本試驗在陜西省楊凌區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北校區旱區農業水土工程教育部重點實驗室灌溉試驗站進行,試驗站地處北緯34°17′38″,東經108°04′08″,海拔521 m,地勢平坦開闊,光熱資源充足,年日照時數2527.1 h,年平均氣溫13 ℃,多年平均蒸發量1 500 mm,年平均降水量632 mm,主要集中于7-9月,且降水年內季節分配不均,7-9月降水占全年降水量的70%左右,地下水埋深80 m,屬于半濕潤易旱地區,試驗土壤質地為壤土。試驗站內設有縣級自動氣象站。土壤基本理化性質:容重1.45 g/cm3,有機質16.02 g/kg,速效磷13.67 mg/kg,速效鉀182.30 mg/kg,全氮0.88 g/kg,堿解氮52.2 mg/kg,pH值8.22。
1.2 試驗布置與設計
試驗玉米品種為漯單9號,生物質膜為寬100 cm,厚0.008 mm,秸稈為前茬小麥秸稈,平均長度10 cm,供試肥料為尿素(總氮含量46%)、氧化鉀(K2O質量分數50.0%)、過磷酸鈣(有效P2O5含量≥16.0%)
本試驗于2016年6-10月在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北校區旱區農業水土工程教育部重點實驗室灌溉試驗站進行。試驗在壟覆薄膜,溝覆秸稈條件下,按秸稈覆蓋量設置4個處理,即2 500(MG1)、5 000(MG2)、7 500(MG3)和10 000(MG4) kg/hm2,以平地無覆蓋為對照(CK)。小區寬3.5 m、長4 m,所有小區隨機分布,每個小區兩邊設有保護行。所有小區壟寬60 cm、壟高25 cm、溝寬60 cm。于2016年6月11日播種,2016年9月27日收獲,株距28 cm,行距60 cm,采用人工穴播,每穴2顆。播前2天施肥翻耕,施肥量為氮肥120 kg/hm2,磷肥120 kg/hm2,鉀肥60 kg/hm2。除草、殺蟲等均按一般大田管理措施完成。
1.3 測定項目與方法
地溫測定:采用德圖 Testo 105(-50 ℃~+275 ℃)手握式溫度計,按照前、中、后3個階段在夏玉米苗期(播種后18~20 d),大喇叭口期(播種后48~50 d),成熟期(播種后93~95 d)測定玉米根部溫度,測量時間為8∶00-18∶00,每隔2 h測定一次,測量深度為0、5、10、15、20 cm,以連續3 d平均值為該點溫度,日平均氣溫取0~20 cm平均溫度[16]。
土壤硝態氮測定:夏玉米成熟期(收獲)測量0~200 cm土層土壤硝態氮含量,取土方式采用土鉆法取土,以10 cm為一層,取土位置為小區內部相鄰兩株玉米中間區域。待自然風干后過2 mm篩網,并稱取5 g土樣,用50 mL的氯化鉀溶液(2 mol/L)浸提震蕩0.5 h后過濾,用紫外分光光度計測定土樣硝態氮含量,其計算公式[17]為:
Cs=cVD/m
(1)
式中:Cs為土壤硝態氮含量,mg/kg;c為溶液中硝態氮濃度,mg/L;V為浸提液體積,mL;D為稀釋倍數,不稀釋為1;m為烘干土樣重,g。
1.4 數據處理與統計分析
采用Excel2007進行數據整理;SPSS 21.0進行數據統計分析,方差分析使用最小顯著差異(LSD)進行;Origin9.0進行繪圖處理。
2 結果與分析
2.1 不同處理對土壤溫度空間變化的影響
夏玉米前期由于植株矮小,棵間蒸發作用較強,秸稈覆蓋表現出明顯“低溫效應”,土壤溫度表現為各處理間淺層溫度差異大于深層,如圖1(a)所示。中期植株進入旺盛生長階段,遮陰面積增加,此階段土壤溫度差異的決定因素由覆蓋量轉變為植株長勢,但由于覆蓋處理前期的保水作用從而為中期植株生長提供良好的水分條件,因而表現為同一土層內溫度隨秸稈覆蓋量增加而降低的趨勢,各處理間溫度差異逐漸縮小,如圖1(b)所示。進入生育后期,氣溫較前期、中期逐漸下降,覆蓋處理各層平均溫度均低于前期、中期,同時麥秸腐化隨生育過程的推進而加劇,不同處理間溫度差異較中期進一步減小,如圖1(c)所示。

圖1 不同處理對土壤溫度空間變化的影響Fig.1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spatial variation of soil temperature
由圖1分析知,根區土壤溫度變化隨秸稈覆蓋量增加和土層深度的加深而降低,前期各處理間溫度差異隨土層深度加深而減小。0 cm處土壤溫度差異最大,MG1、MG2、MG3和MG4較CK分別降低1.59、3.64、4.95和5.18 ℃,其中MG2、MG3和MG4較CK差異顯著(P<0.05),MG3和MG4較其余3個處理均顯著(P<0.05),5 cm處變化趨勢同0 cm處。當土層深度大于10 cm時,土壤溫度隨土層深度的加深變化不再明顯,但不同覆蓋量之間仍存在顯著差異。10~20 cm區域內MG1、MG2、MG3和MG4平均溫度較CK分別降低1.42、1.65、2.66和2.93 ℃,MG3和MG4較CK差異顯著(P<0.05)。
中期及后期不同覆蓋量下根區土壤溫度差異減小,且溫差最大區域較前期明顯下移,表現為5 cm處各處理間溫度差異最大。MG1、MG2、MG3和MG4在5 cm處土壤溫度中期較CK分別降低0.70、2.66、2.95和3.86 ℃,末期較CK分別降低0.60、2.67、2.90和3.51 ℃,且MG2、MG3和MG4較CK均達到顯著差異(P<0.05)。0 cm處與10 cm處溫差變化接近,中期為0.55~2.79和0.27~2.14 ℃,末期為0.11~2.35和0.20~2.33 ℃。
2.2 不同處理對土壤溫度時間變化的影響
前期由于地表裸露較大,土壤溫度隨時間變化差異明顯,且各處理間差異顯著,如圖2(a)所示,隨植株生長,中期溫度差異逐漸減小,但溫度峰值后移,且峰值附近溫度變化劇烈程度小于覆蓋前期,如圖2(b)所示,后期由于氣溫降低,各時間點溫度均低于前期、中期,土壤溫度隨時間變化趨勢同覆蓋中期,如圖2(c)所示。

圖2 不同處理對土壤溫度時間變化的影響Fig.2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time variation of soil temperature
由圖2(a)分析知,秸稈覆蓋“穩溫效應”隨覆蓋量增加而增強,土壤溫度峰值為14∶00處。測量時段內溫度差異CK最大,為16.9 ℃,MG1、MG2、MG3和MG4溫差逐漸減小,為14.1、9.2、8.1和7.3 ℃,其中MG2、MG3和MG4較CK差異顯著(P<0.05)。MG2、MG3和MG4處理日平均土壤溫度較CK同樣差異顯著(P<0.05),分別降低3.2、4.6和4.8 ℃。圖2(b)表明,中期由于夏玉米生長旺盛,遮陰效果較強,各處理峰值溫度均低于前期,且由于該時期田間郁閉,空氣流動性差及秸稈覆蓋的滯后作用,土壤溫度峰值較前期推遲,MG3和MG4均在16∶00處達到最大。MG3和MG4處理日平均氣溫較CK差異顯著(P<0.05),分別低1.6和2.1 ℃。圖2(c)表明,后期植株逐漸衰老,加之氣溫逐漸下降,各處理日平均土壤溫度達到最低,分別為24.2、23.9、23.78、22.8和22.1 ℃,其中MG3、MG4處理較對照差異顯著(P<0.05)。
2.3 不同處理對土壤硝態氮分布的影響
氮素是作物生長需求量最多,對產量形成貢獻最大的營養元素,硝態氮作為能直接被作物吸收的礦質態氮,其在土壤中的分布對植株生長具有重大意義。收獲期0~200 cm土層土壤硝態氮分布如圖3所示。

圖3 不同處理對土壤硝態氮分布的影響Fig.3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distribution of nitrate nitrogen
由圖3分析知,夏玉米生育末期土壤硝態氮質量含量隨土層深度呈“>”型變化,各處理0~40 cm變化較為平緩(14.78~20.12 mg/kg),40~140 cm變化幅度較大(15.37~32.92 mg/kg),140~200 cm變化幅度介于前兩層之間(9.73~18.76 mg/kg)。同時,由于覆蓋量的差異致使在淋洗作用下硝態氮含量的峰值有所不同,MG1、MG2、MG3和MG4較CK分別低20、30、40和40 cm。
為進一步探索覆蓋量作用下硝態氮分布,將0~200 cm土層以40 cm為間隔,研究該層內硝態氮含量占土壤硝態氮總量的比例,如表1所示。

表1 各層土壤硝態氮占0~200 cm總硝態氮的比例 %
由表1分析知,0~80 cm土層內土壤硝態氮所占比例隨覆蓋量的增加而減小,MG1、MG2、MG3和MG4較CK平均降低5.55 %、12.18 %、18.71 %和19.89 % 。80~200 cm土層內土壤硝態氮所占比例隨覆蓋量的增加而增加,各處理較CK平均增加4.81 %、9.58 %、13.22 %和13.80 % ,其中MG2、MG3和MG4在0~80和80~200 cm較CK均差異顯著(P<0.05)。
3 討 論
(1)秸稈覆蓋對土壤溫度的影響。秸稈覆蓋通過減少太陽的直接輻射,增強光波反射,同時降低土壤熱量向大氣散發,從而抑制極端溫度,使土壤溫度趨于緩和,為作物根系提供良好的生長環境,同時又促進微生物活動,防止土壤板結,提高肥效。大量研究表明,秸稈覆蓋能夠平抑土壤溫度,降低對作物的傷害作用,且平抑作用隨覆蓋量的增加而增強,本研究結果表明,前期MG1、MG2、MG3和MG4在8∶00-18∶00溫度差較CK分別降低2.8、7.7、8.8和9.6 ℃,這與前人研究結論基本一致[18]。朱自璽等[19]研究發現4 500 kg/hm2的麥秸覆蓋下土壤溫度較對照降低2.3 ℃,而本研究設置的5 000 kg/hm2處理平均土壤溫度降低1.6 ℃,降溫幅度略低,這可能與觀測時間及氣候條件差異有關。于曉蕾等[20]對小麥的覆蓋研究發現,覆蓋秸稈既能抑制地溫過快上升或迅速下降,土壤溫度變化速率隨覆蓋量的增加而降低,這與本研究前期試驗結果相似,但中后期尤其是午后時段各覆蓋處理溫度變化速率差異不顯著,這可能由于中后期植株旺長,遮陰面積較大對熱量傳導產生抑制作用有關。張俊鵬[4]研究發現秸稈覆蓋處理溫度峰值出現時間晚于不覆蓋,本研究中后期部分處理也出現類似現象,即溫度峰值的滯后性,這是由于秸稈覆蓋提供相對封閉的環境,在大氣溫度降低時繼續累積導致,同時該研究認為,當秸稈覆蓋量增加至7 500 kg/hm2時,地溫趨于穩定[18],劉超等[21]研究發現覆蓋量介于6 000~9 000 kg/hm2時覆蓋效果最明顯,本文通過比較MG2(5 000 kg/hm2)、MG3(7 500 kg/hm2)和MG4(10 000 kg/hm2)處理發現,MG2和MG3土壤溫度日變化差異顯著,而MG3和MG4差異不顯著,與前人研究結論一致。蔡太義等[18]研究發現秸稈覆蓋的低溫效應隨玉米生育期進程的推進而減弱,且0~15 cm處差異最大,本研究通過對不同時期0~20 cm土壤溫度研究發現,前期0 cm處溫度差異最大(與朱自璽研究結果一致),中后期5 cm處差異最為明顯(與蔡太義研究結果一致),即覆蓋量對溫度的調控主要在5 cm處,但整體表現為溫度隨土層深度增加差異逐漸減小的趨勢。也有學者研究發現生育后期秸稈覆蓋會產生微弱的“增溫效應”,而本研究未出現該現象,這可能與地區氣溫差異有關。
(2)秸稈覆蓋對土壤硝態氮含量的影響。土壤養分對玉米生育進程的推進至關重要,并且決定著作物產量的高低,高亞軍[22]研究認為,壟溝覆蓋種植與常規覆蓋相比,能顯著提高作物對氮素的吸收利用,但同時增加土壤硝態氮殘留,本研究收獲期0~200 cm土壤硝態氮含量較對照分別高7.80%、9.23%、15.03%和14.90%,且表現為隨著覆蓋量增加,硝態氮殘留量呈逐漸增加的趨勢。本研究通過對收獲期硝態氮隨土層深度變化的研究發現,不同覆蓋下硝態氮含量有所差異,有研究指出[23,24],覆蓋下土壤淺層硝態氮含量小于不覆蓋,而深層大于不覆蓋,本研究通過比較得出,硝態氮含量0~80 cm較對照低5.55%~19.89%,80~200 cm較對照高4.81%~13.80%,主要由于覆蓋促進作物生長及對淺層養分吸收利用,而深層硝態氮含量高于不覆蓋是淋洗作用所致。周昌明等[25]發現壟溝半覆蓋下硝態氮峰值位于120~140 cm,但銀敏華[17]研究指出壟溝半覆蓋下硝態氮峰值在70~80 cm處,而壟覆薄膜溝覆秸稈(4 500 kg/hm2)種植條件下硝態氮含量明顯下移至140~160 cm處,本研究發現秸稈覆蓋下硝態氮峰值在80~100 cm處,研究結果各有差異,這不僅與作物生育期內降水量有關,還可能與某次降雨強度及作物種類有關,因此水分對硝態氮的淋洗作用還需進一步研究。
4 結 語
(1)秸稈覆蓋能顯著降低生育期內平均土壤溫度及變化速率,與對照相比,MG1、MG2、MG3和MG4全生育期8∶00-18∶00平均土壤溫度降低0.5、1.6、2.5和3.0 ℃,夏玉米生育前期平抑地溫作用大于后期,且覆蓋量越大,平抑地溫效果越明顯。
(2)覆蓋作用對土壤溫度的影響主要表現在0~10 cm處,其中5 cm處溫差最大,該處與對照相比,MG1、MG2、MG3和MG4生育期內平均土壤溫度降低0.54、2.08、3.04和3.51 ℃,從而有效抑制夏玉米生育期高溫作用的影響,為作物提供適宜的生長環境。
(3)作物吸收利用及水分淋洗共同作用下,土壤硝態氮含量淺層較對照分別降低5.55%、12.18%、18.71%和19.89% ,深層較對照分別增加4.81%、9.58%、13.22%和13.80% ,且土壤剖面中硝態氮含量峰值較對照下移20、30、40和40 cm。
[1] 畢于運,高春雨,王亞靜,等. 中國秸稈資源數量估算[J].農業工程學報,2009,25(12):211-217.
[2] Hallsted A ,Mathews O. Soil moisture and winter wheat with suggestions on abandonment[M].Manhattan Kan: Agrie. Exp. Sta.,1936.
[3] 肖繼兵,楊久廷,辛宗緒.遼西地區秸稈覆蓋試驗研究[J].節水灌溉,2008,(1):8-10.
[4] 張俊鵬,孫景生,劉祖貴,等. 不同麥秸稈覆蓋量對夏玉米田棵間土壤蒸發和地溫的影響[J].干旱地區農業研究,2009,27(1):95-102.
[5] 盧星航,史海濱,李瑞平,等. 覆蓋后秋澆對翌年春玉米生育期水熱鹽及產量的影響[J].農業工程學報,2017,33(1):148-154.
[6] 張金珠,虎膽·吐馬爾白,王振華. 秸稈覆蓋對滴灌棉花土壤鹽分分布的調控影響[J].節水灌溉,2012,(7):26-28.
[7] 王罕博,龔枝道,梅旭榮,等.覆膜和露地旱作春玉米生長與蒸散動態比較[J].農業工程學報,2012,28(22):88-94.
[8] 王兆偉,郝衛平,龔道枝,等. 秸稈覆蓋量對農田土壤水分和溫度動態的影響[J].中國農業氣象,2010,31(2):244-250.
[9] 李 榮,王 敏,賈志寬,等. 渭北旱塬區不同溝壟覆蓋模式對春玉米土壤溫度、水分及產量的影響[J].農業工程學報,2012,28(2):106-113.
[10] 李立群,薛少平,王虎全,等. 渭北高原旱地春玉米不同種植模式水溫效應及增產效益研究[J].干旱地區農業研究,2006,24(1):33-38.
[11] 銀敏華,李援農,張天樂,等. 集雨模式對農田土壤水熱狀況與水分利用效率的影響[J].農業機械學報,2015,46(12):194-203.
[12] 張開乾,鄭立龍. 隴中半干旱地區地膜覆蓋和補灌對玉米及土壤溫濕度的影響[J].節水灌溉,2016,(2):61-65.
[13] 卜玉山,苗果園,邵海林,等. 對地膜和秸稈覆蓋玉米生長發育與產量的分析[J].作物學報,2006,32(1): 1 090-1 093.
[14] 馬 龍,毛全年,李 強,等. 涇惠渠灌區秸稈還田條件下夏玉米節水灌溉制度試驗[J].節水灌溉,2016,(3):15-20.
[15] 胡亞瑾,吳淑芳,馮 浩,等. 覆蓋方式對夏玉米土壤水分和產量的影響[J].中國農業氣象,2015,36(6):699-708.
[16] 時學雙,李法虎,普布多吉,等. 秸稈覆蓋對高海拔寒區土壤溫度和春青稞生長的影響[J].農業機械學報,2016,47(2):151-160.
[17] 銀敏華,李援農,李 昊,等.壟覆黑膜溝覆秸稈促進夏玉米生長及養分吸收[J].農業工程學報,2015,31(22):122-130.
[18] 蔡太義,陳志超,黃慧娟,等.不同秸稈覆蓋模式下農田土壤水溫效應研究[J].農業環境科學學報,2013,32(7):1 396-1 404.
[19] 朱自璽,方文松,趙國強,等.麥秸和殘茬覆蓋對夏玉米農田小氣候的影響[J].干旱地區農業研究,2000,18(2):19-24.
[20] 于曉蕾,吳普特,汪有科,等. 不同秸稈覆蓋量對冬小麥生理及土壤溫、濕狀況的影響[J].灌溉排水學報,2007,26(4):41-44.
[21] 劉 超,汪有科,湛景武,等. 秸稈覆蓋量對農田土面蒸發的影響[J].中國農學通報,2008,24(5):448-451.
[22] 高亞軍,李 云,李生秀,等. 旱地小麥不同栽培條件對土壤硝態氮殘留的影響[J].生態學報,2005,25(11):2 901-2 910.
[23] 劉立軍,桑大志,劉翠蓮,等. 實時實地氮肥管理對水稻產量和氮素利用效率的影響[J].中國農業科學,2003,33(12):2 282-2 291.
[24] 周麗娜,雷金銀. 覆膜方式對坡耕地春玉米產量、土壤水分和養分的影響[J].中國農學通報,2014,30(33):20-25.
[25] 周昌明,李援農,谷曉博,等. 降解膜覆蓋種植方式對夏玉米土壤養分和氮素利用的影響[J].農業機械學報,2016,47(2):133-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