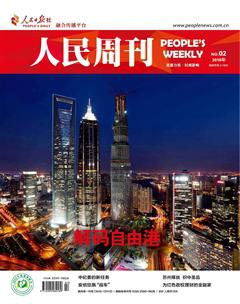網絡游戲:毒藥還是榮耀
頗具戲劇性的是,在輿論對網游口誅筆伐之時,以網游為載體的電子競技卻開始“登堂入室”。亞運會、亞洲室內和武藝運動會等賽事,都在2017年宣布將電競作為比賽項目。
從《王者榮耀》點燃手游市場到《絕地求生》《荒野行動》等網游引發全網“吃雞”(游戲術語,指奪取勝利),2017年中國網絡游戲市場“爆款”頻出,產業規模及影響力不斷擴大,甚至已超越出版、電影等在文化產業中的份額;而與此同時,有關游戲的爭論也從未止息。
一方面,讓玩家欲罷不能的“爆款”游戲動輒被貼上“精神鴉片”“電子毒品”等標簽;另一方面,以游戲為載體的電子競技登堂入室,躋身亞運會等大型運動會官方比賽項目之列……簡單粗暴地對游戲進行定性,作出“好東西還是壞東西”的價值評判似乎行不通。
在學者眼中,網游引發的輿論撕裂背后,暗藏著互聯網時代背景下,媒介迭代及受眾迭代所帶來的深層次文化挑戰。《王者榮耀》等游戲的走紅,也反映了網民結構及其心理需求的變化。虛擬的游戲已經與現實生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并且共同影響著社會的各個領域。
我們究竟該如何理性地面對這個飛速成長的新興產業及其背后的玩家群體?
悖論:“精神鴉片”也能為國爭光?
近年來,中國網絡游戲市場越來越火爆,典型代表是一款名為《王者榮耀》的手機游戲。在游戲中,玩家們可以自由選擇根據歷史人物、神話人物改編的角色,組成不同陣營,在一張地圖上進行對抗,哪方先摧毀對方基地就算獲勝。
《王者榮耀》具有目前流行手游的幾大突出特征:一是碎片化,每一局游戲的耗時都不長,玩家可以即開即玩;二是強調對抗,在不同陣營的比拼中追求感官刺激;三是多使用戲謔的方式表現內容,比如將歷史人物與神話人物進行改編。這些特征及背后的社會文化傾向,值得關注與研究。
一段時期以來,社會各界對《王者榮耀》的批評,大概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對游戲本身的批評。比如,有媒體曾譴責這款游戲不尊重歷史,理由是它把荊軻改成了女性;再如,有媒體譴責游戲的內涵淺薄,怕它會把孩子教壞。
另一個層次的批評,則已不再局限于《王者榮耀》這一款游戲,而是給所有網游貼上的負面標簽。熟悉網絡游戲及網游產業的人都知道,這樣的批評其實有些危言聳聽。
頗具戲劇性的是,在輿論對網游口誅筆伐之時,以網游為載體的電子競技卻開始“登堂入室”。亞運會、亞洲室內和武藝運動會等賽事,都在2017年宣布將電競作為比賽項目。國際奧委會主席和巴黎奧申委副主席都明確說,正在認真考慮是否將電競納入2024年巴黎奧運會中,最終結果將在2020年東京奧運會閉幕后宣布。
這就產生了一個評價體系上的問題,也即傳統觀念和現實情況的悖論——一方是整體呈批判態度的輿論,甚至不惜用上“精神鴉片”“電子海洛因”等詞匯;另一方卻是網絡游戲走向傳統印象中象征國家榮譽、體育精神的奧運會。
可以預見的是,隨著網絡游戲進一步發展,這種認知與現實的撕裂或許會越發嚴重。因此,主流學界、主流輿論界有必要更客觀地評價網絡游戲、理解《王者榮耀》爭議背后的歷史邏輯。其關鍵在于理解移動互聯網時代下,媒介迭代及隨之而來的受眾迭代帶來的深層次文化挑戰。
手機游戲:媒介迭代浪潮下的寵兒
從國家經濟構成這個宏觀層面上看,網絡游戲目前已成為我國文化產業的一大支柱。2016年,包括手機網游在內的網絡游戲所創造的GDP為1700億元左右,而2017年全年預估可以達到2000億元。
2000億元是什么概念?我國文化產業的整體規模目前已達4萬億元,網絡游戲的產值已占其5%。而占比超過5%即是支柱型行業的門檻標準,因此,網絡游戲事實上已成我國文化產業的支柱。
就文化產業內部結構而言,網絡游戲近幾年的海外影響力、營收能力,都遠遠超過了電影。
中國電影在過去10年里,單年的海外票房從來沒有超過30億元,而且在海外的文化傳播力非常有限。作為對比,2016年中國自主研發的網絡游戲的海外營收為500多億元人民幣。
實際上,以新媒體為代表的數字文化產業在整個文化產業的占比已不低于70%,現在甚至已經到了一款《王者榮耀》的規模就能“碾壓”出版行業的地步。
以上這些數據,無論從宏觀還是微觀層面,都在挑戰那些認為網絡游戲行業“不上檔次、不入流”的舊觀念。
這就是前文提到的媒介迭代:新一代媒介已經以碾壓者的姿態占領傳統媒介市場,這是一個大趨勢下的文化情境。不過,我們學術界、輿論界的主流視野,卻依然還停留在上一代新媒體上,幾乎看不到這些顯而易見的新的深層次的文化挑戰。
新結構:受眾迭代與新文化轉型
不難看出,以移動互聯網尤其是以網游為標志的媒介迭代周期已經開始,而由這場媒介迭代所引發的文化轉型也已拉開序幕。
要理解這場文化轉型,必須知道它是一種結果而非原因。其背后的深層邏輯是受眾的迭代,是主流網民的構成發生了歷史性變化。根據工信部2017年8月份公布的數據,我們可以給目前最廣大的網民做一個初步的“畫像”:
第一,7.5億網民當中有90%是沒有受過本科以上高等教育的;第二,月收入8000元以下的網民占據了7.5億網民中的90%;第三,7.5億網民中,40歲以下的網民占70%;第四,60%的網民沒有正式工作,當然其中包括學生、離退休人員、自由職業者和個體戶等。
此外,還有兩個數據也值得注意。一個是農村網民比重上升,數據顯示農村上網用戶的占比已達25%。再一個是通過網吧上網的網民有1.3億,也就是說,每6個網民當中就有一人依然選擇在網吧上網。
我國網民的主流、主體已經發生重大改變,或者說傳統意義上的網民已被新涌入的網民群體所稀釋。近年來,隨著智能手機和移動互聯網的普及,更龐大的人口被納入網民范疇中來,過去很多“非互聯網人口”,也已成為互聯網的一分子。
在這個新型網民結構的基礎上,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主導互聯網市場取向的,或者說互聯網產品的主要消費群體,并不是極少數的所謂精英,而是近十年來被不斷降低的上網成本所吸引的新網民。
對于今天互聯網上“網紅”頻出、直播火爆、《王者榮耀》《荒野行動》風靡市場等現象,如果僅從所謂的“精英視角”居高臨下地來看,很容易引發不小的爭議。但是,一旦回到剛才的數據,基于我國網民的實際結構來分析,就會發現出現上述現象并非偶然,而是有著深層次的文化動因。正是在移動互聯網時代的新型網民結構下,隨著以往被忽視的海量網民群體的涌入,他們一度被壓抑的需求得到充分的釋放。長期以來,我們的文化產業主要面向一二線城市的市民群體,直到近年來隨著新網民開始不斷走到主流社會的聚光燈下,三四線城市和廣大縣級市被郁積多年的文化娛樂需求才接連爆發。
總之,我們要理解《王者榮耀》的爭議,必須從媒介迭代以及其背后的受眾迭代這個視角去把握。新生事物固然有其值得批評的缺陷,但它的出現和壯大,用長時段的歷史眼光來看,是勢不可擋也不能回避的發展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