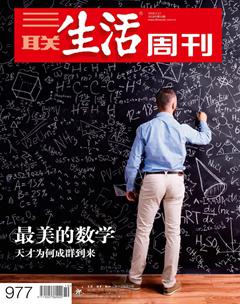數學所作的選擇
蒲實
“00級”數學系畢業的郭化楠在培訓機構“學而思”當數學老師。從小學開始,他的數學成績一直很好,興趣也濃厚,就去人大附中辦的華羅庚學校上課。小學時他是北京市“迎春杯”賽事的前12名,點招進入人大附中,一直參加奧數競賽到高中。中學階段,他周末同時上好幾個數學培訓班,高中數學競賽也一直是北京前10名的水平。高考填報志愿的時候,他自然選擇了數學。
剛進北京大學時,每個人都是優秀的學生。“大一”的時候,大家都還沒有覺得數學很難,考試基本都是90多分。數學系本科頭一年半不分專業,填報志愿時雖然有統計數學、基礎數學和應用數學的選項,實際上進來后平行分成四個班,都上一樣的課程,“大二”下半學期才正式分班。“大一”時,郭化楠與張偉、袁新意在一班。“大二”下半年再進行選擇時,可以選擇的方向有信息、統計、計算和金融,郭化楠選擇了基礎數學班。“00級”在那一年選擇基礎數學的人有五六十人,后面的“01級”在分班時選基礎數學的大約是70人。大概10年后,當“00級”和“01級”出國留學的畢業生回北大任教時,數學學院仍然每年招生150至200人,選擇基礎數學的人卻下降到了30人左右。
對于數學來說,“天賦”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很好識別。郭化楠說,他一直自認為也算是個有數學才能的人,現在也這么認為,看周圍的人能很快看出他們是否有數學思維。但在北大,他見識了天賦高低可以產生的落差,進而認識到,在數學上,天賦是有等級之分的。
本科四年的學習,分化出現在“大二”和“大三”。那時郭化楠的成績從90多分逐漸下滑到80多分,再滑到70多分。成績的逐年下降對數學系的很多人來說是一件自然發生的事情,用郭化楠的話說:“平時學習中的點點滴滴讓人對這種后來看起來有階段性退化的事特別習以為常。”數學系的大多數學生都知道一句話:“復變函數學兩遍,實變函數學十遍,隨機函數隨機過。”這些特別難的課,平時寫作業都不是很懂,只是套用課上的定理,考試前再突擊復習一下,勉強能通過。大學時,老師講一個定理,寫了幾個黑板的板書,用了好幾個小時。“我完全出于對這個定理的尊重而把公式背下來了,但它究竟說的是什么,背后的東西我并不懂。”天賦的級別識別起來并不難:一個定理,大多數人看一個多小時才能理解,有些人十分鐘就理解,而且理解得要深刻得多。做作業也是這樣,“一道題我需要想兩個小時,得出的方法不是捷徑,過程也不是很嚴謹,別人半個小時就用很簡潔的方法證明出來,而且特別嚴謹。一求教,就是一句話解決的事情,問怎么想出來的,‘沒有理由”。
2004年,當時北大深圳研究生院剛剛招生,郭化楠去參加了信息科學系的面試,進入了計算機和互聯網這個領域。嘗試了一段時間計算機,他最終還是回到了數學上,做了數學培訓老師。和數學打交道,他覺得更舒服也更有興趣,雖然沒能成為職業數學家,但還能以數學為業。現在以一個數學培訓教師的視角回過頭看,他恍然領悟,在進入大學之前,奧賽數學實際上一套與職業運動員訓練和選拔相似的體系。他雖然是省隊前10名,但放在全國,大概也就是國家隊100名至200名的水平,“省里面的前幾名與全國頂尖水平相差很大”。中學的時候,一直在奧賽賽道上的郭化楠覺得,自己與北京市第一名之間的差距并不是很大。各省前幾名進入全國冬令營后,排名靠前的人即可保送,“00級”北京有3個人左右通過冬令營保送進了北大。但那一屆北京市的第一名也沒能進國家隊。國家隊的30個人是層層選拔上來的,最終再選出6個人代表國家隊去參加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進入北大,和這些國家隊隊員成為同學,差距感驟然變化,看惲之瑋、袁新意這些人,他認識到“遙不可及”。開始他還嘗試旁聽一下“牛人”課下與老師的交流,但完全不知道他們在說什么,遂逐漸放棄。如今,奧賽冬令營的數量在各省已經“擴招”,如果按照今天這個規模,當年北京市前10名的郭化楠也能進入冬令營。但當年他沒有,他形容自己就像“省隊的人沒進國家隊,就退役當乒乓球教練了”。
從事數學教育多年后,他開始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待數學競賽。他認識到,數學相對有一套成熟的甄別機制來選擇有天賦的人:從課堂數學成績好、有興趣,到進入奧數、做越來越難的題,基本有跡可循。他觀察這些學生的思維方式、解法和過程,同樣都能得出正確答案,但那些懂得把復雜問題轉化成更精巧問題的學生,通常更有數學天賦。他說,把學過的知識組合在一起,就像給孩子散亂的積木;有人會做正統的四方建筑,有人則想不斷突破,勇于創新,把舊的知識做新的組合。數學奧賽的一系列解題訓練,都是在模擬這個環境:由舊的知識創造新的知識。實際上,99%的人都通不過整個過程,而最終選拔出來的人,基本不會有錯。
即使如此,選擇與數學相處的人,日后卻無法選擇以何種形式與數學為伴。很大程度上,那是數學所作的選擇,不由人。郭化楠說,小學參加奧數競賽的人,很多人的職業理想都是長大做數學家,沒有想過別的。中學所學的數學還與現實物質世界有直觀的聯系,到了大學,則完全脫離生活本身,全是高度抽象和推導。小學數學的3個蘋果、15平方米,逐漸抽象為沒有對象和單位的數字,股票指數、彈道導彈這些現實世界的現象抽象為連續曲線可導可積。在這個從高中所學的古典數學,包括本質上是高中數學知識的奧賽,過渡到大學所學的近現代數學的過程中,悄然橫亙著上千年的數學演進,并非每個人都能跨越。對天賦落差的自知,讓人與數學的關系開始游離,不再明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那時候,“00級”的班上,有人想創業,有人想出國,有人想轉做金融。郭化楠開始轉而想做一個一般大學的數學教師,到畢業時,他選了信息科學,嘗試別的職業的可能性。在深圳,他的計算機專業學得很不錯,是優秀畢業生。但最終他還是從雅虎研發中心辭職,“像看到了啟明星的方向一樣”,回到了生命中與之為伴了14年的數學上來。
郭化楠告訴好友,他在考慮換工作時,其實本也曾有過一個審慎的計劃:先用業余時間備課,周末試一下上課,如果行,再從雅虎辭職。但當他打開數學課本時,他“等不及了”,立即辭職。他說,他并不適合計算機,難以在特別實際的訴求中找到意義。“算法優化一些,可以把速度從0.05秒提高到0.04秒,但到用戶那邊,經過3秒的網絡延遲,完全感覺不到。除了發論文,沒有什么效應。”回到數學,走不了學術,給人講課他也很開心,不想放棄數學,他便順應了它對他所作的選擇。他現在免費給本科生講一些線性代數,把高中所學的三維空間向量視為線性代數的簡化版本,這是一種理解線性代數的簡便視角。大學的時候,他理解線性代數用矩陣計算就是一套算法,按規則算就好,并沒有思考過背后是什么。現在他用業余時間重新學,發現線性代數其實是對高維空間的直觀想象。“一個多元線性方程組,系數矩陣的秩表達系數之間的相關性。十元齊次線性方程組,實際就是解決十維空間的問題。如果系數矩陣的秩是7,那系數的相關性是7,形成的解空間就是三維的。整個空間是n維的,減去系數空間的秩(約束),等于解空間的維數(自由度)。”當他理解到這一點時,他翻過一道山,看見了前面更多的山。他恍然明白,當年同窗的那些“牛人”,在那個時候就已比他現在所理解到的深刻,領略過全然不同的風景。
數學仍然從智識上吸引著郭化楠。如果把數學之美視為一個藝術品,經過一定的審美訓練,一個有優秀數學修養的人能夠欣賞它美妙的結構并體驗到愉悅;雖然創造這種美,完全又是另一回事。郭化楠曾讀到過一個觀點,至今印象深刻:如果有外星人,他們的宇宙構成可能和我們不一樣,比如他們可能不靠氧氣呼吸,而靠氮氣呼吸,甚至這些氣體的化學構成可能也不一樣,但他們的數學一定是和我們一樣的。比如他們一定也會有圓形和正方形,這些幾何圖形早已高度抽象,不依賴于任何世界的物質構成,無論你生活在水中還是氣體中。向外星人發信號的時候,人類將使用什么語言?最有可能是質數。只要有文明,發展出這種文明的生物就一定知道計數,只要計數,有智慧的生物就會發現一些數和另一些數不同,從而發現其中一種在地球上被命名為“質數”的數是不可以被其他數整除的。他深信,如果宇宙有一種通用語言的話,那必然是數學。
大學里,當郭化楠與數學的關系變得若即若離時,他的生活空間擴大了。人間煙火的溫暖也許是對虧欠的天賦的補償。在排球場和曲藝社團,他認識了很多社團的朋友,來自各個不同的院系。逐漸的,他與社團的人聯系越來越多,在那里他獲得了許多快樂和友誼。他喜歡聊話劇和曲藝,和朋友在一起,他可以侃侃而談羊肉泡饃的數種吃法和法源寺淵源的不同假說。“非典”的時候,郭化楠沒有回北京的家。有一天,吃完宿舍同學王寧用電熱杯煮的牛肉片和炒雞蛋,他和全宿舍的人都發起了燒。他燒到了37.5攝氏度,被懷疑在“家和學校之間往返”和“疑似接觸疑似病例”,校醫院將他隔離起來。他的社團朋友們輪流打電話陪他聊天,等隔離結束,他和這些人成了可交心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