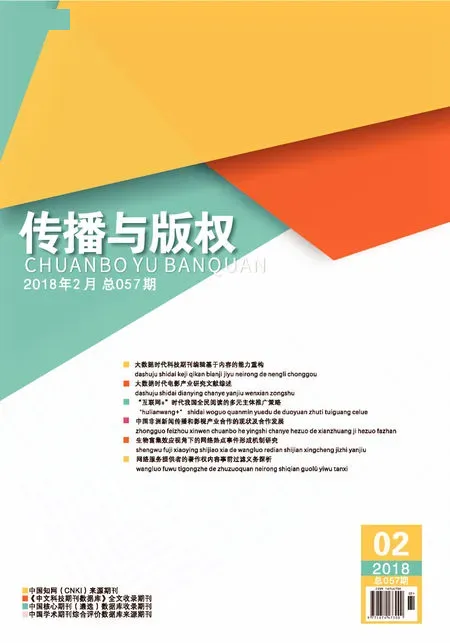大數(shù)據(jù)時代科技期刊編輯基于內(nèi)容的能力重構
周 潔
隨著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云計算等信息技術的快速發(fā)展,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等移動設備的大規(guī)模普及和以微博、微信為代表的社交平臺的迅速崛起,在社會生活生產(chǎn)的各個領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產(chǎn)生、交換和積累海量的多樣化數(shù)據(jù)。國際數(shù)據(jù)公司(IDG)的研究預計,2010—2020年全球數(shù)據(jù)量將增加50倍。自2008年《自然》雜志率先推出了“大數(shù)據(jù)”專刊以來,關于大數(shù)據(jù)對各領域產(chǎn)生的影響的研究迅速成為顯學。[1]通過對海量數(shù)據(jù)的挖掘與分析,可以發(fā)現(xiàn)隱藏在數(shù)據(jù)表象之下的深層次規(guī)律,從而重塑各種商業(yè)模式和服務。包括科技期刊出版在內(nèi)的內(nèi)容傳播行業(yè)同樣正在被大數(shù)據(jù)所帶來的技術變革重塑,從而引發(fā)了對從業(yè)者業(yè)務能力的重構。
一、大數(shù)據(jù)時代科技期刊出版的不適應性
科技期刊作為學術成果的主要發(fā)表陣地,起著傳播科研成果、引領科學研究方向、促進學術交流、評價學術成果價值及學者學術能力的作用。這就要求科技期刊有發(fā)現(xiàn)最新科研熱點、進行精準組稿約稿并及時將科研成果面向公眾進行傳播的能力。然而在大數(shù)據(jù)時代,傳統(tǒng)的科技期刊出版在以上諸方面均表現(xiàn)出了一定程度的不適應性。
(1)內(nèi)容精準度不夠高,無法發(fā)揮引領科研方向的作用。一本優(yōu)秀的科技期刊,應該是該學科領域最新科研進展的“風向標”,讀者據(jù)此可以了解該學科領域的未來研究發(fā)展趨勢。目前在許多科技期刊的出版流程中,稿件多為作者自由投稿,編輯部處于“等米下鍋”的狀態(tài)。作者投來的稿件,其論文主題自然五花八門,選題的依據(jù)完全來自作者的研究方向和興趣,體現(xiàn)的并非是科技期刊編輯部的意志。就算有小部分編輯部策劃的專題約稿,又囿于學科專業(yè)知識匱乏,難以精準地把握學科熱點或找到最合適的作者撰寫文章,導致內(nèi)容精準度不夠高,無法發(fā)揮科技期刊引領科學研究方向的作用。
(2)傳播速度慢,無法滿足快節(jié)奏學術交流的需要。傳統(tǒng)科技期刊出版論文要經(jīng)過多輪審稿修改、編輯校對和排版印刷等環(huán)節(jié),并且受期刊版面限制,每期刊載的論文數(shù)量有限,使得一篇論文從投稿到出版往往需要花費大半年甚至更久的時間。盡管這其中有科技期刊需對內(nèi)容質(zhì)量嚴格把關的因素存在,但曠日持久的出版周期已不能適應大數(shù)據(jù)時代快節(jié)奏溝通交流的需要也是不爭的事實。在等待出版的過程中,作者或許早已在各種社交平臺上發(fā)表了自己對某一領域問題的評論和見解,科技期刊淪落為僅僅記錄科研成果的檔案庫,喪失了引領輿論風向的主動權。[2]
(3)傳播渠道單一,缺乏整合知識內(nèi)容提供服務的主動性。雖然大多數(shù)科技期刊已經(jīng)授權其論文的電子版給數(shù)據(jù)庫服務提供商出版,但現(xiàn)今用戶的互聯(lián)網(wǎng)行為早已移動化,數(shù)據(jù)庫中的論文需要用戶登錄PC端進行檢索才能利用,是一種被動的服務形式,單一的傳播渠道已嚴重制約了讀者對科技期刊論文的閱讀和利用。此外,在大數(shù)據(jù)時代,對科技期刊存量論文進行重新編排,挖掘其中更深層次的聯(lián)系和規(guī)律,從而為用戶提供經(jīng)過整合的知識產(chǎn)品已成為可能。[3]受限于知識能力結構的不足,大多數(shù)科技期刊在整合知識產(chǎn)品方面缺乏主動性。單一的傳播渠道以及提供服務主動性的缺乏,造成的結果就是雜志社盈利模式單一,嚴重依賴數(shù)據(jù)庫服務提供商,喪失產(chǎn)品議價權。
二、科技期刊編輯基于內(nèi)容的業(yè)務能力重構
科技期刊從本質(zhì)上來說屬于內(nèi)容產(chǎn)品,盡管有些科技期刊雜志社也提供學術會展策劃、學術論文寫作指導等服務,也是立足于做好內(nèi)容的基礎上開展的相關性服務。所以,如何基于內(nèi)容重構業(yè)務能力,解決上述科技期刊出版的不適應性,是大數(shù)據(jù)時代對科技期刊編輯提出的新課題和新要求。
(一)重構獲取內(nèi)容的能力
對海量數(shù)據(jù)進行挖掘分析從而發(fā)現(xiàn)事物內(nèi)在規(guī)律是大數(shù)據(jù)最基本的作用。在大數(shù)據(jù)時代,科技期刊編輯應學習數(shù)據(jù)挖掘分析相關的知識,在此基礎上重構自己獲取內(nèi)容的能力,使得期刊內(nèi)容更合理、更精準。
(1)利用大數(shù)據(jù)挖掘選題。科技期刊一般是通過編輯部開選題會來確定選題,依據(jù)的是編輯個人對行業(yè)發(fā)展的了解和學科熱點的判斷,這種確定選題的方式隨意性較強,缺乏科學合理的論證依據(jù)。利用大數(shù)據(jù)確定選題最成功的案例莫過于網(wǎng)飛(Netflix)公司制作的電視劇《紙牌屋》。通過對公司數(shù)據(jù)庫中3000多萬用戶的收視選擇、400萬條評論和300萬次主題搜索進行分析,網(wǎng)飛公司最終確定了拍什么、誰來拍、誰來演和怎么播的問題,使得該劇集一經(jīng)推出便深受觀眾喜愛。[4]對科技期刊來說,其受眾的所有行為,包括論文下載、閱讀和引用等的情況,都隱藏在學術數(shù)據(jù)庫中。科技期刊編輯應該熟練掌握各種學術數(shù)據(jù)庫的使用技巧,長期關注重要的專業(yè)期刊數(shù)據(jù)庫,善于借助其提供的大數(shù)據(jù)分析工具來挖掘選題。利用大數(shù)據(jù)分析挖掘生成的選題,可以獲得科技期刊所在學科專業(yè)的論文下載數(shù)量及引證情況,是論文閱讀者和引用者偏好的精準化測量和預測。例如,《中國實用內(nèi)科雜志》的編輯顏廷梅[5]等,因為發(fā)現(xiàn)其于2013年7月刊發(fā)的《中國急性胰腺炎診治指南》文章在中國知網(wǎng)下載頻次達到6373次,被引頻次為76次,因此判斷急性胰腺炎可能是目前臨床醫(yī)生比較關注的課題。再借助中國知網(wǎng)的學術趨勢搜索功能,發(fā)現(xiàn)2003—2013年關于急性胰腺炎的學術關注度增長迅速,因此策劃了一期“急性胰腺炎的診治”的專題筆談,最終使得雜志紙質(zhì)版較平均每期多賣出3000份,中國知網(wǎng)下載率和被引頻次顯著增加。
(2)利用大數(shù)據(jù)組稿約稿。與傳統(tǒng)確定選題的方式一樣,科技期刊傳統(tǒng)的組稿約稿方式也嚴重依賴編輯個人的經(jīng)驗判斷和人脈積累。要想在眾多學者中找到合適的撰稿人,科技期刊編輯應該對期刊所在學科領域內(nèi)科研人員基本情況及其研究動向非常熟悉。大數(shù)據(jù)技術的出現(xiàn),可以為編輯組稿約稿提供基于數(shù)據(jù)分析結果的參考依據(jù),提高精準性。例如,在萬方數(shù)據(jù)網(wǎng)站首頁(http://www.wanfangdata.com.cn/)的增值服務中,提供了一項名為“萬方學術圈”的服務。如果學者有學術成果被萬方收錄,就可以申請成為認證學者。認證成功后,該學者即可在學術圈中被檢索到。利用萬方數(shù)據(jù)在學術出版領域長期積累的大量數(shù)據(jù),可以提供關于該學者的諸多信息。基于對該學者發(fā)表論文引用頻次高低、核心期刊發(fā)文數(shù)量、發(fā)表論文年度分布、發(fā)文期刊名錄以及主持的重大科研基金項目等信息的分析,可以了解該學者的研究方向、最新科研動態(tài)等,以此作為編輯組稿約稿的依據(jù)。
(二)重構整合內(nèi)容的能力
對于一般科技期刊編輯來說,由于缺乏對行業(yè)深層次的了解,進而導致深度整合內(nèi)容的能力不夠,使得其在數(shù)字化時代不得不將所出版的內(nèi)容交由數(shù)據(jù)庫服務提供商,否則無法有效觸達其讀者。與此同時,科技期刊的受眾也一并拱手轉(zhuǎn)讓給數(shù)據(jù)庫服務提供商,科技期刊只能始終以學術內(nèi)容出版商的角色存在。而在大數(shù)據(jù)時代,內(nèi)容整合能力較強的科技期刊社已經(jīng)完成了向知識服務提供商的角色轉(zhuǎn)變。
學術期刊能夠開展的知識服務,按其延展范圍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是數(shù)字信息服務。將內(nèi)容資源經(jīng)過數(shù)字化和結構化的加工,自建或依托數(shù)字平臺提供簡單的信息文獻服務;第二層是知識產(chǎn)品服務。學術期刊直接針對用戶需求和使用場景,圍繞具體領域與方向定向提供專業(yè)的知識產(chǎn)品與服務;第三層是知識解決方案。[6]拓展由學術期刊衍生的咨詢等其他服務,實現(xiàn)學術期刊出版鏈條的延伸及其與外部產(chǎn)業(yè)的合作。要提供上述三個層次的知識服務,科技期刊編輯可以從如下三個方面著手重構整合內(nèi)容的能力。
(1)整合用戶需求。用戶在科研過程中總是存在諸多的痛點,如課題立項申報、學術論文撰稿指導等。通過大數(shù)據(jù)挖掘技術,深入分析了解本期刊用戶存在的各種不同需求,對相關資源進行開發(fā)、組織,就可以為用戶提供定制化的服務。比如人大《報刊復印資料》旗下的微信公眾號平臺“壹學者”,利用大數(shù)據(jù)分析、關聯(lián)挖掘和推薦、聚類算法等技術,開發(fā)了“課題立項助手”工具,可有效幫助學者迅速確定該學科專業(yè)的研究熱點、研究空白點和發(fā)文趨勢,還可以推薦最佳參考文獻內(nèi)容和合適的合作學者。
(2)打造知識體系。依托海量內(nèi)容資源,傳統(tǒng)知識體系的建設工作一般由大型學術數(shù)據(jù)庫負責實施。但這種以學科分類、關鍵詞標引為基礎的知識體系,揭示的主要是文獻線索,包括主題內(nèi)容、結構與演化、發(fā)展趨勢等,而非知識內(nèi)容。[6]科技期刊編輯應跳出這種思維,基于問題意識主動開展選題策劃,給讀者提供專題化、多視角的學術論文。一個專題就是一個基于相同問題、不同角度的知識體系。在這種基于專題的知識體系中,光是編輯選題的角度就對讀者有啟發(fā)意義,這是數(shù)據(jù)庫無法提供給讀者的。[7]
(3)拓展行業(yè)應用。學術期刊深植于某一行業(yè)領域,圍繞該領域整合各種資源以提供給行業(yè)內(nèi)的從業(yè)者應用可謂獨具優(yōu)勢。可供拓展的應用類型包括行業(yè)資訊、產(chǎn)業(yè)政策、會展策劃、產(chǎn)品測評、實用案例、專業(yè)圖書推薦等。《中國中藥雜志》依托其同名微信公眾號推送科普與大眾健康教育領域的原創(chuàng)內(nèi)容,在利用內(nèi)容積累大量行業(yè)用戶后拓展了衍生品開發(fā)、廣告、培訓等服務,開拓了多種盈利來源。[8]該刊的成功經(jīng)驗值得同行學習借鑒。
(三)重構傳播內(nèi)容的能力
對科技期刊來說,內(nèi)容正逐漸變?yōu)槠湮x者、聚合用戶的手段,因此需要盡可能多地拓寬其傳播渠道,力求吸引更多的讀者和用戶。大數(shù)據(jù)時代學術期刊的傳播媒介呈現(xiàn)多樣化、整合化和傳播范圍全空間化。互聯(lián)網(wǎng)、物聯(lián)網(wǎng)、移動智能終端、各種社交軟件等技術平臺都已成為學術期刊傳播的重要媒介。[9-10]各種平臺因用戶特征、信息傳播機制等的不同,比如豆瓣的用戶偏文藝、知乎用戶偏理性、今日頭條長于智能推薦、微信覆蓋的用戶量最多等,其傳播特性也不盡相同。
以微信平臺為例,微信早已成為最大的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流量入口,石婧等人[11]甚至研究分析認為科技期刊在微信平臺上實現(xiàn)盈利的夢想將不再遙遠。微信是2011年才推出,而公眾號的推出就更晚。對科技期刊編輯來說,如何運營好微信公眾號是一項全新的技能。比如怎么緊跟學術熱點并避免與同類型期刊內(nèi)容同質(zhì)化、圖文內(nèi)容如何編排比較美觀且貼合期刊的整體格調(diào)、推送文章的頻率為多少比較合適、怎么與用戶互動以增強用戶黏性等技巧,都急需在摸索中學習。[12]
其他平臺也有各自不同的傳播策略和規(guī)律所在。科技期刊編輯應該根據(jù)期刊所屬內(nèi)容和行業(yè)的不同,挑選合適的主要傳播平臺,深入分析平臺用戶特征和傳播機制,從而制定針對不同平臺的、適合本期刊的內(nèi)容運營策略,最大限度地傳播本期刊的內(nèi)容產(chǎn)品和服務。
三、結語
大數(shù)據(jù)時代,科技期刊挑戰(zhàn)與機遇并存。一名優(yōu)秀的科技期刊編輯,應該勇敢地擁抱新技術,接受新挑戰(zhàn),基于內(nèi)容不斷重構自己的業(yè)務能力,尤其是獲取內(nèi)容、整合內(nèi)容以及傳播內(nèi)容的能力,才能在新時代的挑戰(zhàn)中抓住機遇,促進科技期刊整體質(zhì)量和盈利能力的雙提升。
【參考文獻】
[1]吳鋒.“大數(shù)據(jù)時代”科技期刊的出版革命及面臨挑戰(zhàn)[J].出版發(fā)行研究,2013(8):66-70.
[2]彭遠紅,孫怡銘.簡論大數(shù)據(jù)時代科技期刊編輯的信息素養(yǎng)[J].科技與出版,2014(3):85-87.
[3]吳赟.產(chǎn)業(yè)重構時代的出版與閱讀——大數(shù)據(jù)背景下出版業(yè)應深度思考的五個關鍵命題[J].出版廣角,2013(23):32-36.
[4]姜中介,黃凱.《紙牌屋》的大數(shù)據(jù)力量:巫術一般的精準營銷[EB/OL].http://tech.163.com/13/0624/01/923M S59U000915BF.html.
[5]顏廷梅,任延剛.網(wǎng)絡大數(shù)據(jù)在優(yōu)化科技期刊選題策劃中的應用與實踐[J].中國科技期刊研究,2016,27(12):1259-1262.
[6]王妍,陳銀洲.基于移動應用的學術期刊知識服務模式與策略[J].中國科技期刊研究,2017,28(10):929-935.
[7]夏登武.大數(shù)據(jù)時代學術期刊的內(nèi)容優(yōu)化與價值重構[J].中國科技期刊研究,2016,27(3):264-268.
[8]呂冬梅,李禾.從傳統(tǒng)紙媒到新媒體的另辟蹊徑——《中國中藥雜志》的“雙轉(zhuǎn)型”戰(zhàn)略[J].中國科技期刊研究,2017,28(1):39-46.
[9]柴英,馬婧.大數(shù)據(jù)時代學術期刊功能的變革[J].編輯之友,2014(6):28-31.
[10]邵玉嫻.大數(shù)據(jù)時代學術期刊的變革及編輯工作的轉(zhuǎn)型[J].編輯學報,2014,26(S1):152-155.
[11]石婧,段春波,周白瑜,等.科技期刊應用微博微信平臺影響力評價初探[J].中國科技期刊研究,2014,25(5):655-660.
[12]吳彬,丁敏嬌,賈建敏,等.利用微信平臺打造科技期刊編輯新方式[J].中國科技期刊研究,2014,25(5):661-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