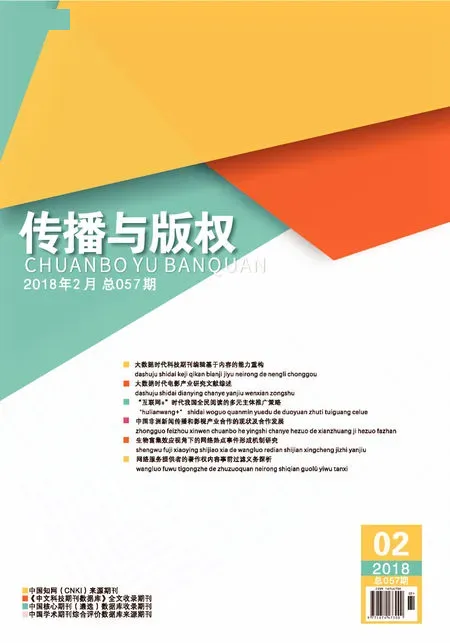“互聯網+”時代我國全民閱讀的多元主體推廣策略
陶賢都 賀子坤
[本文系長沙市科技局軟科學計劃項目“創新長沙傳播戰略研究”(項目編號:K1501021-41)階段成果]
開展全民閱讀活動是我國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重要舉措。自2006年推出全民閱讀活動以來,中國社會逐步形成了推動全民閱讀,共建書香社會的良好氛圍。同時,互聯網在中國飛速發展,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深刻影響。“互聯網+”的本質內涵就是以互聯網為標志的信息通訊技術可以無所不在,不僅可以改造產業和行業,而且可以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和社會管理模式。“互聯網+”行動的實施,為實現數字閱讀與傳統閱讀的融合提供了新的契機,為推動我國全民閱讀提供了廣闊的平臺。
一、“互聯網+”時代我國全民閱讀的新特點
“互聯網+”時代,全民閱讀呈現出了新的變化和趨勢。根據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發布的第十四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報告,抽取近三年(2014年、2015年、2016年)的閱讀調查數據,從公眾閱讀率、數字閱讀接觸率、數字化閱讀接觸者年齡分布和微信閱讀量等四方面進行分析,發現“互聯網+”時代全民閱讀呈現四方面的新變化。
(一)公眾閱讀率逐步提升
2014年,我國公眾的綜合閱讀率為78.6%,圖書閱讀率為58%,報紙閱讀率為55.1%,期刊閱讀率為40.3%,數字閱讀率58.1%。2015年,我國公眾的綜合閱讀率為79.6%,圖書閱讀率為58.4%,報紙閱讀率為45.7%,期刊閱讀率為34.6%,數字閱讀率64%。2016年,我國公眾的綜合閱讀率為79.9%,圖書閱讀率為58.8%,報紙閱讀率為39.7%,期刊閱讀率為26.3%,數字閱讀率68.2%。從數據可以看出,近三年來國民閱讀率整體呈全面上升態勢,近三年來綜合閱讀率高達79%左右,主要包括綜合閱讀率、圖書閱讀率、數字閱讀率在內的數據均全面上揚,在某種程度上說明近三年我國開展全民閱讀活動成效顯著,民眾閱讀意識有了很大提高。
(二)數字閱讀接觸率提高
中國國民數字化閱讀方式接觸率近年來不斷上升。2008年,24.5%;2009年,24.6%;2010年,32.8%;2011年,38.6%;2012年,40.3%;2013年,50.1%;2014年,58.1%;2015年,64%;2016年,68.2%。數字媒體“打破了知識、信息與其物質性載體之間的原有聯系,重新塑造了大眾的私人交往、信息獲取方式乃至公共事務和日常生活形態”[1],從中國國民數字化閱讀方式接觸率顯示,2016年我國國民數字化閱讀方式接觸率達到68.2%,相較于2014年的58.1%和2015年的64%分別上升了10.1個百分點和4.2個百分點,呈平穩增長的態勢,而對比2008年的24.5%則上升了43.7%,增長幅度大,說明在“互聯網+”時代,越來越多的國民開始選擇數字化閱讀方式,數字化閱讀正在改變著我國國民閱讀習慣,數字化閱讀已逐漸發展成為我國全民閱讀的重要方式。
(三)數字化閱讀群體年輕化
針對數字化閱讀接觸者年齡分布情況,主要以2015—2016年全國國民閱讀調查結果進行分析,可以發現,2015年我國成年數字化閱讀方式接觸者中,18~29周歲的占38%以上,30~39周歲占28%以上。2016年我國成年數字化閱讀方式接觸者中,18~29周歲的占36%以上,30~39周歲的占27%以上。2015~2016年成年數字化閱讀接觸者中,18~39周歲人群占63%,說明目前我國國民閱讀中,年輕讀者群體對數字化閱讀有著更高的認知度和接受度,數字化閱讀群體呈年輕化特點。
(四)微信閱讀量增長顯著
微信閱讀作為全民閱讀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互聯網+”時代全民數字閱讀的重要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我國國民的閱讀狀況。第十四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數據顯示,2016年我國成年國民閱讀中微信閱讀增長顯著,有62.4%的成年國民在進行微信閱讀。2016年我國成年手機閱讀接觸群體的微信閱讀使用時長在20—30分鐘之內的人數占所調查總人數的27.4%,使用時長在0.5—1小時內人數占24.2%。2016年我國成年國民人均每天微信閱讀時長為26分鐘,這充分說明微信閱讀已逐漸成為“互聯網+”時代國民閱讀的重要方式。“2016年中國境內活躍的手機上網碼號數量達12.47億,2016年境內擁有用戶量排名第一的APP是微信”,[2]微信龐大的用戶量進一步說明微信閱讀在全民閱讀中發揮的作用日益明顯。
二、“互聯網+”時代我國全民閱讀推廣存在的問題
“互聯網+”時代我國全民閱讀發展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出現了良好發展的勢頭,但是,在“互聯網+”時代,全民閱讀的推廣依然存在一些尚待解決的問題。
(一)全民閱讀層次在“互聯網+”時代呈現“淺閱讀”的態勢
互聯網時代廣泛的數字化閱讀,鼓勵了輕率、浮躁閱讀態度的蔓延,以往那種以深度閱讀為主的“虔誠”與“敬畏”心態,逐漸衍變成一種以淺閱讀、掃讀為主的“隨意”與“瀏覽”心態。美國學者詹姆斯·默蓋爾提出的閱讀層次論把閱讀分為知識性閱讀、理解性閱讀、探索性閱讀三個層次。閱讀中觸及的層面不同,代表著閱讀的不同深度。“淺閱讀”是在數字化時代產生的一種閱讀方式,“淺閱讀”是“簡單、快速甚至跳躍式的閱讀方法,對閱讀內容則淺嘗輒止、囫圇吞棗、一目十行、不求甚解,它追求的是實用的資訊或短暫的視覺快感”。[3]當今社會中閱讀在閱讀層次上片面追求“淺閱讀”,主要由客觀環境和主觀環境所造成的。從客觀方面而言,傳播技術的迅速發展帶來了多媒體的閱讀環境,這種環境造成信息的超載狀態;傳播媒介的特性導致了傳播內容的碎片化,比如手機媒體的屏幕大小、微博發表文字時140字的字數限制,等等;市場運作方式使得眾多數字出版商為占有市場、賺取盈利而一味迎合大眾“碎片化”的閱讀口味;快節奏的生活方式使得公眾很難靜下心進行長時間閱讀。從主觀方面來說,公眾個人功利性、隨意性的閱讀傾向;另外,現代人際交往內容大多是每天新鮮的社會新聞,人際交往的需求影響著公眾的閱讀傾向。“淺閱讀”使人形成一種惰性化的依賴,習慣于通過搜索、提問或者交互來獲得知識碎片,容易使公眾形成“淺思維”、閱讀惰性,對社會則容易產生“知識分子”流失,書香社會建設的效能降低。
(二)全民閱讀推廣主體較為單一
政府作為全民閱讀與書香社會建設的頂層設計者,在整個推廣過程中起著主導作用,政府從宏觀層面對全民閱讀從立法、政策、環境等方面對全民閱讀進行引導。但是在全民閱讀的實際推廣中,出現了推廣主體單一的現象,全民閱讀的推廣多由政府推動,導致民眾參與度不高,社會反響低,進而影響了全民閱讀的推廣效果。例如,政府在每年的4月23日進行世界讀書日的宣傳活動,活動通常以征文活動、圖書展覽等形式為主。雖然活動當天能取得良好效果,但是這些活動往往在讀書日和讀書周以后就銷聲匿跡。此外還有一些全民閱讀活動不免帶有形式主義色彩,導致全民閱讀的推廣變成面子工程。
(三)全民閱讀立法起步晚導致民眾認知度較低
自2012年黨的十八大提出“全民閱讀”后,一直缺少具有全國法律效應的法律來保障全民閱讀相關主體的權利。2013年中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宣布將全民閱讀立法列入2013年國家立法工作計劃。地方性的閱讀法規從2015年1月正式實施,即《江蘇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促進全民閱讀的決定》。這些地方性法規在處理地方性的全民閱讀問題具有可行的法律效力,但是仍不能作為全國性的全民閱讀問題的法律來源。雖然我國關于全民閱讀的立法工作已經展開并取得初步效果,但是結合我國實際情況不難發現,在促進全民閱讀的立法實施實踐中仍存在不少的問題,公眾對于全民閱讀相關立法的認知度較低,全民閱讀立法普及度較低。
三、構建多元主體的全民閱讀推廣機制
“互聯網+”時代的到來,意味著互聯網不僅是作為一種技術出現,在事實上已經引起了閱讀方式的變化。因此,在“互聯網+”時代,必須要用互聯網思維,審視互聯網對全民閱讀的影響,采取相應的全民閱讀推廣策略。針對目前全民閱讀推廣中存在的問題,特別是推廣主體單一的問題,政府、校園、家庭、城市社區和農村、推廣機構多元主體應互相配合,共同推廣全民閱讀活動,掀起全民閱讀的高潮,以使“互聯網+”環境下,全民閱讀的效果進一步提升。
(一)政府:活動倡導與資源調度
在“互聯網+”的大背景下,政府推進“全民閱讀事業”已經不再受到地理空間、工作時間等客觀限制,政府應成為保障全民閱讀推廣活動高效進行的服務型政府。在全民閱讀的推廣進程中,政府職能的重中之重即有效調動社會各方資源參與到閱讀推廣,充分整合行政力量、社會力量,在推進“全民閱讀事業”中形成合力,保證閱讀資源和閱讀設施,從而最大限度地使全民閱讀活動產生成效。具體而言,政府應加大財政資金,完善公共基礎設施。政府應利用互聯網技術優化公共文化服務,創新數字閱讀模式。政府還應該提供財政支持,為移動圖書館和云圖書館提供豐富圖書文獻資源,涵蓋電子圖書、報紙文章、中文外文文獻數據,可供公眾自由選擇。
(二)家庭:創新閱讀形式
家庭閱讀是全民閱讀多元主體的首要選擇,因此加強家庭閱讀建設具有重要意義。“互聯網+”時代為閱讀提供了豐富的形式,家庭閱讀可以采用多樣的方式,在閱讀形式上進行創新,從而提高閱讀的效果。在“互聯網+”時代,家長應主動利用微信公眾號和客戶端,根據相應的閱讀服務,與孩子共同閱讀,選擇公眾號和客戶端的有聲書、視頻和直播等形式,帶領孩子聽故事、看科普視頻和科普實驗直播。家長帶領孩子從紙質閱讀中走出來,選擇分類豐富的有聲閱讀內容和少兒作家的作品,立體形象地為孩子講故事,普及知識,這有利于提高孩子參與閱讀的興趣,既營造了互動的閱讀環境,又促進了全民閱讀走進更多家庭。例如,“口袋故事”APP涵蓋了豐富的閱讀內容,并將內容詳細分為國學、歷史、音樂、英文等多種欄目,將內容按照年齡段進一步細分,同時還設置家長課堂,指導家長正確帶領孩子讀書,切合了家長和不同年齡段孩子的需求。家長可以借助網絡學習平臺和孩子一起制定閱讀計劃,引領孩子適當利用移動終端進行線上的閱讀活動,同時,在現實生活中鼓勵孩子記錄閱讀心得,網絡學習與生活學習相結合。
(三)城市社區和農村:營造數字閱讀環境
城市社區和農村同樣都是全民閱讀推廣的重要社會區域,應利用“互聯網+”時代的新技術營造全新的數字閱讀環境,建立社區和農村數字閱讀書屋,融合傳統閱讀方式,從而加快全民閱讀的步伐。城市社區和農村建立數字閱讀書屋,首先應加大對硬件設施的投入,如電腦、智能手機、智能電視、電子圖書借閱器、平板電腦、電子閱讀器等,開通無線網絡;擴大傳統書屋規模,在紙質閱覽室的基礎上增設電子閱覽室,通過網頁、視頻、音樂、電子地圖等豐富居民和村民的閱讀形式;為圖書設置二維碼,只需掃描二維碼就可以在手機終端閱讀;同時,在推進數字閱讀書屋建設過程中應收集優質且符合民眾閱讀習慣的數字閱讀內容,保障全民閱讀推廣的質量。
社區和農村數字閱讀書屋在完善硬件設施的基礎之上應加大對軟件的開發力度,“互聯網+”時代電子通信技術的發展促進智能手機、智能電視等終端在社區和農村的普及度越來越高,數字書屋建設應從閱讀終端軟件入手,使居民和村民隨時隨地進行閱讀。為此,社區和農村閱讀推廣相關負責人應主動建立本社區和農村的微信閱讀公眾平臺,在專業人員的指導下發布優秀的閱讀內容,為居民生活農民務農提供便捷的信息服務。與此同時,社區和農村負責人要吸引專業人士與軟件開發公司合作開發社區農村閱讀APP,特別是農家閱讀APP,為農民提供豐富的農業資源,惠農助農。
(四)校園:建立云圖書館平臺
“互聯網+”時代,學校閱讀是全民閱讀的基礎部分,而校園作為全民閱讀推廣的主體之一,應結合“互聯網+”的技術特點,借鑒互聯網思維,運用云計算和大數據技術構建校園云圖書館平臺,為學生提供海量的圖書資源和個性的學習服務。云圖書館是“指將先進的云計算技術運用在圖書館的管理和服務中,這是一種新的圖書館運營模式”[4]。“互聯網+”時代的云圖書館通過云計算技術整合紙質圖書和電子圖書,用戶通過終端搜索書籍,付費或免費的方式獲得書籍資源,整個過程簡化了傳統圖書館的借閱服務,提高了圖書館的運作效率。
學校應主動借助平臺建設方的云計算技術優勢,廣泛搜集圖書資源,建立圖書數據庫,聯合其他學校圖書館和公共圖書館的合作,建立校園云圖書館,擴充電子圖書資源,完善基礎借閱設施。校園云圖書館涵蓋了傳統圖書館和電子圖書館的圖書資源,豐富了校園閱讀的內容。同時,這種校園云圖書館依托方便快捷的信息技術,讓偏遠地區的學生也可以瀏覽海量的圖書,拓寬了全民閱讀的范圍,促進全民閱讀推廣效率的提高。同時,校園云圖書館建設還可以與閱讀APP合作,在閱讀時依據學生的閱讀喜好無縫接入APP閱讀推廣內容,擴充校園閱讀內容。
(五)閱讀推廣機構:線上線下智能推廣
相對于家庭、社區農村和學校,閱讀推廣機構是面向全社會成員進行閱讀引導,閱讀推廣的機構,這些專業機構通過多種渠道、形式和載體向公眾傳播閱讀理念、開展閱讀指導、提升市民閱讀興趣和閱讀能力。“互聯網+”時代我國全民閱讀推廣機構既包括專業的推廣組織,如湖南的天心閱讀文化網,也包括全國各地的圖書館、書店、出版社、發行商等等,這些機構通力合作,有利于集聚推廣力量,提高全民閱讀推廣工作效率。
閱讀推廣機構應充分利用互聯網技術,堅持“線上到線下”的推廣理念,同時開展線上與線下活動,擴大推廣工作輻射范圍。線上方面,閱讀推廣機構應采取“三微一端”相互助力的策略。例如,閱讀推廣機構可以開設閱讀微信公眾號和官方微博,在用戶精準定位基礎上介紹全民閱讀推廣活動,實時跟進活動進程,以文字、圖片、視頻和VR等方式多方位呈現活動場景;建立微課堂,以視頻形式邀請專家解讀經典,帶領民眾回味經典;開設官方微博問答,為民眾解答閱讀困惑,推薦好書,舉辦微博抽獎活動,轉發微博領取圖書獎品;建立微信微博讀書群,民眾在微信微博群中交流讀書心得,分享好書。建設線下閱讀互動平臺、提供便捷優質的讀者服務也是閱讀推廣機構提高效果的重要手段。閱讀推廣機構建設線下互動平臺,讓閱讀與社交充分融合。充分利用“互聯網+”時代新興技術,如VR技術制作“真人圖書”,增強互動式閱讀體驗;創辦“共享書店”閱讀平臺,倡導紙質閱讀資源和數字閱讀資源無障礙閱讀;在舉辦讀書會、書展、沙龍等線下活動活躍閱讀氛圍同時,以音視頻為媒介,推動個人閱讀向交互閱讀轉變,組織民眾分享好書,交流閱讀心得。
四、結語
“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對于推動我國全民閱讀活動的開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互聯網+”有利于更好地實現閱讀機會的均等,縮小知識貧富的差距。“互聯網+”為全民閱讀賦予更豐富的內容呈現方式,有利于閱讀方式的創新。“互聯網+”時代的數字化閱讀和信息技術從推廣時間、推廣速度和推廣范圍三個方面提高了全民閱讀的推廣效率,加速了知識普及的過程。當“互聯網+”和全民閱讀兩者結合,多元推廣主體運用互聯網思維在全民閱讀推廣中的合作、協調,更加有利于“全民閱讀”氛圍的形成,加快“書香社會”的建立。
【參考文獻】
[1]陳偉軍.媒介融合語境中的閱讀文化轉型[J].國際新聞界,2012(4):90-94.
[2]中國互聯網協會.中國移動互聯網發展狀況及安全報告(2017)在京發布[EB/OL].http://www.isc.org.cn/zxzx/ywsd/listinfo-35400.html,2017-05-17.
[3]彭敏.淺閱讀時代的深層思考[N].人民日報,2010-08-10(23).
[4]黃燕.云圖書館服務理念及其模式研究[J].江蘇科技信息,2016(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