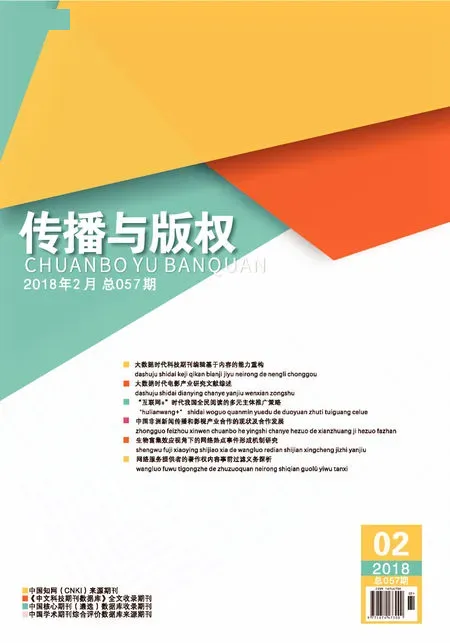網絡暴力行為的認定與防范
劉德祥 黃 婷
(本項目受到南京審計大學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項目資助)
隨著傳播技術的高速發展,“第四媒體”互聯網也日趨成熟,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的有關數據顯示,截止到2016年6月,我國的互聯網普及率為51.7%,而互聯網使用人數已達到7.1億人,世界之最。但身處網絡時代的今天,互聯網作為一個公開交流的信息平臺,方便了公眾自由發表言論的同時,也衍生了網絡暴力這一非常態現象。
近年來,由于互聯網的廣泛應用,網絡暴力事件層出不窮,并以其傳播速度快、作用范圍廣、影響性質惡劣等特點對越來越多的人造成不必要的身心傷害。從早期的8.27兒童網絡暴力事件,到四川直播自殺事件;從被叫囂滾出娛樂圈的袁姍姍,到被污蔑死因的喬任梁,再到默默無名的普通人,網絡暴力真實地在我們面前上演,防范網絡暴力已刻不容緩。
網絡暴力依托于互聯網形成,一方面,實施者通過侮辱性話語和圖片、侵犯個人隱私權甚至現實中的騷擾對事件當事人造成巨大的精神傷害;另一方面,大批不明所以的網民人云亦云,從而產生具有某一導向性的社會輿論,破壞了網絡應有的秩序,并極有可能影響司法公正。
雖然我國已經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但網絡暴力相關的法律法規仍有很大的一部分空白急需完善。而且該法律所針對的對象以網絡服務提供者、網絡監管者及相關監管部門為主,對于普通公眾的保護除了《侵權責任法》有所涉及外,并無具體的條文對網絡暴力行為進行規制。我們必須深刻認識到該研究項目的急迫性與必要性。
一、網絡暴力現象形成的原因
網絡暴力的形成原因有很多種,目前學界將其形成原因主要歸為以下幾類:
(一)網絡環境的特殊性
姜方炳[1]認為網絡技術的風險特性是催生網絡暴力的潛在根源。一方面,借助虛擬技術構造而成的網絡空間為“網絡暴力”的產生提供了主體多元、責任分散的一個輿論場所。另一方面,互聯網本身具有的繁雜難辨的海量信息則強化了網絡受眾的風險感知度。
(二)傳統道德觀念的缺乏
常昕[2]指出,網絡暴力事件往往能夠引起人們注意,源于其事件對社會一般傳統道德觀念的違背。當部分網民對網絡上不道德的事件發表意見、進行道德審判時,容易引起其他網民的共鳴。人們基于道德正義感參與道德審判,卻不料想給當事人造成了法律上的傷害。
(三)意見表達渠道的不足
常昕[2]指出,社會競爭的加劇、社會壓力的增大,給人們帶來了很多負面情緒,如焦慮、緊張、憤怒和失望等,這些情緒在現實生活中,缺少有效的表達。然而通過在網絡上道德的審判,網民尤其是現實生活中的弱勢群體,找到了發泄的渠道,從而也釀成了網絡暴力。
二、現行法律對網絡暴力的認定與應對
本研究小組主要針對上述形成原因中的第五點進行研究,同時憲法、刑法以及民法是本小組研究的法律基礎。經過本小組的研究,對三大法在網絡暴力行為的規制方面有以下幾點見解。
(一)言論自由的合憲性規制
憲法是根本大法,我們也先從憲法入手研究。首先,網絡暴力的現象涉及的憲法問題應該屬于言論自由的范疇。之所以這樣認為的首要原因應從網絡暴力的最直接產生根源出發。網絡暴力的發生一開始只是某些人或集體在網絡這個開放的環境發表了一些不恰當的言論,然后經過一系列的發酵最終演變成為網絡暴力。先不討論所發表的言論是否恰當,這個在網絡上發表言論就是所有公民都享有的言論自由的表現,所以說,我們認為從憲法方面主要涉及言論自由方面的問題。
其次,我們所研究的網絡暴力認定問題,實際上就是言論自由的一個邊界問題,也就是強調這個自由應該在一個什么樣的程度內可以享有。我們也知道自由不可能是毫無限制的,自由一旦濫用的話,就會形成暴力,就會侵犯他人的權利,這也是對網絡暴力現象形成的最直接的解釋。所以,從憲法的角度來講,權利的自由是有限制的,就是在不能侵犯他人合法權益的前提條件下方可行使,根據《憲法》第五十一條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合法的自由和權利。”所以說,解決網絡暴力這個問題歸根結底還是要針對公民的言論自由進行有效的規制。
當然,常見情況下,一般的法學學者都會傾向于擴大人民的自由,尤其是擴大人民的言論自由,保障人民的新聞自由。從幾十年的改革開放歷程來看,中國人民的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包括新聞自由)都是逐步放開的,而且程度是越來越大。比如說言論自由最基本的權能——每個人可以自由開設媒體的這個權利,在以前的話是沒有的。對于這個自由的規制,網絡實名制就是最好的應對措施。網絡實名制所強調的就是網絡用戶在使用網絡的時候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尤其是在網絡上發表的言論。當該網絡用戶在網絡上發表了不恰當的言論并造成網絡暴力的后果時,就可以通過網絡實名對該用戶追究責任,也就是說網絡實名制可以有效地對網絡用戶所行使的自由進行合理的規制。
再者,對網絡暴力的規制還要與公民正常行使自己言論自由的行為區別開來。我們可以借助美國一些言論控制的標準:即刻且危險。實際上,對網絡暴力的控制首先要建立在網絡上發表的言論是否真實的標準之上。如果在網絡上發表的言論是假的或者說是違犯法律條文的,然后再利用一些煽情或者其他引誘或誤導他人的方式,誘使他人擴散該言論,就顯然不屬于言論自由的邊界。僅當你首先保證你發表的言論是真實的,這才屬于依法保護的范疇。
最后,憲法對于有關言論自由的條款是否要修改這個是沒有必要去討論的,因為我們已經有相應的條款,只要通過合憲性的理解或者對憲法的解釋,就可以把言論自由這個概念的內涵進行擴大,這就等同于現在的表達自由、新聞自由等內容,就已經可以對現有的網絡暴力現象進行規制。
(二)網絡暴力行為的定罪量刑
從刑法的角度來講,對于網絡暴力行為的認定就相對來說有點困難了。首先,網絡暴力的產生是在網絡這種特殊的環境之中,基本上不會說侵害人與被侵害人有直接的身體接觸而造成傷害,而且網絡暴力現象的產生是發生在不特定的群體里的(即是公眾),這就在責任認定上有很大的困難。但同時網絡暴力的現象一旦發生,卻又會產生廣泛且嚴重的社會影響甚至是社會危害,這樣又可以說符合《刑法》第一十三條中對犯罪的規定。因此,研究網絡暴力行為的時候,我們首先需要明確的是這個網絡暴力到底是一種什么性質——是一種人身上的侵害還是一種精神上的侵害。如果說這是一種人身侵害,那么在刑法里面就稱之為暴力;如果僅僅是精神上的侵害,那么在刑法里面則稱之為強迫或者說是脅迫。在刑法里面,以人身的侵害(也就是暴力)或者說是精神上的侵害(也就是脅迫)為行為的犯罪有很多,比如說搶劫罪、強奸罪、故意傷害罪、敲詐勒索罪等等,這些本身就已經包含了暴力或者脅迫的行為方式在里面。
由于刑法所調整的不是平等主體之間的法律關系,所以如果說要研究刑法如何去應對網絡暴力行為的話,那么研究的就應該是刑法對于網絡暴力犯罪事實的定罪量刑的標準。針對網絡暴力定罪量刑的制定,我們認為沒必要定那么高。因為在網絡環境當中,所謂的暴力是不能接觸到他人的人身的,所以基本上不會對他人的人身造成傷害或者說是重傷甚至死亡的后果,也就是說不見得非得把它的程度規定為輕傷以上。我們現行刑法對暴力性犯罪的定罪量刑程度為輕傷以上,然而并不適用于網絡暴力的特殊性。但是程度也不能無限地低,畢竟達到犯罪的程度都是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必須與普通民事侵權行為或者行政違法行為相區分,要達到一定的嚴重程度。
網絡暴力更傾向于一種由不特定或者多數人也就是公眾參與的暴力,而不是僅僅對于特定的某一個體或者某一個群體參與實施的暴力行為。畢竟網絡是一種開放的空間,誰都可以利用其進行各種活動。所以說可以將網絡暴力的程度以規模為標準,以侵害人是否達到一定特定數量為標準,比如說把侵害人達到一千人以上或者三千人以上這樣的標準來定性該案件是否達到嚴重或以上的程度。
(三)侵權責任的認定與追究
民法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民事關系的法律,是我們合法權利受到侵害時可以拿起來維權的最直接的法律武器,所以對民法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目前來看,在現行法律體系下,從民法方面我們可以借助一般的侵權責任法來解決想要研究的問題。根據《侵權責任法》第三十六條的規定:“網絡用戶、網絡服務提供者利用網絡侵害他人民事權益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
至于這個侵權責任的承擔方式,同樣還是可以參照現行一般侵權責任法對于網絡服務提供者的侵權責任的規定。因為網絡環境比較特殊,如果要用過錯和無過錯的方式來舉證責任的話,那就有可能會有點難以分配。所以,如果是無過錯的話,那肯定是過多苛責了這個參與網絡的各個方面。主體認定方面,還涉及一個比較特殊的方面,就是網絡的監管者和網絡服務的提供者,也就是在認定侵權時應該參照現行的一般侵權責任法中網絡服務的相關規定,即對網絡服務監管者和提供者與侵害人之間的關系進行考慮。比如說網絡服務提供者在知道網絡侵害現象的存在后,應當刪除的沒有刪除,應當制止的沒有及時制止。然后針對這些情況,可以進行一個連帶責任承擔的認定。當然這個網絡服務提供者有沒有參與到侵害行為之中,這就是網絡服務提供者應承擔責任的程度認定,我們就不討論了。
最后還有一點,根據《侵權責任法》第三十六條的規定,我們應當要明確自己的權利,一旦發現出現網絡侵害行為,我們有權通知網絡服務提供者,并要求該網絡服務提供者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網絡侵害行為的進一步惡化,從而在網絡暴力還在發酵之時將其解決。
三、對進一步完善對網絡暴力行為的規制的建議
從法律層面對網絡暴力行為進行進一步的規制是具有迫切性、必要性的,但是在現行的法律體系下直接就網絡暴力現象進行法律上的修訂也是不合適的,因此如果要對網絡暴力行為從法律層面進行進一步的規制,據本小組的研究,有以下幾點建議。
第一,網絡暴力是一個法學概念,或者社會學概念,如果要立法,應該要做相應的轉變,在法律概念中找到對應的名稱,并歸納到立法用語中,但本質是對網絡暴力行為進行處理。比如,尋釁滋事就包含傳播謠言、網絡恐嚇,侵犯隱私權就包含傳播謠言、違法偷拍等行為。法律用語要規范,也要保持穩定性。
第二,從目前來看,我們現在針對言論自由方面的立法主要是現行的法條法規。而這些發條法規的位階比較低,主要還是一些部門規章以及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比如說出版管理條例之類的,如果可以的話,未來還應該制定一些類似出版法、新聞法等法律法規來完善現行對言論自由這一方面管理的法律法規。
第三,為了衡量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網絡暴力行為處罰,刑法對于網絡暴力是否應單獨列示的研究時,應該關注其是否屬于一種新型的、不能為刑法現有的以暴力、脅迫為行為的犯罪所包含的行為犯罪,還是屬于可以涵蓋在刑法現行的以暴力、脅迫為行為的犯罪里面的犯罪,這是必須明確的一點。如果能夠涵蓋在刑法現有的以暴力、脅迫為行為的犯罪,就沒有必要單獨列示出來;如果這種網絡暴力行為是一種新型的行為方式、現有刑法所不能涵蓋在里面的犯罪行為,那么就有必要把這種網絡暴力的犯罪行為單獨列示在刑法里。
第四,對網絡暴力行為立法的前提條件是,我們國家完善相應的人格權部分,因為只有當人格權完善之后,網絡暴力行為所侵犯的法益和所指向的利益才有一個明確的客體。在人格權法里面,應當強調身份權和人格權,因為網絡暴力在很多時候侵犯的就是個人的一種人身權而并非財產權。所以在我國現行的民事法律體系里對人格權這一部分略顯單薄,也就是說網絡暴力行為如果現在要直接立法的話是肯定不太合適的。但是到了現在,頒布施行的《民法總則》后續的單行人格權法、物權編、債權編等基本的法律平臺構建已經比較完善,即對于網絡暴力行為肯定是較之前有所規制的。
【參考文獻】
[1]姜方炳.“網絡暴力”:概念、根源及其應對——基于風險社會的分析視角[J].浙江學刊,2011(6):181-187.
[2]常昕.關于網絡暴力的案例分析[D].蘭州:蘭州大學,2013.
[3]梁麗莉.法律規制視角下的網絡暴力現象研究[D].重慶:重慶大學,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