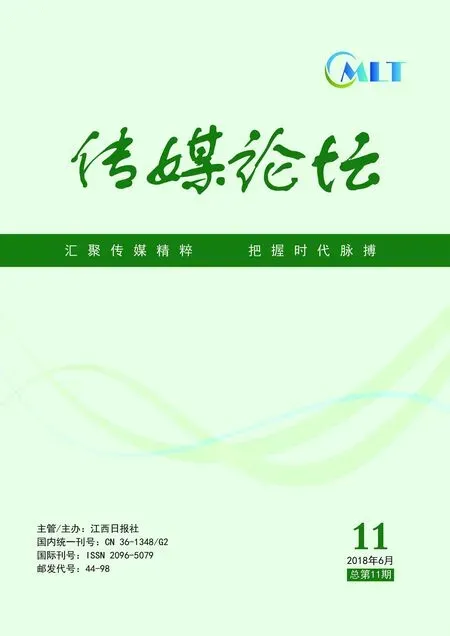論新聞評論的理性和倫理
——以新京報三篇文章評“異煙肼毒狗”為例
王婧瑤
(貴州民族大學傳媒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
近日,一篇來自某公眾號名為《遛狗要栓繩,異煙肼倒逼中國養狗文明進步》的文章在各社交媒體平臺上呈刷屏態勢,轉發閱讀數量超過十萬余次,文章表面對現如今各類不文明養犬行為痛心疾首,提倡應該用一種名為“異煙肼”的藥物來毒殺犬類并聲稱此藥物對人無害,實則立足于當下社會的“人狗矛盾”,煽動公眾輿論的負面情緒。隨后新京報評論官方公眾號針對“異煙肼毒狗”連發三篇評論,分別為《整治不文明養狗,城市應堅定立場》《異煙肼毒狗,以暴制暴情緒反映公力救濟不足》《應該拿中國版“惡犬法案”制惡犬傷人》,本文將以此三篇評論文章為例,淺析新聞評論中的理性和倫理。
一、“異煙肼毒狗”事件背景分析
“異煙肼毒狗”的導火索是源于被“造假狂犬疫苗”激化了中國社會人與狗的矛盾。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人們養狗的初衷已經不再局限于看家護院,而是把狗作為寵物、作為家庭成員來看待,城市中寵物狗的數量越來越多,隨之出現的是種種不文明的養寵現象,如遛狗不拴繩造成狗撲人或傷人、放任狗隨意大小便、狗叫聲擾民等,流浪狗在城市街頭游蕩并充滿攻擊性使人們對于狂犬病的傳播更為忌憚,由于狂犬病發作后致死率為100%,造假狂犬疫苗事件的發酵無疑成為了壓垮公眾心理防線的最后一根稻草,種種群體負面情緒在傳播過程中變得更為極化,仿佛屠狗之舉刻不容緩。
此外,其中除了人與狗之間的矛盾,還有更為復雜的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一直以來,“愛狗人士”同“憎狗人士”紛爭不斷。前者批判后者沒有愛心同理心,怯懦自私甚至容不下一只動物生存;后者則批判前者常常以愛心的名義做出各種違法行為,使“愛狗人士”的內涵朝著貶義和諷刺方向發展。兩派人士在社交平臺上爭論不休,然而情緒宣泄遠遠多于理性分辨,對實際問題的解決并無益處。且在提倡異煙肼毒狗的文章風靡朋友圈過后,社會上已然出現了大量寵物狗食用有毒餌料致死的報道,這進一步激化了線上與線下的社會矛盾。
新聞評論是表達作者對社會現象的理性批判與思考,是人們通過媒體交流觀點的工具,在教育受眾理智看待社會事件上首當其沖,新京報評論三篇發文沒有把目光僅僅凝視在事件的焦點狗身上,而是經過對社會背景的深度剖析,把“罪魁禍首”歸于狗背后的人和規則上,深刻體現了新聞評論應有的理性態度。
二、新聞評論中的理性分析
第一篇評論《整治不文明養狗,城市應堅定立場》以西安市公安局加強養狗的源頭管控和末端治理這一“史上最嚴”整治不文明養犬的舉措為例,揭示解決“愛狗”和“憎狗”兩派人士矛盾的核心不是“和稀泥”,而是在于城市治理應該“明晰規則,嚴格執法”,以規則的嚴格執行來倒逼養犬文明,反過來養犬文明的發展也有利于規則的進一步完善;第二篇評論《異煙肼毒狗,以暴制暴情緒反映公力救濟不足》則是將“異煙肼毒狗”歸類為一種私力救濟的行為,從私力救濟的概念出發揭示這一行為發生的本質原因是公力救濟不足甚至是缺失,如城市中養犬條例虛置,沒有形成相應的法律效力,同時作者分析執法不力的深層原因為不文明養犬行為是一種從眾行為,且文明養犬規章的可操作性不強,最終給出的建議是“將嚴格執法落在實處”,如在重點管理區進行試點、多部門協同合作、借助居委會的力量;第三篇評論《應該拿中國版“惡犬法案”制惡狗傷人》則立足于我國當前的法律現狀對受眾進行科普,如“異煙肼毒狗”屬于私立報復行為且要承擔法律責任,狗主人有看管好犬類的法律義務,最后提出建議認為我國在治理惡犬傷人時可以借鑒歐美法律細則。
從行文邏輯而言,三篇文章從不同的層面出發,采用判斷、概念、推理的手段提出觀點,就“異煙肼毒狗”這一社會熱點深入探討,分析其背后成因和實質并給出切實可行的參考建議,體現了新聞評論中邏輯的理性。同時,由“異煙肼毒狗”事件本身引發了人們對于該事件的批判和養犬法規并不完善的思考,實則是一種具體判斷和價值判斷,體現了新聞評論中判斷的理性。
此外,除第一篇評論由媒體從業人員撰寫,后兩篇評論均出自于高校法學教授之手,對事件分析切入點的不同也體現出不同作者思維方式上的差異,具體表現如下:媒體人撰寫的第一篇評論中有大量的新聞事實,如西安市公安局深夜在街頭出警查狗,小區內他們則與小區物業協作治理不文明養犬行為,同時該文引用了媒體網上調查的結果——近三成網友贊成“異煙肼毒狗”,反映出輿論場上“愛狗人士”和“憎狗人士”矛盾之激烈,從西安市的應對舉措延伸到所有城市的可以借鑒西安市的舉措是一種類比推理論證的方式,體現了作者將事物普遍聯系的思辨理性;后兩篇評論則從法律專業人士的視角出發,對于養狗法律細則并不完善提出了建議,具體到本地應該采取怎樣的治理措施以及認為應當借鑒歐美相關法律是一種歸納推理論證方式,體現了作者具有批判性思維的思辨理性。這三篇新聞評論中呈現出的理性都為其觀點增加了確定性和合理性,這對于受眾而言更易產生說服效果。
三、新聞評論中的倫理
新聞評論作為大眾傳播內容表現形式的一種,也履行著大眾傳播的社會功能和倫理要求。
首先,“異煙肼毒狗”事件把人們的視線集中于社會中激烈的“人狗矛盾”之上,然而“欲毒之而后快”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極端行為,原文章超過十萬的轉發量足以刺激眾多不理智的受眾造成難以估量的不良后果,新聞評論應實現其社會關系協調功能,調和社會各部分之間的矛盾,正如三篇評論中就此事件提出的關于愛狗人士和憎狗人士之間矛盾的正確解決、相關部門之間的有法不依和執法不力、私力救濟與公共救濟之間的不平衡等。
此外,新聞評論主張用批判的眼光看待社會問題,有解釋與規定的社會功能,尤其新聞評論是帶有明確意圖的說服或動員活動,它有義務在所傳達的內容之中帶有對社會事件的解釋并提示人們怎樣采取正確的行為反應。“異煙肼毒狗”其實已經觸犯到了法律的邊緣,后兩篇文章著重于向受眾普法,著重從法律的角度闡述“毒狗”可算作投毒和侵害他人合法財物,呼吁人們理性對待“人狗矛盾”。同時,也不忘提醒狗主人縱狗傷人要付相應的法律責任,對狗主人們的行為能起到一定的約束作用,這體現了新聞評論作為大眾傳播的社會化功能,它對傳播正確價值觀和行為規范有重要的作用。
第三,新聞評論也應該重視對社會議題的構建作用。正如“異煙肼毒狗”的根源不在于“憎狗人士”,也不在無辜的狗身上,而在于其背后相應法律法規的不健全,三篇評論文章均在文末呼吁完善養狗法規,實現有法必依和執法必嚴,新京報作為權威的主流媒體,其呼聲可以引起社會立法部門的注意,建立健全相應的法條規章,從根本上解決“人狗矛盾”,這也體現了新聞評論所充當的環境守望者角色,正確發揮了其職能。
綜上所述,新京報的三篇就“異煙肼毒狗”的評論文章,都很好履行了其社會功能,遵循了新聞評論的倫理要求。三篇評論中正確價值觀的傳達離不開三位作者的專業素質,而錯誤價值觀的傳達不但會損傷媒體的公信力,還會誤導社會輿論,嚴重的會導致犯罪、損害他人利益。因此,新聞評論作者應加強行業自律,提升自己的專業素質,媒體平臺也應繼續強化把關,讓受眾看到更多的優質評論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