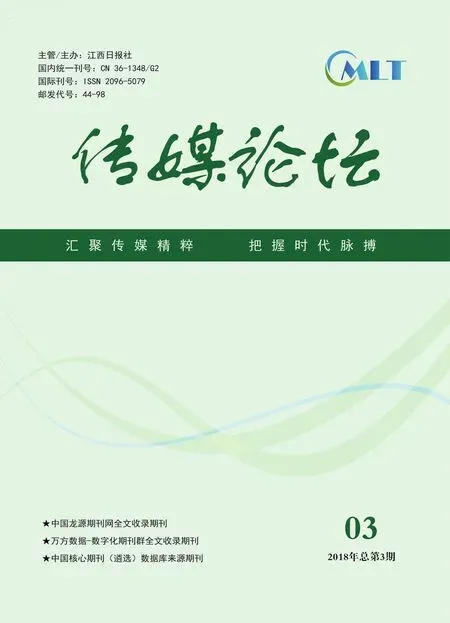社會化媒體語境下“平民記者”的角色分析
胡向華
(云南省曲靖電視臺,云南 曲靖 655001)
博客、微博、微信等一系列社會化媒體的興起,在給傳統專業新聞媒體帶來沖擊的同時,也給新聞業的整體發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以前,專業記者是大多數人可望而不可及的角色,現在,普通人獲得了社交的平臺以及發聲的權利,源源不斷的內容資源隨之而至,信息的傳播從原來的專業化媒體開始轉向平民化的視角,在不知不覺中,網民也開始扮演起“媒體記者”“編輯”的角色。
一、“平民記者”概述
(一)“平民記者”的概念厘定
雖然“平民記者”在社會化媒體上層出不窮,但是到目前為止“平民記者”還不是一個被學界廣泛認可和普遍使用的學術概念。關于“平民記者”定義的闡述仍是莫衷一是、含糊不清。
趙志立教授從平民記者的行為特點出發,認為平民記者就是“通過大眾媒體、個人通信工具,向社會發布自己在特殊時空中得到或掌握的新近發生的特殊的、重要的信息的公民。”除此之外,公民一詞在其他相關定義中也有所提及。實際上,所謂的“平民記者”“草根記者”“市民記者”都是強調了報道人所處的社會階層,其內涵與“公民記者”無異,只不過前三種提法更加強調了報道人的平民特征。
綜合來看,“平民記者”就是指某些掌握了一定技術和手段,出于某種興趣、動機,自發地、獨立地參與相關社會事件或對人物進行報道和傳播的普通平民。
(二)“平民記者”的行為特點
1.自發性
平民記者參與新聞報道一般是出于自身的某種興趣、需要或動機。例如11月22日,名為“認真的趙先生”的微博用戶為了救治父親尋求公義,在微博上控訴車禍肇事者,這是趙先生在對話語權的自覺行使的基礎上,出于自身的需要,自發地進行新聞報道。
2.隨意性
平民記者并沒有經過專業的訓練與嚴格的考核,他們所發布的新聞既沒有受到職業規范的約束,也沒有經過專業人員的層層把關與重重篩選,因此具有極大的隨意性和不穩定性。
3.集體性
布倫斯用“集體看門”過程來指稱社會性媒介內容傳播的管理過程,用“集體看門人”來界定在這一過程中所有內容參與者肩負的角色。平民記者與傳統的職業記者不同,它不屬于某個固定的組織,但是他擁有集體性的把關人。
(三)“平民記者”與職業記者
平民記者與傳統職業記者不同。從新聞理念層面來看,職業新聞記者將新聞報道看作是一份職業,他們追求真實與新鮮,有其自身信仰的新聞精神。平民記者則將新聞看作是一種興趣,他們出于個人的需求和動機來報道新聞。從報道方式層面來看,職業新聞記者秉承現場采訪、寫稿、審稿,最終才發布的報道方式,且記者個人一般隸屬于某個官方新聞媒體,發布平臺也就是他們所屬的官方媒體。平民記者以個人為單位,通常省略了采訪的環節,自顧自地在個人的社交平臺上進行發布。從輿論監督層面來看,職業記者行使輿論監督的權利,與其所屬的媒體單位是密不可分的,受其所屬單位的委托。平民記者也有監督的權利,但這種監督略顯單薄,只有在重重傳播后擁有更多的支持者后才生效。
二、“平民記者”的角色定位
(一)新聞的生產者
從廣義上來看,新聞生產是指新聞機構及從業者對新聞的選擇、加工與傳播,它是一條單向的鏈條,由生產主體、生產客體以及所形成的生產關系構成。在社會化媒體的影響下,新聞生產開始從單向的組織化生產向交互的個人化生產轉移。不僅新聞生產的主體被改變,傳統新聞生產的過程也發生了變化。
社會化媒體的核心是用戶,各種移動終端不再是單純從事閱讀活動的工具,即時的反饋讓用戶進行新聞生產成為可能。在生產新聞期間,他們從普通民眾的身份轉換成為記者。尤其在突發新聞的生產中,“平民記者”往往扮演著關鍵的角色。
(二)新聞的傳播者
“平民記者”的新聞生產去除了傳統媒體組織化生產的特性,單個人的聲音難免顯得單薄。社會化媒體平臺上的信息只有傳播出去,并引起一定的關注才能被稱之為新聞。新興媒介的即時性與便利性讓傳播唾手可得。因此,“平民記者”在自己生產新聞的同時,還從事著一定的傳播活動。
除此之外,大眾文化具有很強的流行性,尤其在當今快節奏、高風險的社會中,人們極其容易產生趨同心理。個人為了與群體中的多數意見保持一致,從而避免因孤立而遭受群體討伐的心態,致使原消息存在被跟風傳播的可能,規模性的追捧和盲目效仿甚至能夠形成輿論。
(三)新聞的消費者
身處消費社會的新聞業必須要把新聞當成一種商品,這樣才能贏得消費者的青睞。這些青睞在傳統媒體中體現為收視率、收聽率,在社會化媒體平臺中則體現為點擊率、點贊數、評論數、轉發數等。在此基礎上,才能把新聞的消費者轉賣給廣告商或贊助商,作為他們評測的依據,從而實現新聞媒體或“平民記者”個人的某些需要。
社會化媒體的出現正好契合了消費者的這種欲望和需求,只要打開一個新聞網頁就可以獲取最新的信息,快速地尋找到自己需要的各類信息。作為“平民記者”的媒體用戶不僅僅是新聞的生產者與傳播者,在資訊爆炸的今天,他同時可能也是一名新聞消費者。
三、關于“平民記者”的反思
(一)“平民記者”存在的問題
(1)“記者”層面:身份多重,定位模糊。在社會化媒體的情境下,“平民記者”的身份是即時的,他是新聞消費者的同時,也是新聞信息生產者和傳播者。“平民記者”的身份和角色并不穩定,反而在新聞傳播的過程中表現出“平民記者”、普通大眾、媒體用戶之間不斷轉換的特征。三種身份在很多時候是可以共存的,但是在某些特殊的場合中,就可能因為利益取舍的原因而發生矛盾,從而將當事人置于兩難的境地。定位在“記者”還是定位在“普通公民”,由此采取的行動將大相徑庭,后果也必然不同。
(2)受眾層面:信息誤讀,錯誤傳播。社會化媒體平臺為普羅大眾的自由表達提供了快捷方便的渠道,但是,網民們往往沒有能力或沒有意識去鑒別他們所傳播信息的真實性問題,導致一些假消息泛濫傳播。他們在轉發傳播“平民記者”的新聞信息時,更多衡量的是該信息是否符合其對新聞真相的自主預期,而不是我們所期待的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客觀審視,由此便可導致受眾對“平民記者”新聞信息的錯誤傳播。
(二)“平民記者”的改進策略
(1)“記者”層面:提高新聞素養。“平民記者”雖然有機會也有條件接觸到第一手的新聞材料,甚至會成為一些突發事件的目擊者或經歷者,但是他們容易受到思想覺悟、思維方式、認識水平、文化程度等多方面主客觀因素的限制。因此,他們生產出來的新聞產品多是隨機的、表面的、碎片化的,這就需要他們提升自身的新聞素養。
(2)受眾層面:提升辨別能力。社會化媒體在聚集了大量的信息的同時,也聚集了大量的網民,但是,網民的媒介素養卻依然止步不前。社會化媒體中因為“平民新聞”而侵犯隱私權、名譽權的事件屢屢發生,更有各種對信息的誤讀所導致的網絡謠言。網民應仔細甄別信息真假,在確定新聞的真實性之前不妄加評論;對于“平民記者”的新聞報道中明顯的個人化戲謔觀點不惡意轉發和評論;在事實真相尚未澄清時,應以開放的姿態對待各種觀點,不輕易定論。
四、結語
“平民記者”在社會化媒體語境下的產生與當前的社會環境分不開。當前的新聞受眾顯然已經不像20世紀30年代早期“子彈論”中的“中彈者”那么被動,“平民記者”的產生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必然。就新聞專業主義而言,“平民記者”還存在很多的不足,但不能否認的是,這個角色豐富了當今新聞業,也給正在“液化”的新聞業提供了一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