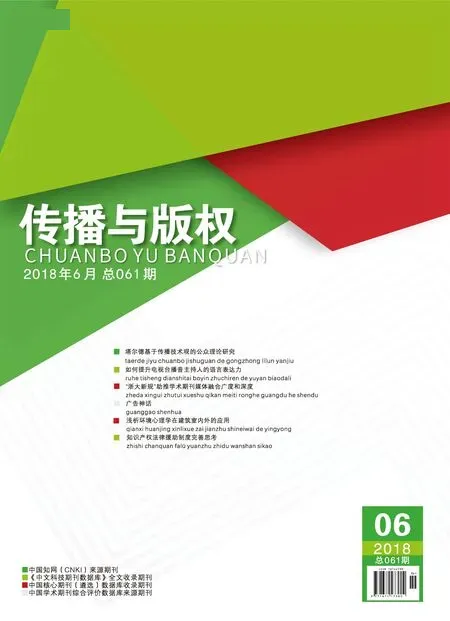隱性采訪的合法適用邊界
——以暗訪“海底撈”后廚為例
倪彤陽
一、研究背景
2017年8月25日,一則名為《暗訪海底撈:老鼠爬進食品柜 火鍋漏勺掏下水道》的新聞引起了熱議。海底撈火鍋因服務態度好又給人很干凈衛生的印象,深受消費者喜愛。而記者四個月臥底暗訪后廚得到的結果令人吃驚。
這則新聞從實效性和沖擊力來說是成功的,而記者采用隱性采訪的方式,真實地記錄了實際的情況,最大程度保證了真實性。但是,隱性采訪這種方式是否會觸犯到別人的權利?采取隱性采訪的合法邊界在哪里?
近年來,中國新聞侵權導致的糾紛越來越多。而相較于正規的采訪方式,隱性采訪更容易卷入侵權糾紛中。目前,對于暗訪的合法性,我國還沒有相關的法律法規對其進行規范,沒有法律條文證明其合法性,也沒有法律條文說明這是違法的。所以,如何把握好隱性采訪的使用限度,如何在法律和道德允許的范圍內運作隱性采訪,是值得新聞界關注的問題。為暗訪這一采訪方式尋找一個合理又合法的邊界是有一定的意義與必要性的。
二、隱性采訪中的法律限制
在記者暗訪海底撈的事件中,記者作為一個參與者和記錄者,在真正融入該事件的環境中的同時記錄下了后廚的環境及日常狀況,既沒有誘導也沒有“釣魚”行為。在調查過程中,暗訪記者的存在沒有對事件本身的發生或發展產生人為影響。而在該事件的相關報道中,記者沒有對涉事人員的面部形象進行公開,未侵犯任何人的肖像權或名譽權。盡管餐廳的后廚并不是完全公開的公共場合,但是出于維護公共利益的目的,記者的暗訪具有正當性,符合社會利益的需要。
暗訪海底撈后廚事件是一個成功的案例,既保證了新聞的真實性,又沒有逾越法律的邊界。但在新聞采訪的歷史上,也曾有許多越界暗訪的例子,引起社會的爭議,引發糾紛,甚至觸碰法律底線。新聞記者擁有新聞自由,但新聞記者也應該比普通公民具備更強的法律意識。
(一)記者和其他公民享有同等的合法權利
記者承擔著監測環境、獲取并傳遞信息等職責,為配合這些工作展開,記者需要進行各種形式的信息采集活動。由于記者的采訪活動屬于職務行為,所以很多的機構會給予他們較常人更多的便利,但這并不意味著記者的采訪活動具有司法或行政的強制力。近年來,由于法律意識淡薄和相關法律法規不健全,許多新聞工作者的自我角色定位錯位,產生“特權”思維,往往認定自己以新聞仲裁者、審判者和正義的化身出現在新聞事件中,不適當地擴張采訪權。最終往往導致其采訪活動的動機、手段和結果錯離了自己的義務和責任范圍。[1]媒體享有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但與此相對應,他們也有義務使用正當手段獲取新聞信息、維護新聞的真實性。
我國《刑法》第四條規定:“對任何人犯罪,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法律并沒有授予記者任何形式豁免特權,記者和公民享有同樣的權利。他們的身份僅是新聞事件的見證人和記錄者,所以記者不能因為采訪需要而侵害他人權利、妨礙社會秩序。
(二)隱性采訪侵權
我國憲法規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時不能損害國家、社會、集體利益和其他公民合法的自由權利。而在暗訪中,記者很可能會侵犯他人的權利,包括名譽權、肖像權、隱私權、人格尊嚴等人格權。
在隱性采訪中,記者通常會采取偷拍偷錄的方法取證。被采訪者在不知情的情況下,非自愿地接受了采訪,他們對記者不設防的狀態完全自然地暴露在鏡頭下,這種本色的狀態正是新聞報道中鮮活的素材。但在這種情況下,被采訪者的聲音、肖像、隱私都會在其無意識的狀態下被公布。公民有言論自由的權利。從公民的言論自由可以推定出一種逆向的言論自由權,即不言論的自由或沉默權。[2]就憲法意義而言,沉默的自由本質上是一項公民權,這種權利是“自然的、不可剝奪和神圣的”,是言論自由的體現。憲法保障言論的自由,也保障沉默的自由。[3]從這種角度來說,隱性采訪極有可能侵害到被采訪者的合法權益,也容易觸犯法律。因此,對隱性采訪的使用需要慎重考慮。
隱性采訪如果是以公共利益為基本前提,尤其是在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時使用無可厚非。但記者在進行暗訪時應該注意,不應該透露商業秘密、國家機密和與案件無關的個人隱私。對于記者來說,如果因為處理不當造成侵權行為,不僅獲得的資料無法作為證據,還會導致自己身陷糾紛。
(三)暗訪中記者角色扮演的程度把握
在有些事件的采訪過程中,為了減少采訪障礙和干擾,獲取有價值的新聞事實,記者選擇采用暗訪的方式,親身介入到事件中。但在不同的情況下,不同的新聞記者對案件的涉入程度和性質也不同。根據這種程度和性質的不同,隱性采訪可以在大體上分為三類:旁觀式隱性采訪、冒充式隱性采訪和誘導式隱性采訪。[4]
1.旁觀式隱性采訪。在旁觀式隱性采訪中,記者以一個旁觀者、目擊者的角色存在,不暴露記者身份,不干預新聞事件的發展,持中立態度,將特定場合中的事件發展過程偷偷記錄下來。從法律層面講,只要記者所旁觀的信息不涉及個人隱私、商業秘密和國家機密等,這種采訪方式就不構成違法。
2.冒充式隱性采訪。冒充式隱性采訪是指,由于記者在正常情況下難以獲得必要的信息,所以采用欺騙的手段,扮演特殊的身份,以便于收集新聞素材。在這種情況下,記者主觀上的欺騙程度和對事件的參與度都比旁觀式隱性采訪高。雖然冒充式隱性采訪是采用欺騙的手段隱藏記者的身份和目的,但是由于其社會危害后果不大,或者產生的負面效果小于新聞事實本身對社會的危害程度,很多記者沒有因此受到法律追究。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要采用冒充式隱性采訪,記者應該注意兩個問題:第一,是記者不能扮演警察、法官、人大代表、審計員、稅務員等具有一定權利的公務人員,如果在假扮采訪中行使了權力,有可能被視為刑事犯罪;即使沒有行使權力,也可能會誤導公眾,擾亂社會秩序。第二,記者要格外注意在隱性采訪中的參與程度,不能在假冒身份的過程中從事違法犯罪活動。例如2001年,中央電視臺記者為采訪非法倒賣文物的事件,假扮文物販子,臥底盜墓團伙,并偷拍下了一座西漢古墓被盜掘的全過程。這次盜墓活動成功盜掘出西漢時期的13件文物,雖然事后記者將這13件文物捐給了陜西省文物局,但是記者在此案中已經不再是單純的記錄者,而是違法行為的參與者。
3.誘導式隱性采訪。在誘導式隱性采訪中,記者通常人為地推動新聞事件的發展,此時他們的身份也已經由新聞事件的記錄者變為了制造者,背離了客觀、公正的職業立場。在這種情況下,新聞事件的真實性和客觀性受到了非常大的影響,事后無法準確界定事件原本就會自然發生,還是由于記者在其中的推動作用才會發生。因此,記者要盡量避免誘導式的采訪,不僅僅是出于對職業道德的遵守,也出于對自身的保護。
在上述三種隱性采訪中,記者的涉入程度遞增,其本身的爭議性也是遞增的。記者在進行暗訪時,要注意角色扮演程度的把握,不能觸碰法律的底線。要自覺遵守相關的法律、法規,謹慎守法。
三、隱性采訪中應遵循的原則
在隱性采訪的案件中,記者的行為往往具有爭議性,但是質疑此次暗訪海底撈后廚的聲音很少,主要是因為記者的暗訪保護了社會公共利益,并滿足了消費者的知情權。從這個角度來說,記者的暗訪是具有正當性的。此外,記者雖然是以親身介入的方式進行調查,但他的行為并未存在主動的誘導、鼓勵、暗示,那么他的暗訪便可以被視為公民自由權利的延伸。這可以對其他暗訪行為產生啟示作用:在隱性采訪中,記者要嚴格秉承某些原則。
(一)公共利益至上,基于滿足公民的知情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的陳力丹教授就曾在《傳媒》雜志中表明:“暗訪原則上不宜采用,特殊情形(例如涉及重大的人民生命安全之時)可以采用。”[5]新聞的根本目的是維護社會公共利益,伸張社會正義。隱性采訪可能會造成新聞媒體公信力的損害,也可能會侵犯到部分人的權益,這就更要求記者謹慎對待。除非是出于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且是在正規采訪渠道中無法得到的信息,否則就不應該采取隱性采訪的手段。如果隱性采訪所報道的新聞給社會帶來的有利影響超過了其所造成的損害,那么該采訪還是有意義和理由進行的;如果不然,那么該采訪不但缺少現實的意義,而且還會受到道德甚至法律的譴責。
(二)把握尺度,注意場合,盡量避免身陷其中
新聞事件發生的地點一般分為公開場合和非公開場合。公開場合是允許公眾自由活動的場所,“當一個人將自己置身于公共場合中的時候,也就承認了自己行為的公開性,放棄了該行為的隱匿權,而不管是記者,還是其他人都有將其在公共場合所看到的東西拍攝下來、記錄下來的自由。”[6]所以在公開場合的情況下,記者的隱性采訪一般不會構成侵權。但是在一些未經公開的場合,隱性采訪很可能會侵害其主人或利害關系人的隱私權、住宅權等權利。所以,記者要注意自己所處的場合,并把握好參與的尺度,避免侵犯他人權利甚至“以身試法”。
(三)秉持新聞的真實性、客觀性
真實性是新聞的生命,記者的職責便是客觀記錄并公開事實。隱性采訪因為其本身的特殊性,相較于常規的采訪方式更容易遭到質疑,這就更要求記者在采訪中嚴格遵循新聞的真實性原則,實事求是,采用合理且合法的方式,客觀記錄,遵守新聞職業道德。既不為了獲取證據進行誘導或“釣魚”,也不在事件報道中摻雜個人觀點和情緒,更不夸大其詞甚至不顧職業操守捏造事實。總而言之,記者要有回歸“事實本位”的自覺。
四、審慎把握隱性采訪
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給自己的信條:“無論如何,秘密調查都是一種欺騙。新聞不是欺騙的通行證,我們不能以目的的正當為由而不擇手段。秘密調查不能用作一種常規的做法,也不能僅是為了增添報道的戲劇性而使用。”[7]雖然隱性采訪是一種獲取客觀真實的、有價值的新聞信息的有效途徑和渠道,但它所涉及的問題不僅僅局限于新聞業務的范疇,其道德問題、合法性以及相關的侵權糾紛是當前新聞學界、法學界共同關注的話題。尤其在科技發展的今天,隱性采訪可借助的渠道越來越多,也使得隱性采訪帶來的問題與糾紛日趨復雜。審慎地把握隱性采訪,值得引起每個新聞工作者的注意。
(一)謹慎使用,防止濫用
隱性采訪從本質上講是一種欺騙,是一種通過博取他人信任來達到追求真相的目的的行為,其道德的正當性較弱。“隱性采訪沒有法律地位,不受法律保護,甚至經常成為法律和道德的悖論……各種媒介對隱性采訪的使用要十分謹慎,既考慮到社會的效果和社會的容忍度,也要考慮盡可能回避法律禁止性的區域。”[8]如果一味追求有吸睛度的新聞而濫用隱性采訪,不僅會造成大眾印象中的記者職業形象下降,而且會降低媒體的公信力,甚至會影響到社會誠信體系的構建。
《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準則》中規定:“記者要通過合法和正當的手段獲取新聞,尊重被采訪者的聲明和正當要求。”在涉及普遍的社會價值或重大的社會利益,又無法通過正常渠道獲取信息時,才考慮使用暗訪的方式。
(二)提升自我認識,正確實施新聞暗訪
為了更好地為人民、為社會服務,記者應該加強各方面的知識素養,特別是法律素養。許多新聞記者出現角色錯位或特權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其法律意識不足造成的。記者除了加強專業素養之外,也應該在思想上、觀念上加強對法律權威的尊重、對法律基本要求的認同,豐富自身,從法治的要求和法律的規定出發,開展新聞活動,防止違法、侵權的發生。同時也要掌握一定的技巧,在保證真實客觀的基礎上,盡量全面地收集信息。
五、研究意義
新聞暗訪本身具有一定的復雜性。在法制日益健全、權責界限也日益清晰的時代,新聞暗訪規范化合理化的使用要求越來越高,新聞從業者應該自覺地、有意識地對此形成一個綜合了邊界、準則、尺度的認識。因此,關于隱性調查的適用邊界的研究是有現實意義的。
此外,一方面,記者要加強自己的業務素養,新聞媒體要加強內部自律;另一方面,與之相關的立法也應該進一步完善。盡管在很多情況中,暗訪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存在復雜性,很難以一個嚴格一致的標準進行規范,但對隱性采訪進行立法上的明確的強制規定,將許可條件、抗辯事由等內容納入立法,有一定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緊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