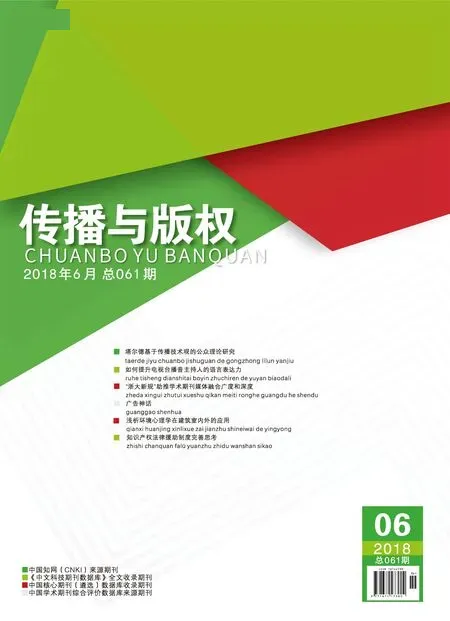社交媒體情境下明星遭遇網絡暴力成因分析
謝 磊
網絡技術推動傳播發展同時也滋生了許多問題,比如網絡暴力。國內外關于網絡暴力的研究較多,主要從傳播倫理與道德、法律規范、暴力生成機制以及對青少年的影響等角度出發。這些角度有著共同的特征,著眼點都是關照普通人所承受的網絡暴力。在網絡時代,還有一個群體——明星,承受著普通人施加的語言暴力,由于其身份特殊性往往被忽略。
2017熱播劇《那年花開月正圓》杜明禮的飾演者俞灝明于9月19日發了一條微博“我愿意接受所有聲音,但是我看不慣這些丑陋的心!有種站出來繼續噴!我只會更好地打你們臉!”并上傳了《那年花開月正圓》騰訊視頻彈幕截圖,彈幕內容主要有“當年你為什么沒有直接死了,這讓我給氣的”“趕緊死吧,你這演的也沒誰了”。當然俞灝明不是個例,另外一部熱播劇《我的前半生》中凌玲的飾演者吳越也遭到網友的語言暴力,無奈只能關閉微博評論。2018年初李小璐出軌門事件中無辜被扒的馬蘇無奈使用法律手段維護自己的權益。本文聚焦于明星所遭遇的網絡暴力,分析網絡暴力的成因。
一、數字生活空間傳者和受者平等的信息實體的地位
傳統大眾媒介情境下,傳播者掌握信息傳播的主動權,網友作為受者處于一個被動接受的地位。在整個傳播反饋過程中,網友對于明星的評論、意見,大多通過網友間的人際傳播進行消化、消解。另外,傳播反饋不及時,明星神秘化、與網友距離化,這樣的傳播模式下很難產生網友對明星的極端的評論。
在新的媒體環境下,陳剛將其稱為“數字生活空間”[1],我們很難將傳統媒介環境下的網友當成一個普通的個體對待。這數字生活空間下的網友被稱為“生活者”。“生活者”的概念肯定了消費者在網絡生活中,特別是微博之類的社交平臺傳播過程處于主動的地位。借用其生活者的概念,至此,作為“生活者”的網友與明星之間的對話處于一個平等的信息實體的語境下。在社交平臺中,網友作為接收者的同時,也是傳播者。
網友與明星雙向互等的傳播地位,一定程度上確保了網友可以方便及時地表達自己的意見、觀點。另外,基于微博的傳播特性——傳播與接收的同時性所決定,明星也可以第一時間查看網友的觀點。這種平等的權利賦予了網友群的“話語權”,是網友對明星語言暴力的基礎。
二、社交媒體的意見表達的“不自由”性
新的傳播環境,特別是以微信、微博等為代表的社交媒體給予了網友主動傳播的權利。很多情況下網友得通過社交媒體的言論引發輿論,但是這種輿論并不一定是大多數的意見集合。《我的前半生》中凌玲的飾演者吳越微博評論中除了“小三”的言論,還有很多支持者的聲音,肯定其演技。《那年花開月正圓》視頻彈幕包括俞灝明的微博中的評論是贊譽俞灝明的演技,覺得毀容后的行為很勵志。少數的帶有攻擊的意見為什么成為輿論?持理性、正面態度的網友在一些極端評論意見面前選擇沉默,擔心自己的言論與他人不符合,受到攻擊。“我在參與討論時,爭吵討論的事情也有發生,但極其容易受到周圍人的圍攻。”[2]所以網友在社交媒體表達觀點時,要么選擇沉默回避與他人觀點沖突,免于攻擊;要么隱藏真實意見,屈從于所謂的“主流觀點”。從這個角度來看,雖然社交媒體賦予個人表達的主動性,但是這種情景下沒有完全的自由性。
三、網友與明星強弱聯系的轉變
美國社會學家格蘭諾維特將人際關系分為強聯系和弱聯系。本文借用其對人際關系兩種形態用以描述明星與網友的關系。筆者認為伴隨著媒介形態的變化,明星與網友的強弱關系也發生了質的變化。
(一)傳統媒介情境下的明星與網友的弱聯系
在描述傳統媒介情境下明星與網友群體間關系,筆者借用了結構洞理論進行分析,較為形象地展示了這種情境下二者的關系。所謂的結構洞主要是指在社會網絡中有的關系形態是個體與個體間可以發生直接聯系,但有些個體沒有直接聯系,換句話說沒有關系或者關系間斷。從網絡結構上看,缺少了直接聯系的兩點,在二者之間就形成一個洞穴。社會交往過程中,如果無直接聯系的個體想建立直接聯系,必須通過第三方。那么第三方就占據了上述描述中出現的一個結構洞。
明星和網友就如同兩個缺少直接聯系的個體。二十個世紀七八十年代,明星與網友群體的關系大多通過影視劇作品、歌曲建立一些微弱聯系。而真正幫助二者建立關系的是明星的經紀公司,演員通過經紀公司安排出演某些影視作品,以熒屏形象與受眾見面。那個時代的明星生存、發展有賴于經紀公司的培養,而明星一旦出現問題有遭遇雪藏的風險。所以伯特認為,個人在網絡中的位置,比關系的強弱更重要,處在結構洞上的第三方掌握著資源與權力。傳統媒介情境下的明星個人發展主要有賴于經紀公司策略。在這種微弱近似于無聯系的情況下,網友群對明星的語言和行為缺乏有效途徑。
(二)數字生活空間中明星與網友的強聯系
數字生活空間下經紀公司依然存在,但是不能作為建立網友與明星聯系的第三方存在。數字生活空間中同時作為生活者的二者可以直接建立聯系,由傳統媒介情境下的微弱聯系發展成為一種強聯系。這種強聯系不僅體現在聯系的面對面、反饋及時、針對性強,更多地表現為網友的態度、數量可以決定明星的生存與發展。在這種情況下經紀公司失去了占據結構洞的可能,失去了絕對掌握明星發展的權利。這種強聯系的狀況,無形中強化了網友的傳播主動權,刺激了網友群體的“成敗在我,能奈我何”的心理。
四、群體壓力下的話語表達
新傳播情境下的網友掌握了表達的主動權。如何表達?表達什么?似乎成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網友的視頻彈幕“當年你為什么沒有直接死了,這讓我給氣的”,從網友表述語言內容來分析,對話好像是點對點的單純的人際傳播。但社交媒體不是單純地將人際傳播搬上了新媒體的舞臺,而是多種傳播形式的融合。網友在微博傳播過程中喪失了個體的特性,而是作為群體中一員而進行的話語表達,其表達行為、內容必然受群體影響。
(一)社交媒體情境中群體
在傳播過程中,個人的理智很容易受到群體行為的影響。“中國式過馬路”就很好地解釋了這一現象,處于群體中的個人帶有“別人都過,我也過,就是被懲罰也是大家一起”的從眾心理。盧因的“群體動力理論”群體行為可以直接影響和約束個人的行為。在網絡社會中,對某一事件關注而形成的一個群體,作為群體中的成員,獨立意識減弱乃至缺失,謹慎、理性的良好的個體特征消失,容易被刺激性、極端的語言或形象所感染。個體容易受群體的感染或者暗示,這樣一種行為機制下,個體理性消失,關注點轉移到同一個方向或者評論。在網絡傳播環境中,過激或惡意的言論更容易引起他人的模仿[3],社交媒體傳播機制語境下,群體中的個體行為表現為贊同、轉發或參與一切過激的討論。
(二)群體情緒:簡單、夸張、極端
群體中個體良好特征消失,必然導致群體情緒夸張而簡單。這種極端風格的群體情緒最直接的后果是,在群體的壓力下,受情緒(感性)支配的個人的語言和行為容易陷入極端。缺少理性的思維,個人智力作用減弱,群體智商為零。網友對演員吳越的評論,樂于混淆其在《我的前半生中》飾演的角色凌玲與其本人,對吳越的評論與其角色混為一談直呼其“小三”。而傳統媒體語境中的人際傳播中很難產生這樣的語言行為。“它就像女人一樣,一下子便會陷入極端”[4],由一個簡單的評論轉變為缺少個體理性作用的語言攻擊。
(三)群體中的去個體化
私下交流的人際傳播的個體會理性控制自己的語言進行表述觀點,在網絡傳播中對話要粗暴、刻薄許多。群體的夸張制作用于情感,在一個群體毫無顧忌地對他人包括明星進行侮辱、謾罵、攻擊的時候,群體中的每一個個體都可能出現去個體化現象。去個體化即群體環境下,個人自我知覺、理性能力喪失,從而導致自我約束的消失。某種情況下個體可能會放棄道德的約束,進行本能的宣泄,所以在網絡空間中對他人的謾罵、攻擊是個體喪失自我約束能力的群體狂歡。
20世紀50年代費斯廷格﹒佩皮通和紐康姆關于去個性化的實驗中,在昏暗的燈光下,去個性組受測試者通過長袍、面罩隱藏自己的身份(個體),相互不知對方身份信息的情況下,無所顧忌的發表自己對于父母不滿的意見,甚至數落、辱罵。隱藏身份本質上就是一種匿名現象,可以說匿名性是產生去個體化的主要原因。
五、評論的匿名性
(一)匿名性的個體行為
在傳播的過程中,匿名性使得群體感情狂暴、極端進一步強化。數字生活空間下的生活者的真實身份難以辨認,彈幕評論、微博評論中的群體相互之間不知姓名身份。在對于明星的演技包括生活等各方面進行評論是更顯得隨心所欲、缺少理智、不負責任。一切在于明星的身份的明確性,評論者的匿名性。作為群體中的個體,匿名性讓個體產生一種法不責眾的心理。此時個體在微博中的評論,是基于群體壓力下的一種行為。這種行為中的個體道德倫理觀削弱,缺少約束性,最終行為淪為宣泄原始本能的沖動。
數字生活空間下,無論是企業、組織、個人還是明星,都作為生活者而存在,他們之間是對等的信息實體。這種信息對等的關系,改變傳統媒介情境下網友被動接收者的地位,肯定了其傳播的主動性。基于這種對等的關系,出現了網友積極主動參與評論的現象,才有可能出現網友對明星的網絡暴力。
(二)匿名性一定意義上造成了傳播的不對等性
匿名性的存在在一定意義上又造成了傳播過程中,傳播者和接收者不對等性。微博傳播過程中,匿名的群體(傳播者或接收者)對于實名的明星(接收者或傳播者)的關系就是一種不對等的關系。言論行為對象的真實性,使得匿名群體的傳播更具針對性和指向性,從而刺激了群體宣泄原始本能的沖動。所以這種匿名對真實身份的傳播,只會更進一步強化群體的極端宣泄行為。在《那年花開月正圓》中飾演反派角色的俞灝明也因自己飾演的角色遭受攻擊。在評論中有大多評論都是脫離角色,直接攻擊個人。恰是因為俞灝明作為傳播對象身份真實性,群體在評論中對于角色的評論延伸到對個人的攻擊,乃至對其過往經歷進行深挖,比如在李小璐出軌門事件后,馬蘇作為好友幫助李小璐開脫,引起網友不滿,并揚言對其相關信息和過往經歷開挖。網友群體的匿名性與明星身份真實性的不對等關系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網友群體評論極端狂歡。
隨著社交媒體的發展,網絡暴力現象越來越多,但對其關注大多局限于普通人所遭受的網絡暴力。網友對于明星的語言暴力容易被忽視,一是由于明星身份的特殊性,二是與線下可見的暴力不同,網絡暴力大多是一種心理、精神傷害難以衡量[5]。除了群體心理、傳播者和接收者地位轉變、匿名性等原因,筆者認為網友與明星關系轉變是強化暴力最主要的原因。注意力、網友量經濟時代,明星個人的發展很大程度上依靠于網友量、網友態度,這種依靠關系強化了網友的主動地位,無形中成為網友群體狂歡的又一籌碼。